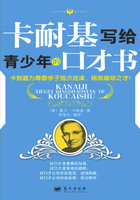当庹师把洞口的树根都清除干净时,他把供自己攀援而上的最后一根树根也一道砍断。张幺爷不由得自言自语道:“这哑巴不傻啊!做事比谁都聪明谨慎啊!”庹师仰头看了眼俯看着洞口的张幺爷,打手势让张幺爷让开,他好上来。张幺爷就让张子恒蹲下去,从张子恒的肩膀上下来了。庹师就像一只灵活的猴子般从树洞里钻了出来。钻出来的庹师也没有闲着,他又用铡刀卖力地砍起了铺散在地上的树枝,落在树枝上的积雪在庹师的铡刀下粒粒飞溅。张子恒不明白庹师这是要干什么,朝张幺爷说:“这哑巴是不是疯了?好像有使不完的蛮力?”张幺爷没好气地说:“你才疯了!庹师的脑瓜子比我们谁的都灵光,他是要把那个洞口用树枝盖住。”张子恒哦了一声,都看着庹师在那儿忙活。庹师砍断了一堆树枝,朝张幺爷打需要帮忙的手势。张幺爷朝张子恒说,去帮帮他,他够不着。张子恒和几个愣小子一起,搭起人梯把树枝送上树桩,把洞口掩盖了起来。忙活完后,张子恒对在一旁抽叶烟的张幺爷说:“幺爷,这样盖住也不是办法。这个洞终究是个后患啊,得想个周全点的办法。”张幺爷说:“暂时先这么弄着。
洞里的妖孽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回去我们再合计个办法出来。不过我话先说到前头,这个洞的事情,你们一个个回去后,就是天王老子问起,都不许给老子说半个字出去。这洞太过邪气,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可不能再把地下的妖孽惹毛了!”大伙儿都冲张幺爷点头。张幺爷又过去看喜哥,喜哥依旧睁着那双死鱼般灰白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那棵树桩。张幺爷叹了口气说:“你可不要像张子坤那样疯一辈子啊!你是个还没点大蜡的人呢!”张子恒说:“幺爷,现在就把喜哥弄回去吗?”张幺爷说:“弄回去吧!”“弄回去怎么说?”这还真是个问题。张幺爷搔了搔后脑勺,说:“回去就说喜哥撵蛇的时候跑得太急,被一块石头绊倒了,把脑门磕破了,就成这样了。”张子恒说:“这谎话村子里的人会信吗?”张幺爷说:“不信也得信。都人心惶惶的,可不能再说些古怪的事情出去添乱了。”于是张子恒就派了两个愣小子扶喜哥回去,又一再嘱咐回去后该怎么说隐瞒真相的谎话。喜哥被送出林子,张幺爷就过去和庹师打手势。庹师正围着掩盖好的树桩转悠,似乎对这个掩盖的洞口极不放心。
张幺爷朝庹师打着要去继续寻找蟒蛇的手势。庹师看着朝他打手势的张幺爷,射着凶光的阴阳眼看得张幺爷心里直发毛。张幺爷骂了一句:“我日你先人!你去不去表个态啊!这么看着老子搞卵!好像老子要害你似的。”庹师盯着张幺爷看了一阵,然后朝张幺爷咿咿唔唔地狂打手势,情绪似乎还很激动。张幺爷被庹师的这一通哑语给弄懵了,理不出一点头绪。张子恒在一旁说:“这个怪人比的什么意思?”张幺爷很不耐烦地说:“鬼知道啥意思!”庹师朝张幺爷咿咿唔唔地打完一通手势,然后把锋利的铡刀朝肩膀上一扛,就朝刚才巨蟒逃跑的方向走。张幺爷朝张子恒和几个愣小子说:“跟上。”这回老林子里蟒蛇留下的血迹非常明显,尽管林子的光线已经非常昏暗,看不清蟒蛇流在荆棘上的斑斑血迹,但是一路上弥漫着血腥的气息却可以领着庹师和张幺爷他们顺着蟒蛇逃跑的路线寻着过去。越往前面走,张幺爷的心越是不踏实起来。“糟了!要坏事!”张幺爷冷不丁地说。紧跟在后面的张子恒说:“什么要坏事?”张幺爷说:“妖孽一定是逃到饮牛池里去了。”张子恒说:“我刚才就说它是朝那个方向逃了。
本来是想一直追过去的,一是没有庹师跟着,心里没底;二是担心你没有跟上来,所以就折回来了。”张幺爷说:“真要是逃到饮牛池里去那可就祸害了。”张子恒说:“有那么悬乎吗?”张幺爷说:“悬乎的还在后头呢!真是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啊!报应啊!唉!”张子恒说:“幺爷,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村子里谁作孽了?你可不要信口开河啊!”张幺爷说:“你个青屁股蛋子懂个屁!村子里的人能作好大的孽?你还嫩呢!好多事情你根本看都看不到。”张子恒不服气地说:“你看得到?你是神仙?”张幺爷说:“我把话先撂这儿了,这个事情小不了。你见过寒冬腊月下落地雷的吗?还劈开了那么大一棵树!奇闻啊!”张子恒说:“幺爷,你这么大数岁了说话可得负责的。现在谁造谣谁倒霉。你的嘴也不该这么松的。”张幺爷说:“老子还不知道这些吗?我只是在这儿说说。”张子恒朝跟在后面的愣小子们叮嘱道:“幺爷刚才说的话哪儿听到的哪儿丢哈!别拿出去乱说。我要是知道谁出去乱说了,非揭了他的皮不可!”张子恒恶狠狠的表态让后面的愣小子们面面相觑。
寻着蟒蛇留下的血腥气息,一伙人终于走出了老林子。一个三四百亩宽的椭圆形的水塘出现在了面前。这就是饮牛池了。饮牛池的得名几乎已经无可考证,它的得名应该是和卧牛山捆绑在一起的,包括现在的卧牛村。饮牛池在村东头,池塘的北面是卧牛山,牛头绕了一个弯,就伸在池塘里。从地理位置上分解,这个池塘被称做饮牛池也是非常恰当的。无论天旱还是发洪水,饮牛池的水总是保持着不涸不盈,始终清清浅浅的。这就给这个池塘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就是这么一个水色清亮的池塘,卧牛村的人却很少光顾,因为他们对这个池塘一直心存敬畏。说池塘里的水是神牛饮用的,谁去打搅了神牛饮水,谁的家里就会遭瘟!祖祖辈辈,一直心存着这种顾忌,所以这口池塘的周围竹子树木芦苇都长得非常茂盛。就是池塘边上的污泥里长的野荷莲藕,也从来没有谁去动过。村子里的人认为,夏天长起的翠绿的荷叶是神牛在饮牛池困乏的时候歇荫凉的,冬天里埋在污泥里的藕是神牛过冬吃的食料。很多时候,有了传说才会有敬畏,有了敬畏才会有和睦共处的平衡。
传说和封建迷信不能混为一谈,但在那样的年月,概念的混淆不清已经令所有的人疯狂和失去理智。也许当时的张幺爷已经感觉到了这样的疯狂会带来灾难的后果,所以他才有了不祥的疑虑。这饮牛池的水也是挺神奇的。夏天凉爽刺骨,冬天却如同温水。别的小沟小河、池塘水渠都结成了厚厚的冰,唯独这饮牛池的池水,蒸腾着白茫茫的雾气。天色已经昏暗下来,饮牛池的水面蒸腾起的白茫茫雾气越加地浓重。雾气悬浮在池塘的表面,使池塘显出几分神秘。池塘的四周非常安静,看不出池塘有被什么东西打搅的痕迹。一伙人站在雾气弥漫的饮牛池边,有点迷茫了。只有庹师围着池塘转起来。池塘岸边上的杂草长得非常杂乱茂盛,高的齐胸,矮的也可以没膝。或许是由于池塘周围的水汽太重的缘故,蟒蛇留下的血腥气味在这儿神秘地消失了。杂草上的积雪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只留下一朵朵残雪点染在上面,显得有点苍凉。杂草很湿,张幺爷他们身上的衣裤已经被杂草上的雪水打湿得差不多了。张子恒说:“怎么看不见这东西进入池子里的痕迹?”张幺爷用眼睛梭巡了下四周,说:“跟着庹师找找看吧。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如果真是出了这片老林子,这个池塘应该是它唯一藏身的地方。”张子恒听了张幺爷的话,就吩咐跟上的愣小子们分头围着池塘寻找蟒蛇进入饮牛池的蛛丝马迹。虽然知道蟒蛇在老林子里受到了重创,但是大伙儿对这么大的阴邪之物还是心生芥蒂,在寻找的过程中显得小心翼翼极其谨慎。突然,庹师矮小的身影隐没在杂草丛里,就像在杂草丛里突然消失了一般。其实大伙儿在池塘边分头寻找蟒蛇的过程中,眼角的余光始终是瞄着庹师的。庹师现在俨然已经成了这伙人的精神支柱,庹师身影突然在杂草从里消失了,大伙儿的心里顿时就是一惊。张子恒是最谨慎的一个人,他立刻大声喊道:“庹师呢?庹师怎么不见了?”张幺爷也一直在注意着庹师那边的动静,他朝张子恒做了个不要出声的手势。大伙儿立刻明白庹师那边出现了状况,都用直愣愣的眼神看着庹师隐没的那片杂草丛。庹师隐没的那片杂草丛是池塘边长势最好的杂草丛,庹师在那一块地方搜寻时,茂盛的杂草几乎就要漫过他的耳际。而现在,庹师整个人却在杂草丛里消失了。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张子恒和张幺爷开始战战兢兢地朝着那片杂草丛靠近!突然,只见深深的杂草丛里呼的一下抬起一颗邪恶的头!蛇头!是巨蟒的头!这颗蛇头的邪恶只能用惊怵和战栗来形容!张子恒和张幺爷虽然也有点心理准备,但对巨蟒的突然出现也是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几个愣小子也是吓得浑身打颤。巨蟒的头抬得很高,高出杂草起码有半米,这样它就处在了居高临下的位置。它的头在草丛上面游移搜寻。它也意识到了危险的逼近。庹师矮小的身影这时在巨蟒的脑袋下面现身出来。看见庹师的身影又出现在眼皮底下,巨蟒邪恶的眼睛里射出两道黄澄澄的光芒,它呼地朝庹师吐出了猩红的芯子,鼻孔间喷出一股浓浓的白气。庹师在巨蟒的脑袋底下弓腰缩身,两只长长的手臂微微张开,似乎随时准备和巨蟒放手一搏。张子恒和张幺爷虽然心惊肉跳,但是他们还是鼓起仅有的勇气朝着巨蟒和庹师慢慢靠近。突然,巨蟒张开了血盆大口,朝着庹师兜头叼了下去。庹师这回没有只是晃动脑袋和身体,而是一个鹞子翻身,以极其快捷灵敏的速度伸手骑在了巨蟒的脖子上。巨蟒庞大的身躯顿时从杂草丛里翻滚出来,白色的肚皮和青色的背脊在草丛间翻滚起伏。
庹师显然是用赤手空拳制住了巨蟒,巨蟒在草丛间剧烈地翻滚,显得惊慌而且没有章法。张幺爷大喊道:“上,赶紧!”说着带头朝巨蟒翻滚的草丛扑去。张子恒和几个愣小子亢奋的神经也在极度惊怵的状态下被完全激发了出来,从四面包抄上去。庹师在巨蟒庞大的身躯下死死地钳制着巨蟒的咽喉部位,无论巨蟒在草丛中怎么翻滚,庹师就像吸附在了巨蟒的身体上的蚂蟥一般。就在张幺爷和张子恒他们对巨蟒形成包围之势的同时,巨蟒庞大的躯体朝着饮牛池里飞卷了过去。
张幺爷大叫了一声:“糟了!”随着话音的落下,巨蟒青黑色的躯体已经盘卷着射入了水塘里,轰的一声溅起一两米高的水花。庹师也被巨蟒带入了池塘,他的身体陷入了巨蟒扭曲盘卷的躯体里。巨蟒显然仍旧没有挣脱庹师的钳制,它在池塘里越加翻滚得厉害,池塘里一时间波浪翻滚、水花飞溅,清清的池塘水顿时变得浑浊不堪。张幺爷和张子恒他们站在岸边的草丛里,一个个都傻眼了,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在池塘里和巨蟒做着垂死搏斗的庹师。不一会儿的工夫,巨蟒已经翻滚到了池塘的中心,翻卷起的水花也越来越大。张子恒声音打颤地说:“幺爷,咋办?咋办?”幺爷这时也是神情呆滞。他眼巴巴地看着在池塘的中心翻滚的蟒蛇,双膝直挺挺地跪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