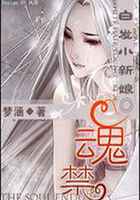这个女人止住脚步,回敬道:“哟,高大经理急了?您不是号称财主嘛,这点钱算什么,权当是给我们几个加菜了,怎么着也该你放放血了。”
“臭娘们,你”
吴爽突然阴森问道:“想动手打我?来啊,动手啊。别以为只有你才知道要自己的利益,这年头,累死累活,不为自己,天诛地灭。”
高经理愣在原地,等吴爽走远了,才反应过来,无可奈何,只能破口大骂。
“妈的破鞋,就是一破鞋,得瑟什么呀得瑟,不就和孙扬有一腿嘛,得,逼得老孙又割脉又毁容,就是死不掉,现在又把腿伸给陈治这个娘娘腔,妈的,都是一班”
话没说完,经理从办公室走出来,高经理硬生生把后面的话和着口水一起咽进肚子里,愤愤不平。
经理假装没听到,面无表情。
大厦,是用一张一张的钱,糊起来的。
大厦里的人,是用一张一张的钱,糊起来的纸人,钱被烧掉,他们就会消失。
如果被烧掉半边脸呢?
孙扬,我一直以为他死了,原来没有。
不奇怪,这栋大厦,除了工作,没人愿意和我来往,他死了,还是活着,我又怎能知晓?
原来,消防通道里的半脸人,是他。
每座大厦,窗户后面,都有一个秘密。
下班,黄昏,漫无目的行走。
竟走到地铁入口。
犹豫,下了自动梯,直走,左拐。
我的地铁通道里的朋友。
他还像往日一样忙碌,把牌打散又叠起,又打散,又叠起。
我蹲下。
他没有理会我。
“朋友,你的大楼,还没盖好?”
第一次称呼别人为朋友,这让我有些别扭。
“为什么要盖好?”
他没抬头。
“你不是一直在盖吗?”
看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
“哧,你真幼稚。事情怎么就只看到表面?”
“啊?”
他很不屑,道:“我是在找大厦里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每一座大厦,窗户后面,都有一个秘密,既然是秘密,又怎能告诉你?”
无言以对。
良久,我艰难开口:“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哈哈大笑,显得非常愉快,道:“我是什么人?是神经病。”
“你”
“你们不都这么认为吗?”
“我不认为自己在和一个精神病患者对话。”
“嘿嘿,那你认为我是什么?”
“我把你当朋友。”
说出来,心里,轻松了。
我的朋友,没说话,使劲抹把脸,托腮,发呆。
良久,他问我:“你觉得快乐吗?”
我没回答。
“你不快乐。”
“这个话题,有点矫情。”
我的朋友,自顾自地说下去,道:“大厦,藏了很多秘密,大家都不开心,孙扬不开心,吴爽不开心,老高不开心,你也不开心,大家都不开心,这个城市里,每座大厦中,都有许多人不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脊背上的毛细血孔一下紧缩起来,有点冷,从里面发出来的冷,一个地铁通道里的流浪汉,他,竟然对我了如指掌。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哈哈,你刚才不是说我是你朋友吗?”
“我问的是你另外一个身份。”
“我是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哦,不对,还是个乞丐,你也可以称我为流浪家。”
“你太可怕了。”
我决定立刻离开,今后,不再进这地铁站。
脚抖。
他突然“噌”的一下跳起,居高临下,死死按住我的肩膀,歇斯底里,露出森然白牙,他贴近我的脸,大吼道:
“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不敢面对,你是个懦夫,你不敢面对,你困在自己的世界里走不出来,你们全都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简单点?我是个神经病,我就很简单,我就很快乐,啊啊啊,你们要逼死我呀”
他双眼充血,他嘴里的热气,烘在我脸上,似乎,有点血腥味。
挣脱开,落荒而逃,背后远远传来他的声音:
“人哪,何必跟自己过不去,放下,要放下啊。”
心里有些东西被搅起来,混沌,时而又清晰,有些东西,要破茧而出。
一个星期后,深夜十一点半。
赶报表,公司里还有几个人没下班。
走到电梯里,站定,昏暗灯光下,看着电梯门,缓缓合上。
灯闪了几下,今晚,可能电压不稳。
突然,一只手,从外面直直插入门缝中,电梯,艰难地挣扎两下,缓缓打开。
那只手上,擦着粉红色指甲油,熟悉的记忆。
吴爽。
她面无表情走进来,面对电梯门,不做声。
门,缓缓合上。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突然打我电话,那该多好。
灯又闪几下,更暗了。
喉咙很痒,忍不住咳一下。
她还是背对我,没动静。
电梯坏了。
震两下,在十三楼的地方,卡住。
灯在刹那间,熄灭。
令人窒息的黑暗,空气里,皮革腐烂味道,闷,极闷。
伸手不见五指。
可我,能感觉到,她,正在慢慢,转身。
这个女人,此时如此安静。
“唉。”
一声叹息,似来自遥远的某处角落。
“你很怕我?”
她突然开口问道。
嘴巴张了张,说不出话,像有个东西哽在喉咙。
“也难怪,半夜三更穿个红衣服到处跑,脸上全是血,谁看了都怕。”
“我不怕。”
突然,她朝我迈近一步,“咯咯”笑着,问道:“如果,我是已死去的人呢?”
怒火,开始疯狂在心头烧起。
“我知道,三年前,你就已经死了。”
她的笑声,从嘴边被只无形的手一把夺去,无声无息。
“什么意思?”
“你是个死人,和我一样,是藏在大厦里的尸体。”
“好,说得好,继续说啊。”
很疲惫,有种感觉,想摸出美工刀,在电梯墙上刻下“范进”。
很多很多个“范进”。
“你怎么不说了?”
“没什么好说的。”
“我过得很苦,范进,我快撑不下去了,孙扬,天天晚上在消防通道里守着我,那脸烂了,也不治,我又不能报警。”
“那是你自找的。”
吴爽,她突然尖叫起来,咄咄逼人,她质问道:“什么叫自找的?我为了活得好一点,我有错吗?啊?我有错吗?”
“你没错,是我错了。”
“你以为自己就很好吗?你天天像个神经病一样在桌上刻名字,偷偷把桌子藏在天台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说的真没错,你是具尸体,行尸走肉,脑子有问题。”
我突然想起我的朋友。
“吴爽,你快乐吗?”
她像泄气的皮球,委顿,黯然道:“我快不快乐,难道你看不出来?”
“你能放得下吗?”
“放下什么?”
是的,放下什么?
阴霾,不是来自大厦。
来自心灵。
黑暗里,在虚无的上空,我看到自己,慢慢脱下身上结茧的盔甲,我想笑着告诉每一个人,我活过来了。
是的,我活过来了。
放下,放下什么?
放下你心中的秘密,放下你心中的欲望。
人为什么活着?
心灵自由。
这与大厦无关,与窗口无关,与桌上的名字无关,与别人的冷眼无关,与一切一切都无关。
心灵,才是家园。
“吴爽,我很快乐,祝你幸福。”
灯亮了。
电梯缓缓下行。
吴爽,诧异地看我,在她眼里,我看到自己,在微笑。
“叮”。
一楼到了。
电梯门打开。
跨出去前,我友好地伸手过去,握住她冰冷的手掌,曾经牵着走过大街小巷的熟悉的手掌,对她说:
“我放下了,祝你快乐,愿意放下,就能美满。”
她的眼眶有点红。
春天来了,冰冻的田野开始解冻,鸟儿“吱吱”歌唱。
走出两步,想起个问题,转头问她:
“你认识前面地铁通道里那个经常在的流浪汉吗?”
“认识,怎么了?”
“哦?”
“他叫叶增,你来之前,这里的销售部经理,后来斗不过别人,被陷害,弄得身败名裂,现在有点疯疯癫癫,在地铁里整天打牌唱歌。”
走到地铁口,他还在,发呆。
我提两个面包,两瓶水,蹲下,笑道:“朋友,别发呆了,谢谢你,放下,就是快乐。”
好了,今晚的故事,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