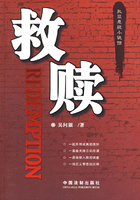张幺爷有点得意地说:“看看,我就说这儿有古怪吧?躲在这山洞洞里头教这些娃娃读孔老二的‘望天书’,要是让县里头或者公社一级的晓得了,这些人早就被抓起来了;还教这些孩子‘奇门遁甲’的哄人把戏,真是不像话。”
白晓杨现在对张幺爷说的话也是半信半疑,没有说话。她也被朱珠等四个孩子的离奇表现给整得云里雾里地有点蒙了。
张子恒这时朝张幺爷说:“幺爷,春明咋办?”
张幺爷经张子恒这么一提醒,说:“对了,春明这孩子得带走,不能跟着这几个孩子在这里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幸好我明白得快,不然就上了张子坤的当了。”
“可是这铁栅栏关得那么死,我们咋把春明弄出来啊?”张子恒见张幺爷终于和自己站在了一条战线上,说。
张幺爷说:“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我这就去找佘女子放春明出来。大不了我跟他们翻脸。咱春明是正派人家的孩子,咋能在这儿学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张幺爷说完就朝巷子口走。
白晓杨怕张幺爷又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连忙说:“干爹,我跟你一起去。”说着脚跟脚地跟着张幺爷走了。
巷子里现在只剩下张子恒一个人,他转过身看着被关在山洞里的春明。
春明已经退到了山洞靠里面的地方,光线昏暗。张子恒一时间不能看真切里面的情况,就朝春明说:“春明不要怕,我们这就想办法把你弄出去。”
春明却朝张子恒摇头。
张子恒说:“你摇头干什么?难道你不想五爸把你带出去?”
春明又点头。
张子恒叹了口气说道:“完了,这孩子中邪了,好坏不分了,要在这深山沟里变精变怪了。”
张幺爷和白晓杨出了巷子,径直来到台地上,却见柳妈妈站在台地的边缘望着下面的台地出神,脸上的表情焦虑又忧伤。
张幺爷和白晓杨走到柳妈妈的身边她竟浑然不知。
“柳妈妈,你在看啥呢?”张幺爷问。
柳妈妈回过神,见是张幺爷和白晓杨,脸上的表情更加忧虑了,说:“佘女子又一个人回那边的黑风洞里去了,又不晓得要在那边住多久才回这边来。”
“黑风洞?哪儿有什么黑风洞?”张幺爷问。
“就是你们来的那边的那个洞。”柳妈妈说。
“你是说佘女子回那边的山洞里去了?”张幺爷边问边朝那道石门望去。那道石门紧紧地关闭上了。
柳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回那边去了,估计是心病又犯了。”
“心病?啥心病?”张幺爷越加不解。
“佘女子的心病重得很,她不说,谁知道?”柳妈妈又叹了一口气说。
张幺爷还要刨根问底,柳妈妈已经转身走进了屋子。
柳妈妈也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张幺爷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这究竟是咋回事?咋一阵晴一阵雨的?各个都鬼头鬼脑的!”
最底下的一层台地上,伍先生已经把朱珠等四个孩子召集在了一起。四个孩子的手老老实实地背在身后,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起。
伍先生半躺在那张逍遥椅里,一张瘦脸阴沉沉的,薄薄的镜片后,两道眼神就像寒光闪闪的刀锋一般在四个孩子的脸上溜过来溜过去的。
朱珠等四个孩子似乎已经被伍先生驯化成了四只听话的宠物。在他们脸上,再也看不出有丝毫的调皮和顽劣的品行,就更别说能够从他们身上嗅到春明的那种野性十足的气息了。
四个孩子低垂着脑袋,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就像是正在接受批斗的四类分子一般。
“哪个先说我就饶了哪个,哪个最后说我就惩罚哪个。”伍先生说。
伍先生对这四个天真单纯的孩子用起了离间计。
四个孩子没有中伍先生的计,但样子却噤若寒蝉,看见张幺爷和白晓杨走过来,眼神既单纯又可怜。
伍先生端起乌木茶几上的盖碗茶,喝了一口,见四个孩子有宁死不屈守口如瓶的架势,从薄薄的镜片后射出的两道眼神更加阴冷了。他从逍遥椅里欠起身,拿过那根蜡黄的荆竹条子,在乌木茶几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提高了声音喝道:“你们是不是要跟先生硬抗下去?嗯?”
四个孩子对伍先生手里那根蜡黄的荆竹条子似乎已经产生了条件反射似的恐惧感。伍先生手里的荆竹条子抽在茶几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时,四个孩子的身子骨也同时震颤了一下。
白晓杨皱了一下眉头,走过去,轻声朝伍先生说:“先生,你别把这些孩子吓着了!他们还小的,没经过事的。”
伍先生这时朝白晓杨冷冷地瞟了一眼,正色地朝白晓杨问:“你是谁啊?”
白晓杨没有想到伍先生会这么问自己,而且声音又冷又硬地不近人情,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了,尴尬得脸也泛起了粉色。
张幺爷连忙朝伍先生打起圆场说:“伍先生不要见怪,她是我的干闺女——白晓杨。我平常都叫她小白的,刚才忘了跟你介绍了。”
伍先生却说:“我不管她是谁,我在教我的学生,别的人就不要插嘴。牛圈里还伸出马嘴了?”
堂堂的伍先生居然出言不逊。白晓杨急得瞪起了眼,脸越发地涨得红了,眼睛里有了几分怒意地看着伍先生。
伍先生已经懒得理会白晓杨和张幺爷。教书先生的古板与刻薄此时在他的身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和刚才提着一壶酒找张幺爷的那个伍先生简直是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