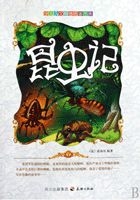(1)
赠你一场盛世
春分,玄鸟至,胭脂国。
十年前初见她,那里是一座碑,无字无名。
她浅浅朝我笑。一瞬间,殷红了桃,碧翠了柳。
立夏,蝼蝈鸣,胭脂国。
热风吹落了一地繁花,沁脾芳香。门外有人轻扣柴门,我浅声应过,竹帘浮动三层迎了微风潜入,那男子随这青岚而来,馨香拂过我颜面。
“景阳君,如今天下谁姓?”我问他
他久久不语,许是夏花太艳,扰了他思绪。我又问,如今天下谁姓?他缓缓,吐出一个“卫”字。
卫,卫膺。
我听过无数关于他的故事,他叛国、灭世,所有都缘起一个女子。十年间他烧杀掳掠四处征战,想不到如今他还是得了天下,如今听起来像是个笑话。
但是天下与我无关,我在此处,不知岁月。
每隔一季,我会待见一次客人,问他们如今是何朝何代、太平抑或乱世。来者便事无巨细地将见闻告知于我,关于国、关于世,有时候,他们也会讲写风花雪月。
作为回报,我为他们织梦。
胭脂国遗世独立,古往今来所有的织娘都生活与此,编织不同的锦绣,许久以前,这里有人编织将来、有人编织富贵,有人编织权势……然而如今她们都不在了,或是逃离,或是绝杀。我也是其中一名,最小的织娘,只编织梦境,梦境是无害无伤无所谓攀比的,所以,我被留了下来。
巧弄机杼,景阳君在竹木中躺下,我在他身上化了一层薄丝,他如孩童般闭上眼睛,我见窗外浮云凝了一片,似雨将至。
“景阳君,今日你想要怎样的梦,盛世,还是安宁?”
他在睡梦里露出一丝浅笑,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清澈。景阳君忧国忧民十三年,年年都会向我讨要一个太平盛世的梦幻。明知道等他醒来,又要面对新一场浩劫。如今的卫膺应该是他最后一个浩劫。
我常想,若是三姐,她可以为他编织强兵壮马,让他御敌千里。若是二姐,她可以为他编织国富民安,让他稳坐江山,可惜,我是织梦娘。我能给他的,只有一夜梦幻。
今年立夏的时候,景阳君亡国,他最后一次来找我,他要我为他织一个梦,梦中不再是焕然盛世,是一名女子,天然去雕饰。
她名唤卫嫣然,卫膺之女。
我拉过棉丝,重重又叠叠,景阳君安然睡着,我轻抚他的睡脸。
卫嫣然,卫嫣然。
忽然锦帛撕裂,我的丝线被他全数割裂,化为乌有。景阳君的眼睛布满血丝,我能见到他身上满溢的杀气,他的剑架在我脖上,神智不清。
“景阳君。”我叫他,他不应。满地散乱的线,如银色的溪沟,密密布置。
十年前他收留了一名卫国女子,当时卫膺尚未成势,他放狂言曰:染指嫣然者必灭之,片甲不留,他果然言而有信。
“谁都知道卫嫣然是卫膺之女,他视她为珍宝,高于八国的百姓,高于天命。当初你为何非要她不可?”我问。
“你还小,未必能知道。”景阳君惨笑着,起身夺门而出。
我一路追赶他到胭脂山谷,见他仰天长啸纵身跃入那万丈深渊。他把梦境当成现实,混乱了神元,这个男人断八脉、裂五脏,必死无疑。
脚下的胭脂山谷,传来腐臭的气息,第八位国主在这里轻生。他们要我编织一个卫嫣然的梦,醒来之后,便失去了心智。失去心智之前,他们已然失去了国土。
“为什么要染指那个毫不相关的女子?”
他们的答案不约而同,你还小,你未必能知道。
从来,我都只默默看着,不做表情,热风吹落了一地繁花,沁脾芳香,灼雨滴打在脸上。胭脂谷,君落冷山,觅却无踪。
我赠你一场盛世,幻化成空。
寒露,鸿雁来宾,胭脂国。
到了季秋,便是胭脂国最清静的时候,高楼上有人抱着琵琶弹唱,我按拍寻步,不觉悠然。这个秋日不一般,城门外聚齐了三千雄兵,那男子御马而来,在我眼前停驻。
“织梦娘?”
我不喜欢这颐指气使的高度,逃开了他的追问。
“你不问我如今天下谁姓么?”
我不问,因为我已经知道。如今天下姓卫,卫膺的天下。
身后的声音又追随过来,男子说:“如今这是我的天下,你逃到何处都是一样。”我回转身躯,错愕地看着他。并不难认,传说里的卫膺额头有一枚痣,逆天的痣。这就是逆天而行的霸主,十年灭八国,统天下,眉宇间都是龙气。
英挺的男子迎风下马,就在此处的胭脂香里,他说想要一个梦。
我将丝帛覆他周身,他呼吸平缓,看着我,缓缓笑。我不与理会,淡淡问:“卫膺,你想要什么梦?”
“卫嫣然。”
他轻巧说,却不像景阳君那般执著。又是卫嫣然,即便你已经统一了天下,卫嫣然依然杳无音信。为她一人征遍八国,生灵涂炭,究竟是爱女情深还是残暴无度?我问他,他不答,已经沉沉入眠。
此刻,他应站立在桃花间,绵绵细雨,润物无声。她手持绸伞,锦帕遮面。她叫他父皇,他叫她嫣然,相亲,相爱。
我拉动木片,千丝万缕穿梭其间,卫膺睁开眼睛,起身,朝我笑。
“你还小,未必能知道。”
我还小,可我知道一个女孩不该背负如此沉重的宿命,这并非真情。
“这世上……真的有卫嫣然吗?”
并非无凭无据,早先我已窥视了景阳君的梦。十年前,梦境里是一个沾血的襁褓,正是那具婴孩的尸体惹来事端。无所谓染指,这都是你卫膺的一封战书、一个局。人人都觉得我还小,不应懂这些事故、阴谋。
“卫膺,你是个残酷的人。让一个莫须有的孩子背负你的狼子野心。”我的眼神坚定,卫膺这样的男子居然都微微颤抖起来。
“小织娘,你叫什么名字?”他忽然问。
我想了很久,人人都叫我织梦娘,我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我摇摇头,卫膺忽然心情大好,伸手抚摸我的头发。我急忙躲开。
“我赐你一个名字,”他说,“卫嫣然。”
“我不是卫嫣然。”我反驳,可是微乎其微,城门外有精兵围困,胭脂小国甚至没有自己的兵力。我们太弱小,只能任人鱼肉。
我被卫膺带到卫国,此处盛世井然,身披珠花霞帔,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唤我公主,我不知道如何回应。卫嫣然是他争霸的借口,而如今大局已定,他要给天下一个交代,他找到了我。
高高在上,我成了众矢之的。
大雪,鴠鸟不鸣,卫国。
卫膺治国有方,很快那些残忍的往事都变成了赞歌,我想不到转变会这样快。他对我更几乎是溺爱,把天下所有珍宝都送到我的面前。
“小织娘,会冷吗?”
正值冬日,卫膺为我烧红木取暖。可我还是冷。
在此处,人人敬我而远之,我是他们兄弟姐妹惨死的祸因,我是高不可攀之人。动了我的人必遭卫膺报复,谣言传散得极快,卫嫣然三个字是宫中最大的禁忌。
我承担不起这样大的罪孽,卫膺,放过我。
“我想回胭脂国,好想。”我说。
卫膺说:“你若跨出宫殿一步,胭脂国将焚化殆尽,不留一条性命。”
他好执着、好残酷。每日每日他都把我带到群臣面前,叫我嫣然,只有在人前他才会叫我嫣然,那个仿佛恩赐的名字。
我颔首,我不是嫣然。
八位国主都死了,我是最后知道他深情表面下暴欲的人,他不会放过我。
一日,我从冷宫找到了三尺白绫,白绫如雪,耀目得很。我把它挂在枝头,东南闻香梅,西北望月色,我觉得身体渐凉,四周的寒风如同细微的虫子,渐渐钻入我皮肤。然后一把长剑过眸,割断了白绫,我的身子摇摇坠落。
忽然得了一股暖意,是卫膺接住了我,我看到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有了泪痕,不可思议。
卫膺,你怎么会哭?
你应是无情之人。
我上吊的后几个月,卫膺一直伴我身周,悉心照料。而冷宫看守白绫的太监和服侍我的宫女共三十三人将被凌迟处死,我祈求他住手,但是卫膺拒绝,他要我知道我逃离他的代价,三十三条人命。
你怎能如此决绝。
我不服输,在长生殿跪了三天三夜。那正是大风大雪,最严酷的季节,我双腿冰冷毫无知觉,膝盖上肿其了血块。卫膺第一次向我退让,免了那三十三人的罪。我不成人形,但是却从未如此得意。
卫膺看着我咳嗽流涕又洋洋得意的模样,露出了好看的笑。
“好倔的小织娘。”他摸我的头。
这次我重病在身,无法躲开。
卫膺要一出戏:他扮演盛世明君,我扮演绝世公主。我想既然我不能逃走,那至少帮他完成这场戏。时间蹉跎,岁月不再,我要学会随遇而安。
在后宫,我架起了织机,开始为宫人织梦。有人想要心仪之人的青睐,有人想要家财万贯,有人想要童年韶光,即使知道这是南柯一梦,人们还是乐此不疲。我开始和人有了交集,在宫内,并不像以往那样孤独。
渐渐,他们叫我嫣然公主,不再是红颜祸水,我把自己当作了卫嫣然,得到万民爱戴,仿佛名正言顺。我心中也有了她的愧疚,八国惨剧的负罪感,于是,我比卫膺的谏臣更热心时事,常常与他为一道皇命争执不休,
“小织娘,你越来越有公主的样子了。”卫膺叹气,无可奈何。
“承蒙父皇圣恩。”我浅笑,摆架回我的寝宫。我与他从来都是很淡很淡,除了国事只剩下只言片语。
谷雨,萍始生,卫国。
又是春来到,卫国一派欣欣向荣,我倚靠朱栏,看都城热闹非凡。鼓起勇气,我又一次向卫膺请求。
“我想回胭脂国看看。”
“我想回去看看,父皇。”
“就一日。”
这次他额外地点了头,我兴致高昂地带着宫女太监来到了这片香溢国土,琵琶语未变,一切都如初,我跨进自己的小屋,织机也未变。
微风刚过,一个女子走过来,脸上蒙着帕子。她说她叫祯墨,等我很久了。
很久,原来我已经离开这里这么久。我已然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年岁朝代,但是我还是愿意为他们织梦。
她朝我走来,向我讨一个梦。我点头,抱之微笑,摆好器械让她躺下。宫女笑她,因为她脸上有无数刀疤。
“祯墨,你想要什么样的梦?”我问。
“卫嫣然。”她说。
我的手微微一颤,侍女们却调笑开了,想见公主见便是了,还做什么梦?天大的笑话。可这是笑话还是灾难,我至今不知。我选了丝线,为她铺好,机杼咯咯作响。
十几年前,卫国还不成气候,将军府邸亦质朴不奢。她坐在堂前,刀疤从脸上脱落,那刀疤下面,是一张倾国倾城的美貌。
卫膺叫她嫣然,嫣然浅笑颔首,面带桃花。
“嫣然是个好名字,”卫膺说,“将来让女儿也叫嫣然。”
后一年春,她身怀六甲与景阳君私奔,弱国的将军强国的帝王,嫣然选了后者,从此她不再姓卫。卫膺默不作声,只求还他骨肉。在当时,这个笑话流传于天下。满月宴上,八国君主欺他无权,作弄小嫣然,最后惨死于襁褓。
祯墨的梦境延绵,久久不散。直到夜深,宫人皆散去了,她才醒来。她握过我的手,泪流满面。我并不同情这个女子,我看着她满是伤痕的脸,她不是嫣然,我也不是嫣然,我俩心照不宣。
嫣然为母有愧,愿自毁容颜。她含糊着语言,迈出矮墙,倒在一片雪白之间,摇摇晃晃又走了几步,再往前,就是胭脂山谷的方向。
我明明知道,却不作阻拦。那夜莫名飘起了白雪,覆盖了整个胭脂国。我想阳春、白雪必定都有其因果。
“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欢,未免萦方寸。腊后花期知渐近,,寒梅已作东风信。”
这时候已鸡鸣欲曙,我念了前人的词。胭脂国城门早早地打开了,金碧辉煌,卫膺亲自来接我,他离开侍卫,独自走到我身边。
他说:“一日已到,公主应当言而有信。”
今时当日,百姓不再受欺压,天佑苍生,你是治世明君,我是盛世公主。
“父皇。”我亲昵地挽起他满是老茧的手,叫他父皇。他忽然不再说话,紧握住我的手。
“嫣然。”即使四下无人,他也不再叫我小织娘。
天下姓卫,多好的梦幻。
芒种,反舌无声,阴阳关。
我摆动机杼,繁花布匹里的婴孩朝我甜甜地笑,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我替人织梦,常常太入迷,不小心,便走进了他人的人生。
“这样便可以了么?”
我把布匹从她身上取走,那孩子微微动弹了下身子,点点头,煞是可爱。前方出现几个飘摇的身影,恍恍惚惚朝此处走来。
“你遗愿已断,请即刻上路。”孩童从织机里爬出来,轻轻抚摸我的脸。她太小还不会说话,然而却有一个缜密的梦境。
还记得是春分的时候,景阳君派人诡秘来到胭脂山谷,待我去看,那里有了一座无字碑,她灵魂未灭,求我给她一个梦。她浅浅朝我笑。一瞬间,殷红了桃,碧翠了柳。
我答应了,因为我好奇一个满月的婴孩会想要什么梦。
“我要取我性命的之人陪葬在胭脂山谷,我要我父制霸天下,所向披靡。”我见她清澈的眼眸里如此说。这孩子有旷世的恨,那恨已经入了骨髓。
嫣然的梦里八国之君胆小如鼠、皆难逃制裁,卫膺神勇无敌,统一天下,我想卫膺应是一个英雄,可惜无用武之地。
“嫣然,我送你到阴阳关,此后阴阳两隔,你好自为之。”我捏住她的小手,她浅笑如桃花,随即化作一股青烟。
“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悟身外身。”我念了黄山谷的句子,前方是漫漫无垠的泥土。
(2)
我不知道为何人人都想要梦,明明知道那华而不实、虚无缥缈。
我是织梦娘,却没有自己的梦,我常把自己送入他人的梦中。这梦中的一切如昙花也如人生。时而,我倒羡慕嫣然,羡慕胭脂国外头的那些人间烟火。
===================
处暑,鹰乃祭鸟,卫国。
风雨飘摇,燥热的气弥漫在潮湿的街,此处不比梦中富裕,甚至破旧不堪。我背着承重的行囊来到卫国,怀中揣着嫣然的牌位。我想我应找到卫膺,将嫣然还他。
我问路人将军府在何处,路人不屑地给我指出一条小路。
我沿路寻去,一块匾额赫然醒目。将军府,无人看守。我打开朱门,传来恶臭,里面蛛网密布,楼阁失修,而堂中坐着一个人,年已耄耋。
“请问,卫膺可是住在这里?”
他不答,看着兵书没有动响,久久才起身为自己沏一壶茶。
他的额头,有一颗痣,不是灭天的痣,极其平凡,甚至庸俗。
我缓步进去,轻轻把牌位放下,他有些惊慌,见我离去了又转头看牌位上的文字,眼眉挣扎,却是花了很久都未看清。
那夜我并未在卫国逗留,夜朗星稀,我驾马回了胭脂。
离去前,卫人告诉我那是卫国开国来最懦弱的将军,因为如今是太平盛世,久无战事,所以他迟迟不退,他的妻儿被景阳君强行劫走他都不敢吭声一句。
这是个笑话,流传于人世。
我终于知道何人人都想要梦,明明知道那华而不实,虚无缥缈,却还想要,倾其生命地想要。
这世间应是如此。
长安客
洛阳的人说赵长安是天下第一的画匠。将画作嵌入人体的肌肤的幻术,即使痛苦血腥,我却仍然痴迷。忘记了何年何月遇见的他,我只求他教我那样本事,月色下他眉目间有了迷幻的笑,似阴转晴。
我教你纹绘,作为回报,你要给我天底下最好的绘作。他说。
我疑惑望他,无法言语。
只有天下第一的画匠才能做出天下第一的纹绘,只有赵长安才是天下第一的画匠。我心念,却不愿把这没骨气的想法传达给他。
第二年,赵长安收了我做入室弟子。
第三年,赵长安潜心授教,少有新作。
第五年,绘刀不慎刺入他的胸腔,毙命,享年三十六。
那是一个春分,洛阳城里为此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
一入夏,雨意又肆虐起来。
今日起,我继承了赵长安的衣钵,便也要承担他的工作。我在这场雨中等待,等待一位少有的贵宾。成家的财富地位足以让任何人迎在雨中。我已经忘了等了多久,直到沉重的车马声响几乎响彻整个洛阳,那人下了车马,浅笑着。
我依稀记得当时他的手上握着鲜红如血的栀子花。
我说赵长安已经死了。
他的瞳孔忽然一收,打量我。我抬头望他,他则立即回避了我的目光,除了那一身绫罗绸缎,除了那一片奇珍异宝,除了那一瓣诡艳鲜红,蕴着媚色的眸子中的空洞透示着他的一无所有。
你是如今天下第一的画匠吗?他问我。
我摇头。
成玉不满我的回答挥袖而去。
第二天清晨时刻,柴门间有了些响声,是成玉独自来到我的偏厅。他身披朝露,从袖口里抽出一副图交给我,图里是一株极其艳丽的栀子花,就如同他手上的那一朵一样。他要我把花朵纹在他左肩,我没有与他多讲,淡淡取出了绘具。
栀子花惨厉地绽开着,凄凉地吸取他背上微弱的起伏。他的嘴角没有丝毫弧度,但他的眼神却是在微笑,精美到极限的微笑。
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吴楚楚。
你是女孩子?!成玉公子不置信的表情回映在我瞳中。他不顾疼痛迅速起身,望我许久,终于又露出初到此处的浅笑。我穿着粗布衣物,头发梳成男孩模样,人生头一次觉得羞涩,当时我只觉得那笑容好看,接下来的几日,成玉见我就笑,他说我一个人在这里一定会寂寞,不如和他一起回成府。
我知道那都是他的轻薄戏弄之词,可每次我的脸都变得滚烫。
完成纹绘的那一天,车马又像当初一样沉重地回响整个洛阳。我没有不舍,就同成玉一样。他依旧绝代风华,离去的时候所有邻家女子都争相出来见他,成玉不留眷恋地上车,没再提起过一起回成府的事。
我准备目送他去的那一刻,看到他伸出的手,忽而一朵鲜红落到我头上。是他时刻拿在手中的栀子花。
成玉把花留了下来,而他带走的那幅花绘是我做过最美的作品,和他的身体相得益彰。
===================
一直到又一年的夏季,蔓延着潮湿而炎热的空气的夏季,远处传来成三公子暴毙的消息,我忽然觉得头重脚轻。
那天起,我再也画不出像样的东西,荒废了赵长安教授我的技艺,只是重复地制作颜料。很快我的院子就空旷起来,无比悲哀。
人们都说天下第一的画匠走了,如今再也没有天下第一。
正是那段日子里,我闲闷地在街上游晃,目睹一个老人被一群少年欺侮,我看见被我救的老人左肩上模糊映出奇异的花纹,虽然已经磨乱,他的皮肤也褶皱难看,但那艳得蛊惑人心的颜彩同经脉不允许我怀疑。
成玉?
我的声音几乎颤抖,他不可思议地凝视着我,我努力地回想我记忆里他年轻的模样,与他如今的落魄重合,他不理会我的叫喊,拔腿就跑,可他的身子却着实像老了三十年一般,无法灵敏,我轻易拦住了他的去路。
他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只是由身子一天比一天更加衰老。我见他的模样只觉得伤心,全洛阳最好的大夫也无能为力,按他的话说,天下百病都是有所治的,唯独苍老无药可医。
可他今年才十八,应该是骄阳韶光。
那些日子,成玉总是独自看花,我不愿打扰他便独自到郊外采集花朵制作颜料。沿途街市里吵吵闹闹,原来是妇人们正围着皇榜议论纷纷,有个少年心狠手辣,杀了第一夫人不说更是扒了她的皮。
我顿觉悚然。
冬至,洛阳下了一场暴雪,他的皮肤忽然变得黄脆,四肢也扭曲了起来。他的手在我手心化作光斑,潋滟如初,他浑身散发微弱的光芒直到死前一刻,苍老的身子忽然又饱和起来,变成了十八岁公子的模样。
我抚摸着他的脸庞,却再也听不见他的戏谑。
楚楚,不要哭,如有来世我一定对你好。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原来他也知道自己对我不够好。
成玉的尸骨未寒,偏厅里忽然有了动静。刚跨进厅堂,一个浑身沾血的少年卧在地上,我定睛一看,不禁倒退了几步,他就是被重金通缉的少年。与画像上不同,他浑身泥泞,手臂上开了一道道巨大的口子。
姐姐,求求你救救我。
吴鹭见到我便哭起来,我实在不忍心看到这一幕幕,便为他清洗了手脚,包扎伤口,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银两,让他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
吴鹭噗通一声跪倒在地,紧紧抓住我的衣袖不肯放弃,膝盖的伤口血流不止,我赶紧扶他起身。
“我没有别的亲人,自小被第一夫人收养。那日夫人本该在梳妆,却久久不见人影,我也太唐突,冲进门,夫人浑身是血地趟在地上,她手里拿着一把尖刀一张皮,看清了些,居然是一张人皮!我吓得浑身发软。”
夫人竟是自己将皮割了下来,最后疼痛致死。
说到这里,吴鹭咽了咽,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
“姐姐,我已经无处可去,你收留我吧?”
他的话我全都信了,成玉一走我的心也随之空了一半,鬼使神差地,我点了头。这让吴鹭喜出望外,奔奔跳跳地进在屋子里打转。
“我从小就想要一个姐姐,楚楚姑娘我对你一见如故,从今以后你做是我的姐姐可好……”
我没答他,他便自己叫起姐姐来,兴致高昂。可那兴致在进了内屋的时候戛然而止。我险些忘了,成玉的尸体还躺在那里,吴鹭的脸上流露出了复杂的表情。又惊恐又意外。
“你怕吗?”我问他。可爱小的脑袋剧烈地摇动起来。
第二日,他帮我将成玉的遗体入土,我告诉他今时不同往日,我再能绘图,独自生活都相当窘迫。如果哪日我没能力养他了,他还是要另觅生路。
吴鹭努力点头,紧紧抓住我的衣袖不肯放。
我想这世间的事情总是难测,命里有时终须有。
===================
吴鹭来的第二月,有个叫西辰的青楼女子来找我,那女子美艳动人,前一年艳满洛阳,只可惜这世道花无百日红,三个月前被人摘了牌子,如今花容虽在艳色全无。她求我为她绘一只孔雀在她腿上。我无能为力,推辞说颜料用尽了,她面露绝望。
这时候吴鹭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锦盒,我不喜欢他这样古灵精怪的样子,却也无力再做推托。
移开盒子,一股浓香就扑鼻而来。仿佛是逝去的岁月又回到这个屋子,我依稀能见到赵长安宛然模样。
那日,我为西辰姑娘绘了一只孔雀,那只孔雀活灵活现,绝不亚于当年我为成玉绘的花朵。我望着那盒诡异的颜料,心里不知什么滋味。
“吴鹭,这是哪里弄来的?”
他没回答我,反而是喜悦地拉住我的手。
“姐姐又能画画了!姐姐又能画了!”一遍一遍叫喊着。
“这样一来姐姐就能和吴鹭永远在一起了吧?”他问我。
他说得没错。我的纹绘让西辰重登花魁,她赏了重金给我,从此在青楼间有了起死回生吴楚楚的名号,不光是青楼,各家名流达人也都纷纷上门拜访。一时间,这小院子又恢复了当年赵长安在时候的情景。
锦盒的分量越来越轻,香气逐减,然而过不了多久又会满溢出来。我猜是吴鹭在作祟,就躲在帷幕之后见他偷偷地将颜料加了进去,第二夜他又独自去了郊外。
所谓的郊外,却是成玉的墓地。
吴鹭把成玉的遗骨偷出来,磨碎混在颜料中。他像个鬼魅一般完成那些动作,一边是成玉破碎不堪的遗骨。
我把他拽起来,狠狠摔在石上,争执里我用刀具划伤了他的脸,接下来是长久的宁静,一双明亮的眸子惊慌地望着我。
“我只是想和姐姐在一起。”
“我不是你姐姐,你这个妖孽……”
我心疼地抱着成玉的尸骨,泣不成声:“我是妖孽,那你手中抱着的是什么呢?”
成家本没有三公子,成玉是一株赵长安绘给成夫人背上的栀子花,成夫人喜爱他人形模样便收他做了义子,后来成夫人驾鹤西归,他便迅速苍老,成老爷不愿见到这人不人妖不妖的东西,就把他逐出家门,对外说是成玉公子暴毙。
他是一朵花,生前怒放,生后寂寞。我在为他纹花的时候就知道了,他带来的那幅画就是他自己的原型。可那又怎样?我依旧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个风流公子。
“我只是想和姐姐在一起。”吴鹭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传说中花妖骨最上层的材料,历经人世沧桑七情六欲的花精死后将其花瓣磨成粉,更能制出绝佳的颜料。吴鹭说,这朵花妖生前动过情,所以才能绘出这么美丽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