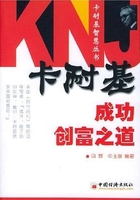骨骨为什么一看到自己就躲起来呢,难道他真如学长所说,会是嗜血的恶魔吗?染诺想到初见时,骨骨那清澈如水的眼神,那么的纯真。他高兴的时候,还会让她用手指碰触他头上可爱的粉色小犄角。
“骨骨,骨骨,为什么你头上会有这么可爱的一个角,为什么我没有,爸爸妈妈也没有呢?”小小的她用稚嫩的童音问他。
“因为小诺和爸妈是人类啊。骨骨是一个亡灵呢。”不管她问什么样的问题,他都是温和包容的,微笑着回答她。
虽然渐渐成长后,为了逃避人类奇怪的眼神,骨骨会一年四季戴着不同的帽子遮挡头顶的小犄角,但他仍然那样的温和,眼神清澈,笑容干净得像三月的阳光一样温暖。
怎么也难忘他晚上守在她的床边看她时的眼神……
望着空空的茑尾花田,染诺的心脏隐隐地疼了起来。
◎ 8 性情大变的奇洲学长
月亮升上半空时,染诺偷偷地从家中跑了出来。凭着记忆的模糊印象,她一个人来到奇洲学长的森林古堡,红过古堡,来到鸢尾花田。
“骨骨,骨骨,你在吗?我是小诺。”她小声地在花田里呼喊。
突然她感觉海岸边站着静静地伫立一个人影,头微向下垂,身体奇怪的僵直着。
“骨骨?”染诺小心地走近。
人影回转身来,却是奇洲。
这时的奇洲表情很是奇怪,他眼睛微闭着,长长的几绺头发随着半垂的头半覆在眼前,他的嘴唇紧抿着。他穿着一件奇怪的披风,头顶上的两只尖尖的长耳朵,像是仿真玩具。
“学长?”染诺小声地喊,全身忽然生出彻骨的寒冷。
眼前的人猛得睁开双眼,像一道生冷的闪电,划破鸢尾花田的夜,成片的鸢尾花刹时传出奇怪的呜咽声,他的嘴角浮起一抹邪魅的笑,长长的指甲飞快地刺到梁诺面前。
“不要杀害她!她是染诺!!”
随着突然的声音,一个人猛得从身后冲了过来,将染诺扑倒在地。
僵硬的学长微微一怔,像是一个灵活的机器瞬间略微迟钝了下,立刻又恢复了运作。尖刺的指甲再次向倒地的两个人划了过来。
“学长!!”染诺惊恐地喊叫出声,长长的指甲已到了眼前,再次迟钝了下。
“学长!学长!”染诺继续喊叫着。奇洲的动作越来越缓,随着染诺激动的喊叫,他眼中银白色的光芒也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直至完全柔和起来,手中的指甲也渐渐地缩回。
啪地一声,奇洲一头栽倒在茑尾花丛里。
将奇洲扶回他的古堡,染诺与骨骨守在他的床边,看着他像婴儿一般沉沉入睡,他头顶的猫耳也完全消失不见。
“骨骨,学长为什么会这样?这些天你怎么会无故消失……”染诺一肚子的疑问。
“对不起,小诺,让你担心了。”骨骨用手摸摸她的脸,还是那样的温柔,他缓缓地说出了这些天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自从城里发生第一件极度残忍的杀人事件后,通过报道所示死者伤口,骨骨身为亡灵异族,察觉到不可能是人类所为,于是他秘密进行了侦查,最后怀疑到优秀神秘的奇洲少爷身上。
果不出他所料,他查到那些死者均是被奇洲所杀。可是当他想设法拯救时,却被奇洲发现了,将他囚困在鸢尾花的画中,前不久才逃了出来,却一直找不到对付奇洲强大的力量的方法。
正说着,奇洲的眉头微蹙了下。
“他快醒来了,我藏下,以免刺激他。”骨骨迅速躲了起来。
奇洲醒来了,一眼看到身边怯生生地望着他的染诺,奇怪地问:“小诺,这么晚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 9 消失于掌心的茑尾花田
“骨骨,学长好像一点都不记得昨晚上发生的事情呢。”染诺满腹疑问。
“是的,猫耳变异的生灵,他的身体是隐藏着两种人格的,一个是完美的天使,一个是嗜血的恶魔。”骨骨说。
“那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帮助学长吗?”
“刚刚变异的族类,可以注射疫苗以防止恶性灵魂的生长。可是对于已经拥有强大力量的变异族来说,暂时世界上还没有想到对付的办法。”骨骨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一半天使一半恶魔?
学长英俊的脸在眼前挥散不去,染诺的心也跟着一点点的沉了下来。学院运动场外那个美好的吻,这些日子以来他安定的怀抱……都是让她心痛的源头。
学长,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你。染诺的心底响起一个坚定的声音。
染诺依然常常去古堡里看奇洲,在骨骨的悄悄陪同下。夜晚他们仍然守在他的旁边,当奇洲的恶性人格开始生长时,染诺在一旁抱着他,直到他僵硬的身体渐渐地柔软。
“骨骨,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你是学长喜欢的你,只有你的声音才能唤醒他身体那个善良的灵魂。”骨骨看着她的眼神有些心疼。
染诺的心里一怔,她想起自己曾经对奇洲学长的追逐,以及问他的话。而现在,每次他都在善恶两个人格激烈斗争后沉沉睡去,醒来后都脆弱无辜得像个孩子。
“小诺——”他叫她,欲言又止,忧伤的眼里分明有着对自己状态的预知。
每次当他紧紧地抱住她的时候,染诺感觉自己的心都碎了。
凶杀案不可避免地持续发生着,紫鸢尾依然越开越鲜艳。骨骨说,因为那些死者的血液,鸢尾才会盛开得如此妖娆。
她搂抱着他的脑袋坐在鸢尾花丛中,感觉到他蓝色的眼泪一颗颗地滴落在花丛里了。
每一滴泪落下去,一小片的鸢尾花便瞬间枯萎……她到底还是听了骨骨的话,将最新研发的清除疫苗悄悄地注入了奇洲的体内。
当输液进入他身体的那刻,她知道他感觉到了,却闭上了双眼,乖乖地在她的怀里。
翌日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依然是骨骨温暖的笑脸。阳光灿烂,街道车水马龙,仿佛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
全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城郊的森林古堡一夕之间消失不见。
只是每当黄昏的时候,染诺感觉到自己的左心房好像空了又空,梦里总有一大片的鸢尾花田。
粉色信封事件
天是蓝的,花朵是栀子白的。姑娘我十七岁粉嫩貌美,站在这鲜花旁,也算是相得益彰吧。唯一遗憾的是站在我对面、手里拿着粉色红信封的不是个传说中的美少年,而是一个硕大的胖子。
他胖还好,关键是他又胖又黑,我们站在一起一对比,落在众人眼中就跟那黑白无常似的。
于是请原谅我做为一个年轻姑娘的小小虚荣,我很难为情地拒绝了他递过来的小信封,特小心地婉拒他,生怕伤害了他的自尊:“那个同、同学,现在我们还是高中生,正是学习的紧要阶段,我、我我不想……”
我开始从宏观的人生理想政治方向试图引导他,可是他的脸红了,在我说了一大堆后,继续将信封推给我,“其实我是想……”
“哎呀,你其实是想跟我做朋友对不对?我知道啦!”
这小子,不吃软的,我怒了,干脆自毁形象双手叉腰地朝他怒吼:“大胖子,思想有多远你就离我多远,我不喜欢你啦,你最好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50米以内……”
小胖子果然给唬住了,乖乖地逃离了河东狮吼的现场。
不过在他转身后,却做了一个让我大跌眼镜的举动,将粉色的信封交给了我们班的班草。班草还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还是谢谢你,这不怪你。”
难道?难道是班草暗恋我已久,于是派了大胖子做他的爱情信使。
OH,MY GOD!难道我就这样扼杀了一段比《初雪》更唯美比《蓝色大门》更纯情美好的初恋情缘么?
我懊悔地直想捶胸顿足。思索再三,决定下午放学后,勇敢地再去找胖子。
下午,我在校门口等到了他,咬咬牙鼓起勇气地跟他说,“今天真是对不起了,我是一时糊涂词不达意……”
“啊?”胖子愣了半刻,然后问,“你是答应帮陈昭(我们班草的名字)做试卷吗?”
“啊!”
然后胖子开始解释,今天拿的信封里除了一张写明来意的纸条,其它是钞票。我们的班草陈昭少年在有钱的老爸的威胁下要考取好成绩,可是凭他自己的实力根本不可能,于是就想着来找成绩优异而且据说家中困难的我。
顿时,我无语凝噎,真想从地上找块砖头将他们一下拍晕。
“那你们为什么偏找个粉红色信封。”我仍然不甘心地再次质疑。
“那个,是一时情急就顺手拿了某个女生给陈昭装情书的信封。
“……”
于是,这天光荣地成为了我十七岁时最屈辱的历史性事件。为此,我也忌恨了那个大胖子(即使他后来长高了,并瘦了、帅了)和陈昭许多年。
后来胖子帅哥问我,“我说你当时没有答应陈昭的请求也得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也对我们爱理不理的呢?”
我只能回以他一个超级大白眼。我能说,他们无意中破碎了一个十七岁少女的粉红色梦么,我能说么?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某天发现看过的某处风景不在了,喜欢的某个明星变老了,日记里曾含泪记下的心情释怀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在一寸寸流失,沧桑却点点成就,在眉宇间凝成了欲说还休的意境。
曾喜欢过的人,你能看到么?我们的青涩和痴狂在渐渐消失,转变成承受和淡定。
一个人的闲暇,喜欢站在阳台,张开手指举过头顶,任慵懒的阳光抚过指尖。如十指风寒的年华里偶然暖风过境,便感动得不能自已,甚至泪盈于睫。
搁在窗台上的手机在响,他又打电话来了。
任它执着地响着,硬是不接听。波动了几年的心跳,此刻风吹无澜。
我们都明白,有些故事一转身便会有转机,关键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转身的力气。既然已失了开始,何不让它继续残了结局?
我还清晰地记得站在香樟繁茂的宿舍窗台,看着他经过时朝气蓬勃的样子;记得自己路过篮球场假装不经意地向他惊鸿一瞥时,心潮的激烈起伏……那些场景都曾是最美最心碎的过往。
可是那些心情再也找不回来了,如今的我更明白相见不如怀念这个句子的含义,想最初写下这几个字的人,有过怎样的失落才会有此切肤的感触。
所幸,闺蜜夺爱,那最恶俗的情节,最疼痛的疼痛,唯有自己独自承受的心伤,也跟着消失不见了。
他给我邮许美静珍藏版的碟,可是他不知道,我依然爱着那个女子,却很少再听她的声音。成长教会了我们生活,而生活里许美静少听为宜。
她唱: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可是关于她为爱的颠狂,留于世人只是闲余谈资。我至爱那样的歌心疼这样的她,却会常常给自己警醒,不能成为那样的她。
就像,我怜惜昨日里为了你要死要活酗酒咆哮哭泣自残的自己,却在今日的心底暗暗发誓绝不重蹈覆辙,要做崭新的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此时便要感谢你,给予了我那些伤害,才有了今时我强大的内心。我们的故事随岁月渐渐流淡的同时,各自也将拥有新的开始。
听无若蓝唱《绿袖子》:你送的鸢尾花早已经枯了,你教的那首歌我学会弹了……歌里不再有你了,你还在回忆住着……
感觉忧伤着,却美好着。
手机铃声终于停止响动,转身进房,第一眼触及的便是电脑旁硕大的盆装仙人球,这来自父亲周末的捎带。
曾经因为个性太冲太过相近,少年的我与父亲话不过三,语出必伤。后来去外地上学,偶尔的电话通联大多都是缄默。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他埋怨过后,我的歇斯底里哭泣和咆哮,我几乎是吼着讲出了这么多年心底的抑郁和压力,而他也在震惊之外第一次用开解的方式与我交流。
才明白,沟能的方式有很多,包括争吵。
这个月中,父亲挤出时间来到我的城市看我,呆了一晚,清晨他早早地起床,一个人走遍我居住和上班的周围场所。他没说,我亦明白,父女聚少离多这么多年,他只是想感受下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生活的环境。
他离开前的那几个小时,与我闲聊家中的琐事,人情事故,像年老的奶奶,将一些细节再三重复。看到他暗沉的皮肤上展开的笑纹,竟有了几分慈爱的味道……
我知道父亲是真的开始老了,曾经的暴躁锐气坏暴躁正在一点点消失,我的尖锐和叛逆也被他生出的慈爱一点点磨掉,即使我们不能彻底改掉自己那过份的自尊,即使依然有分歧和争吵,可喜的是,我终究明白了,世事充满变数,再没有什么是比亲情更贴近心脏、可靠安全。
一个人,努力地工作,安静地思考。生活无惊无喜,亦很好。
身边的他,看上去相亲相爱,表现得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好,可是如人所说,那百分之一的便是致命的,往往只有当事人清楚。
打开电脑时,他挂着的Q上仍会有陌生女孩突然跳出的暖昧言语……
早已从震惊、心痛到淡定、麻木。
似乎是一种信仰,一直以为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过上最贴进圆满结局的童话生活。
直到成长,才顿悟,这种信仰即是童话里最纯真的部分。
他牵着我的手走过绿树成荫的大道,就连谈天激动时都忍不住当众将我抱起;他看我的双眼发着光,温暖的手小心翼翼地将我的脸捧起,动情地说出:看你在我面前笑,觉得自己真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美好如斯,不忍在心头将镜头回放。含泪说分开时,不愿却去与他对视。
最终抱头痛哭,分合反复得像上演欲擒故纵、没完没了的泡沫剧。
患得患失已玩腻,绝望是心中永远不败的烟火,周期性灼烧。请原谅我的悲观主义,一直过于清醒,看得也太过分明。还是相信《红豆》将沧桑道尽: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