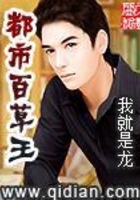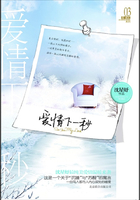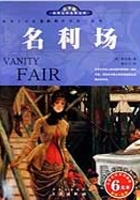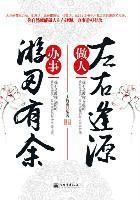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当追日的巨人夸父因饥渴而轰然倒地的一瞬,他尽最后的力,抛出手中的杖。那桃木杖划空而坠,深深地植入黄土地——长出一片桃林,为子孙解饥渴。
当我们的诗人杜甫历尽磨难,于一叶扁舟伏枕托孤之际,他油然记起了遥远的传说:“持危觅邓林。”邓林,那世世代代觅觅寻寻的桃树林啊选可潦倒的天才却没意识到他手中的桃竹杖也早已划空而过,化作文化史上另一片邓林——那星空般熠熠闪烁的一千四百多首杜诗,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选杜甫穴苑员圆—苑苑园雪,字子美,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远祖是晋代名将杜预,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光荣的家世增强了杜甫的家庭观念,“奉儒守官”的家教使杜甫对济世有执著的追求。结合其创作看,杜甫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安史之乱前穴苑员圆—苑缘缘雪,二是安史之乱发生后至入蜀前穴苑缘远—苑缘怨雪,三是入蜀后至死于由长沙到岳阳的途中穴苑远园—苑苑园雪。用杜诗来概括,前期是“赋诗分气象”,从盛唐汲取能量;中期是“忆在潼关诗兴多”,铁与血激荡起诗人浩荡的诗情;后期是“晚节渐于诗律细”,只手开拓诗国的一片新疆域。
千百年来,人们对杜诗的认识与评价,有一个深化的过程。首先,是认识到杜诗集古今诗歌之大成的意义,“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穴元稹《杜工部墓系铭》雪。元稹、白居易倡新乐府,也是从学习杜甫“缘事而发”、“借古题写时事”的形式入手。由于他们对杜诗内容现实性的关注,引发了人们对杜诗具有史的意义之认识。晚唐孟棨《本事诗》首称杜诗为“诗史”,而宋人对其内涵有更深刻的发露:“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穴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雪。此后,凡经乱离,人们都分外痛切地感受到杜诗这一“诗史”的特质。南宋李纲于此体会甚深刻:“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穴《重校正杜子美集序》雪。而王安石则注重其人格力量与伦理风范,《杜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妍丑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于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选”此后三种认识共存而因人、因事、因时代各有侧重。
然而集大成的杜诗是个多面体,只强调某一面,就容易片面。对“诗史”的误解便是显例。诗史非史诗,不是将史迹编年成诗,或将诗写得一似史传体,甚至要求句句与史实如合符契,“如下算子”。诗史者,诗而具史之特质也。中国文化又称“史官文化”,其认识基础是重经验,究天人之际而反思致用。它的深层,便是浓重的忧患意识。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心理。从根子上说,黄河流域那并不裕如的生存环境与“靠天吃饭”的农业活动,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的民族。《诗·载驰》所谓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易》所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反映的便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忧患心态。固然,举凡人类都会有忧患意识,但从此种意识引出的哲理之思,各民族却不尽相似。总体说来,忧患意识使我民族更执著于现实,更注重经验,形成一整套对个人与宇宙形式上的独特理解。方东美《中国形而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一文指出,中国本体论立论特色有二:“一方面深植根于现实界,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趋入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本着这种入世的超越精神,中国士大夫更多的不是向往那来生再世的幸福,或木乃伊、舍利子之类的“永恒”,而是立足于现世间,追求与自然融洽、化入历史的永恒,即“时间人”的永存。尤值得关注的是儒家价值观念所起的整合作用。《孟子·告子》有云: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将人生忧患与社会忧患、个体忧患与群体忧患结合起来思考,从而将忧患意识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规律这一层面来认识。于是忧患意识被视为士大夫必备的修养,由此将忧患意识化为个体人格内在的历史责任感。把握杜甫诗史特质的关键,舍此而焉求芽清人浦起龙于此别有会心。他在《读杜心解·目谱》中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在《读杜提纲》中又说杜:“慨世还是慨身”,“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浦氏已意识到,杜诗“史”的特质是以其个体人格伦理为内涵的,后人通过杜诗感受到的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透过诗人强烈的主观情志所显露的时代命运。因此,我们不但从“三吏三别”中感受到时代的巨痛,还从“独立苍茫自咏诗”的诗人那一举手一投足之间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三吏三别”是诗史,《秋兴八首》也是诗史,《咏怀古迹》《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江南逢李龟年》又何尝不是诗史芽或从时事中提取,或从经验中蒸馏,杜诗意象莫不给人强烈的现实感。更有一类是将堵积胸中的悲天悯人情怀一吐而出,化作超现实的意象,如《凤凰台》者,其意象正是“深植根于现实”而又“腾冲超拔”的儒学化境。溯其源流,当与诗史同出自那深沉的忧患意识。甚至作为杜诗标志的沉郁顿挫风格,也与忧患意识相表里。所谓沉郁,是屈骚的“心挂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是扬雄赋“经年锐积”的“沉郁之思”;是阮籍诗在寂寞中体验忧患人生的“情伤一时,心存百代”。杜甫上承历史多年积淀下来的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海纳了盛唐以壮阔为美的时代特征,而个人深入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又使之将忧患由“上感九庙焚”降及“下悯万民疮”。杜诗的沉郁因之具有更为广阔的基础,“由雅入俗”地横跨“雅文化”与“俗文化”,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杜诗之沉,不是阴沉;郁,不是悒郁;是清人浦起龙所谓的“一副血诚”,是萧涤非先生指出的“沉雄勃郁”。杜诗由是成为中国文化的某种浓缩,也因此而每当民族灾难降临之际,志士仁人总是要手书口吟杜诗。自抗金到反清,从深山隐士到海外游子,莫不如是,莫不如是选在这一意义上,杜甫是民族文化的第一提琴手,谓为中华文化之“托命人”并不为过。
事情往往会是这样:经过反复思量、比较、总结之后,我们竟然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惊讶地发现当初那简单的印象不但是鲜活的,而且是颇富直觉性的。真是禅宗话头所云:“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对杜诗的认识似乎也经历了这么个周期:以“集大成”、“子美集开诗世界”始,中经“诗史”,再到发掘其人格伦理意义之“诗圣”,进而发现“人民诗人”,终于又回到杜甫首先是一个诗人,其贡献首先是诗歌内容与形式之创造。我仿佛看到闻一多透过镜片正视着我们:“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芽”对《诗经》,我们首先要用诗的眼光读它;对杜诗,也应当首先用诗的眼光读它。
杜甫诗歌创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我只想讲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就是内容与形式相适应的追求史。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长期酝酿,无论民族融合、三教互渗、南北沟通,还是中外交流、个体对社会的参与等等方面,唐代社会生活空前丰富多彩。特别是安史之乱激发民族、阶级、宗教、文化诸多矛盾,使中央与地方、个体与社会、心灵与物质、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种种冲突尖锐化,其复杂程度也是前代所难以比拟的。新内容需要新形式。而文学自身的进程,至盛唐末期也成熟到一个“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境地。一切似乎已到了蛇不蜕皮便不能再生长的地步。文学史乃降大任于斯人——杜甫。
杜诗形式对内容的适应,大体有二类:“量体穿衣”与“量体裁衣”。所谓“量体穿衣”,我指的是根据内容选择合适的形式,就是萧先生《杜甫研究》所指出的:“使各种不同诗体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如用伸缩性较大而便于铺叙的古体诗来反映社会生活,用律诗来抒发个人感情。前者如《羌村三首》、《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后者如《春望》、《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有的学者还认为,杜诗中“歌”与“行”也是有分别的,“行”多反映时事与述志,“歌”多个人感慨云。杜甫各种体裁都能运用自如,的确是“集大成”者。然而更要紧的是,即使是旧形式的使用,也是充满杜甫的创造精神的,腾挪跳掷,不受其束缚。如杜甫喜用五古、七古作抒情长篇,以反映壮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抒发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五古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七古如《洗兵马》,无不抒情、叙事、议论并发,一泻千里。叙事带情以行,议论提起全篇精神,使得杜甫的抒情长篇波澜老成,前无古人。
所谓“量体裁衣”,就是根据内容需要改造旧形式或自创新形式。改造旧形式,杜甫往往由改变其功能入手,七律为显例。诚如萧先生《杜甫研究》所说:“杜甫以前,几乎没例外,七律一般都是用来作‘奉和’或‘应制’这类阿谀的官样诗体的,杜甫却大大扩充了七律的领域,往往用来感叹时事,批评现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演进。”可以说,七律到杜甫手中,才成为中国诗的重要体裁。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少陵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篇制多,一也;一题数首不尽,二也;好作拗体,三也;诗料无所不入,四也;好自标榜,即以诗入诗,五也。此皆诸家所无。其他作法之变,更难尽数。”其中“一题数首不尽”是指“连章体”,如《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连章”好比“拐子马”,将几首七律组合起来,每首都具有七律严整典丽之长,又能数首如一首,从不同角度表现同一主题,色阶丰富,灵活而又有整体组织,无排律之弊,有古体诗之长,是杜甫长期潜思实践的杰构选而自创音节,打破旧谱的“拗格律诗”,也有效地增强了律诗的表现力。至于本是“官样文章”的排律,杜甫也赋予新的功能,如《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偶题》、《清明》、《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等,可叙事,可抒情,可议论,成了杜甫手中的长枪大戟。而向来以短小空灵取胜的绝句,在杜甫手中或驱之发议论,或贯之成组诗,手法上则打破唐人熟见的第三句一转的格式,往往四句皆对偶,画面平列,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最具冲击力的改造与创新自当推其乐府歌行之作,“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是“量”新内容之体“裁”出的新形式。然而这种新题乐府比同代人写的任何旧题乐府都更贴近汉乐府之本质——“缘事而发”。客观的叙事,以时事入诗,是其生命之所在。它以典型的素材、逼真的描写、深沉的思考,使时事凝定为永恒而鲜活的历史瞬间。尤其是“三吏”“三别”,以组诗的多角度,全方位而多层面,深度地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在尖锐的冲突中展示人的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刻画了老妪老翁、新婚女子、应征少年诸色人等的形象,交织成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长卷,是中国式的史诗,历史而又超越历史,“直显出一时气运”选而且这种叙事精神在杜诗中泛开来,长如《咏怀五百字》,短如《三绝句》,律如《示獠奴阿段》等各种体裁,无不充满这种“缘事而发”的精神。
对诗歌语言的构建,是杜甫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就。文学语言之所以有余味,就在于能构建艺术之幻象,以象尽意,感发出读者整体直观的意会思维,通过在场者穴“直寻”来的“象”雪,逗出隐蔽者穴“意义整体”雪。自《文选》明确提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以来,语言的文学意味一直是作者的自觉追求。尤其在唐,唐人生活的诗化与语言的生活化互动,有力地促进了诗歌语言的构建。如杨炯《骢马》“夜玉装车轴,秋风铸马鞭”;李白《长相思》“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等,都是诗歌特有的语言。
杜诗的语言,更是一种创构情感意象的典型的诗语言。中国诗与直觉思维有着不解之缘,从来就不想离开这感性世界而去。杜甫用力处,也就在追求语言的感觉化,对个别事物的具体表达。“山豁何时断,江平不肯流”穴《陪王使君晦日泛江》雪。“不肯流”是诗人此时此地对“江平”的特殊感觉。杜甫用词下字总是尽量将词语的指称功能隐去,凸现其表现功能,使之感觉化。“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穴《滕王亭子》雪。“犹”、“自”二字,情景相因,诗人于安史乱世面对盛世遗物,自然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见于言外。“碧瓦初寒外”穴《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雪。无象无形之“初寒”,如何置诸有形有质的“碧瓦”之“外”芽仰视巍巍玄元寺,觉碧瓦之高,已超然乎充塞天地人间之寒气,则非下“外”字不可。此乃“逞于象,感于目,会于心”者也。
再看其字词的特殊组合形式。杜诗组词往往将景物与情志紧密结合到“化合”的程度。“影著啼猿树”穴《第五弟丰独在江左》雪,固然可释为:身羁峡内,每依于峡间之树,而峡间之树多著啼猿;但如此分解,“啼猿树”之意味又何在哉选“池要山简马,月静庾公楼”穴《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雪。马乃今日之马,楼乃今日之楼,却冠之以古人的名目,以名词做形容词,造成古今时空的交错,“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穴陈寅恪《读哀江南赋》语雪,于是主如庾公之雅兴,客如山简之风流如见。
与杜诗语言的情感性质相配套的是:以形象直接取代概念、推理、判断。“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穴《去蜀》雪。万事如何芽“已黄发”。读者自悟出“万事已休”的断语。残生又如何芽“随白鸥”。读者亦可悟出“漂泊无着”的断语。“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穴《暮春题肁西新赁草屋》雪。密集的意象间无一动词,只让意象的张力互相支撑,在对称中形成反差,互相补明意义。从这些富有个性的“句法”中,我们感触到杜甫自家的“逻辑”与“秩序”。
杜诗句法,是以情感生命之起伏为起伏的。其诗句极力追摹生命的节奏,让诗的律动与人的内在生命之律动同步合拍,由此焕发出诗美。将浓烈的情感注入格律,在森严的格律中从容地进行心理刻画,借助诗的律动追摹心理的律动、情感的律动,是杜诗独到之处。“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穴《放船》雪。由第一眼的印象到引起感受的情绪,再到理性的判断,不正是“意识流”所追求的效果芽“返照入江翻石壁”穴《返照》雪,似乎是在追踪客观事象的因果过程,却正与“不可久留豺虎乱”那忐忑心绪同一轨迹。“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穴《秋兴八首》雪。“倒装句”也罢,“以名词做形容词”也罢,“形容短语”也罢,总归诗人服从的是强烈的主观感受而不是语法规则。“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并非实事,只是驰想,“双动”用法与流水对使还乡之思迅疾如飞,体现了诗人当时心灵的节奏。“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穴《又呈吴郎》雪。入微的心理体验使读者体会到贫妇人的恐惧,也间接揣摸到吴郎插篱之用心,更感受到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一枝笔写出三人心理。
总而言之,深刻的人生体验是杜诗语言无与伦比表现力的根本。试读《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其三:
死去凭谁报芽归来始自怜。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杜诗镜铨》引张云:“脱险回思,情景逼真,只‘影静’、‘心苏’字,以前种种奔窜惊危之状,俱可想见。”只有经历过九死一生奔赴朝廷的人,眼中才有“影静”的感受。其背后有多少沦陷区“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的日日夜夜选可以说,杜甫创作的一大特色是:以深刻的人生体验来反映客体;或者说,他表现的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主体对客体的体验。吴乔《围炉诗话》云:学杜诗“须是范希文穴范仲淹雪专志于诗,又一生困穷乃得选”萧先生《杜甫诗选注·前言》引用这一则诗话,有深意在。
自接手杜诗选评这项工作以来,心中着实惶恐。有涤非师《杜甫诗选注》在,本可不作。但由于淡懿诚先生的坚持,也考虑到选评与选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还是有事可做,因勉为其难。本册子仍依据萧注本,选目有所增删,分期也由四期并为三期,注解也参考了他本,特别是海内外的新成果。只是自己明白:以我之浅陋,疏漏错误难免。还乞读者诸君哂正选为了行文简便,一些常用本用简称,详书后所附书目,而引萧注本就不一一注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