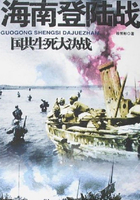青春热血的胡适之在北平大红大紫时,大他十多岁的鲁迅正在北平的绍兴会馆里抄古碑帖。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人,因为同在北平,因为都才高八斗,命中注定要走到一起。
其间的经过很简单,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回忆:“S(绍兴)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那时偶惑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文中提到的金心异其实是化名,真名叫钱玄同,鲁迅称他为“我的朋友”。他与钱玄同确实是老朋友,同赴日本留学,同为章太炎的弟子,两人的友谊长达三十年。这个过程后来被钱玄同总结为“头九年(1908—1916),尚疏;中十年(1917—1926),最密;后十年(1927—1936),极疏”。回国后,鲁迅受蔡元培之邀供职于教育部,钱玄同则在北大执教。两人同处北平,经常走动是免不了的。正巧此时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把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平。这份杂志进京后开始同人化,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都成了这份新生杂志的撰稿人。当时的《新青年》因为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陈独秀与胡适当之无愧地成为青年领袖,而鲁迅、周作人兄弟此时籍籍无名,或者说尚未显示出强劲的势头。那时,正如鲁迅后来自嘲:“不过敲敲边鼓而已。”
这一年的鲁迅已接近四十岁,正绝望于人生,更绝望于中国,生活在沉寂晦暗的阴影中,日子过得清苦又寂寞。那时候他就住在北平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除了去教育部上班,大半的时光便消磨在这间书屋里:抄古碑,看佛经,偶尔去一去琉璃厂搜寻汉砖及旧典籍,这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那时他还过着单身生活,与夫人朱安长期分居。而弟弟周作人正醉心于学术,因为谋生,兄弟俩才不得不集聚于京城,来往不多,对外界的风雨也知之甚少。只有老同学钱玄同偶尔会来看他。
这天晚上,两人便有了以下对话: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只是一个开始,是鲁迅文学创作的发端,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端。鲁迅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从《药》到《阿Q正传》,从《孔乙己》到《故乡》,一系列扛鼎之作一下子将鲁迅在万众瞩目的新文化平台上高高托举起来,一夜之间便成为新文化运动一员骁将——鲁迅的横空出世,就是胡适之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假如没有白话文的发起与推广,鲁迅可能终生蜗居在北平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这个阴暗幽深的老男人,这个墓气沉沉的老男人,以丰富的人生阅历、长久磨炼出的世故与深刻,洞若观火一般操一杆老枪,直抵中国积疴难愈的老病灶: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说鲁迅墓气沉沉,这个“墓”不是错别字,它既是坟墓的“墓”也是暮色的“暮”。暮气,或者说墓气,正是鲁迅身上浓得化不开的气息,他的人是如此,作品当然更是如此,充满枯藤老树昏鸦的悲凉,与陈独秀和胡适的朝气蓬勃与青春洋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做成新文化运动这个局,做局的目的就是要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中国人,把中国近代文化史沉沉大幕齐刷刷地扯开来,锣鼓铿锵中,让全新的一代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