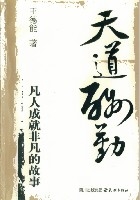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明儿别到河里冼脸去了,到我们这儿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阻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痛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若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大娘说;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抹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浅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占了北平,我彳门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展,我就到女孩子家]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巳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妹底广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柞坚实。女孩子说广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沬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实,问我能不能。他的忙。部队寬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邦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酮希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入背枣,我们妞儿足不合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扪做活了!又说:你们跑了決半月,赚了多少钱,你看,她来査帐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鲜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版下的一个小包袱广我们这叫包袱帐,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犹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够了。
够干什么了?太仂问。
够绐我买张识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左曲阳给我买架织亦机子回来吧无论姥婼、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当的耍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实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部用光了。我们分宕背了回来,麗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象要了几夼地,买冋一头牛;这象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知下这一盯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停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口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若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观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冏到百货公苘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兰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忙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步,有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觅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來!
他说妞儿巳经有两个孩子了,还象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这二年生活好些,却常常想起那几年的艰苦。那几年,我们在山地里,常常接到母亲求人写来的信。她听见我们吃树叶黑豆,穿不上棉衣,很是担心焦急。其实她哪里知道,我们冬天打一捆白草铺在炕上,把腿舒在祅袖里,同志们挤在一块,是睡的多么暧和!她也不知道,我们在那山沟里沙地上,采摘杨柳的嫩外,是多么热闹和忮活。这一切,老年人想象不来。总以为我们象度荒年一样,整天愁厄苦脸哩!
那几年吃的坏,穿的薄。工作的很起劲。先说抽烟吧,要老乡点兰花烟和上些芝麻叶,大家分头卷好,再请一位有把握的同志去擦洋火。大伙围起来,遮住风,为的是这唯一的火种不要被风吹灭。然后先有一个人小心興翼的抽着,大家就欢乐起来。要说是写文章,能找到一张白报纸,能找到一个墨水瓶,那就很满意了,可以坐在草堆上亏,也可以坐在河边石头上写。那年月,有的同志曾经为一个不漏水的墨水瓶红过脸吗?有过。这不算什么,要是象今天好墨水,车载斗璜,就不再会为一个空瓶子争吵关于行军:就不用说从阜平到王快镇那一段讨厌的砂石路,叫人进一步退半步;不用说雁北那趟不完的冷水小河,登不住的冰猾踏石,转不尽的阴山背后;就是两界峰的柿子,插箭岭的风雪,洪子店的豆腐,雁门关外的辣茭杂面,也使人留恋想念。还有会餐:半月以前就放猎神准备,事到临头,还得拼着一场疟子,情愿吃的上吐下泻,也得弄它个碗净锅干;哪怕吃过饭再去爬山呢!是谁摘过老乡的辣茭下饭,是谁用手榴弹爆炸河潭的小鱼?哪个小组集资买了一头蒜,哪个小组煮了狗肉火设宴席?
留在记忆里的生活,今天就是财宝。下面写的是在阜平三将台小村庄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其中都是宾人真事比较。
我们的机关搬到三将台,是个秋天,枣儿正红,芦苇正吐花。这是阜平东南一个小村庄,距离有名的大镇康家峪不过二里路。我们来了一群人,不管牛棚马圈全住上,当天就劈柴做饭,上山唱歌,一下就扣老乡生活在一块了。
那时我们很注意民运工作。由我去组织民校识字班,有男子组,有妇女组。且说妇女组,组织的很顺利,第一天开学就金到齐,规规矩矩,直到散学才走。可是第二天就都抱了孩子来,第三天就在课堂上纳起鞋底,捻起线来。
识字班的课程第一是唱歌,歌唱会了,剩下的对间就碰球。山沟的青年妇女们,碰起球来,宾是热烈,整个村子被欢笑声浮了起来。
我想得正规一下,不到九月,我就给她们上大课了。讲军民关系,讲抗日故宰,写了点名册,发了篇子。可是因为坐位不定,上了好几次课,我也没记淸谁叫什么。有一天,我翻着点名册,随便叫了一个名字:吳召儿!
我听见嗤的一声笑了。抬头一看,在人群末瑢,萊着一根杨木住子,站起一个女孩。她正在背后掩藏一件什么东西,好象是个假手榴弹,坐在一处的女孩子们望着她笑。她红着脸转过身来,笑着问我:念书吗?
对!你念念头一段,声音大点。大家注意!
她端正的立起来,两手捧着令,低下头去。我正要催她,她就念开了,书念的非常熟快动听。就是她这认寞的念书态度和声音,不知怎样一下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紧张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
十一另,老乡们波上羊皮衣,我们反扫荡了。我当了一个小组长,村长给我们分配了向导,指示了打游告的地势。别的组都集合起来出发了,我们的向导老不来。我在沙滩上转采转去,看看太阳就要下山,很是着急。
听说敌人已经到了平阳,到这个时候,就是大声呼喊也不容许。我跑到村匕家里去,找不见,回头又跑出来,才在山波上一家门口迂见他。村长散被着黑羊皮沃,世是跑妁呼哧呼哧,看见我就笑着说:男的分配完了,给你找了一个女的!
怎么搞的呀?村长!我急了,女的能办事吗!
能办亊!村长笑着,一样能完成任务,足一个女自卫队的队员广女的就女的吧,在哪里呀?我说。
就来,就来村长又跑进那大门里去。
一个女孩子跟着他跑出来。穿笞一件红棉祅,一个新鲜的白色挂包,斜在她的腰迅,装着三颗手榴弹。
离是,付长也在抱怨,这是反扫菡呀,又不足到区里验操,也要换换衣裳红的目标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