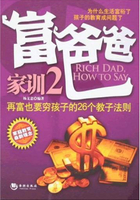大家知道,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会涉及到文学的物质基础及其思想文化背景,涉及到现在文学的生产机制和运行模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我着重要谈的还是当下文学的精神资源,当下中国作家的精神状态,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创作上的一些重要变化和创作中的重要缺失。这些问题都属于精神生态的范畴。
一、直面当代文学的不和谐音
最近,有记者问我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等言论的看法,还有的问我对于网上流行的“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中国作家已经死亡”、“中国评论家已经死亡”、“中国文学理论已经死亡”、“中国教授已经死亡”等十大死亡的看法。这被称为“垃圾论”和“死亡论”。顾彬的话后来有所澄清,但主要意思还是清楚的。问题都提得非常尖锐。我觉得下一个“悼词性”的整体否定的结论也许比较容易,而我更欣赏的是一种分析的态度,一种能就具体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态度。我希望尽可能多看原作,在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品性的基础上去下结论不迟。其实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不无合理的成分和某些严酷的真实,也涉及到了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的危机问题。去年七月,我发表过一篇叫《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的文章,谈的也是问题和危机:比如,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正面精神价值弘扬的缺失,精神超越性的弱化,原创性的缺失等等。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了,或者只剩几个诗人值得一提。比如,说《狼图腾》是宣扬法西斯主义,有没有道理呢?有一点道理,但失之简单化了。这本书的文化宣言部分破绽较多。我曾写过《〈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批评得也非常尖锐,认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还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没有上帝,人啊,是什么都可能做的。”指出滑向极端的危害性。因为书中认为中国的人种狼血太少了,羊血太多了,如果改换一下血液配方,让狼血多一点,转换成狼文化,中国人就厉害了,这当然是错的。但是,细读文本,又不能不承认,在生态层面和形象层面,它对“文革”期间的瞎指挥,粗暴的行政干涉对草原的破坏,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狼的团队精神和狡黠凶顽的野性方面的精彩描绘,富于原创性,能带来一些震惊化和陌生化的效果。这也是它吸引很多读者包括外国读者的原因。今天我们讲精神生态,也并不是要下个什么样的结论,而是分析今天中国文学所面临的问题。近来文坛上比较热闹,出了不少花边新闻,什么裸诵、乞讨、梨花体之类,让人看了遗憾甚至悲哀。但要看到,大部分中国作家还是心存神圣的,在自尊地、艰苦地、大胆地探索着,辛勤地创作着,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收获。
我特别注意到,胡总书记报告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才是站在世界和全球的高度上看问题,不是那种老是局囿在国内的眼光。站在世界的高度,那就要追问我们文学的国际形象怎么样,国家的文学魅力怎么样,以一种新的标尺来要求。事实也是这样。比如今天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很多中国作家不再将世界文学简单视为西方文学,那种与西方文学潜在的隔阂甚至对立心态正在发生改变,向着共生共融方向行进,也把自己视为世界文学的一分子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在上升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文学如何在建设和谐文化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我们曾经讲了多少年的斗争哲学、非此即彼,现在提出和谐理念,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个划时代的理念我们必须要认真地学习和领会。什么叫和谐?我理解,和谐不是绝对地同一,不是统一律,不是“同”而不和。如果只存在一种声音,那不叫和谐,和谐强调的是和而不同,不同的音调才能组成美妙的音乐。一个调好了音的琴和弦,显得很宁静,其实有内在的紧张性和不同力量在一个更高程度上的调和,如果不和谐,弓可能折了,弦可能断了。看不见的内在和谐,比表面上的和谐更重要。对于追求政治理想上的和谐、社会观上的和谐,大家是一致的,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家如何处理他的创作,政治家的政治与文学家的政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作家来说,如何在和谐理念的大背景下,处理悲剧意识、处理苦难意识、处理贫富悬殊题材,如何大胆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可能都是需要深入思索的新课题。事实上,为了和谐,更要敢于直面差异和矛盾,直面不和谐音,大力克服它才是通向和谐之途。
二、市场的力量与文学的分化
新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活、价值取向、审美精神确实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加入世贸以后,在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等各方面都有纵深的发展。在七八年前,我们谈论私人小汽车,还只是梦,离我们很遥远,七八年后,小汽车在一些大城市里急剧膨胀,有的都开始限制了,私人住宅问题也一样。现在我国互联网的注册数达一个多亿,手机注册近四个亿,石油消耗居世界第二位,这些都反映了经济高速发展。“神六”上天,我们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国家,这都是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但也要看到精神层面的生态中存在的逆人文态势:贫富悬殊,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真情缺失,友爱难求,诚信危机,贞操淡薄,贪污腐败,怀疑永恒的种种现象同时存在。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复杂语境。我们必须看到生态的两个方面,好的和坏的。如果只看到一个方面,那作为文学家就没有把我们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研究透彻。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语境下,就出现了我要谈论的“新世纪文学”。为什么不叫“新时期文学”呢?我觉得该换一换了。这绝不是玩新术语,这个名字其实是历史给的,是时间给的,是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给的。我们叫新时期文学已经叫了三十年了,跟现代文学史一样长了,就像一个人,小时候你可以叫他的小名,等他长大了,结婚了,你若还叫他小名就会别扭,并失去新鲜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和之前的文学是不一样的。
必须看到,“新世纪文学”的出现是有一个准备期的,忽略了这个就不科学了。这个准备期大约是从1993年开始的。它是一种市场经济比较充分条件下的文学。现当代文学一百多年了,如果用不尽科学但接近事实的说法来看,它经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还经历了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的文学以及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至今,进入了一个以较充分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文学时代。简单地说,进入市场后,精神的东西变成了商品,文学写作越来越技术化了,文学也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还涉及到今天我们作家的生存状态。如今的文坛早已是三分天下:纯文学刊物,市场化出版,网络传播。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坛了。最近我看到作家“富豪榜”,不知热衷此道的人想说明什么。恐怕只能说明,作家队伍也在贫富分化。但别忘了,文学有自己的标准,最有钱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发行量最大的不见得是最有价值的。最近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刘心武讲“红楼”、闫崇年讲“清史”,都很火,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学和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市场价值的厉害,把文学娱乐化、通俗化、人情化、实用化了。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出不了大师级的大学问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很少有一件事物,一位作家、艺术家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我发现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都说没有想到自己能获此大奖。现在要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和权威,在作家生前就做到这一点似乎比较难。而且,大师和权威的树立需要时间的辨识,甚至数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否与日常化的、平庸的、商业化的时代有关系呢?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人的热情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这只是外在原因。难道我们今天中国的作家就没有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吗?当然有。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作家的几个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市场需求的多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透支的矛盾。市场要求的出产必须快,与文学创作本身的求慢、求精的规律之间的矛盾。此处不再多说。
三、新世纪文学“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