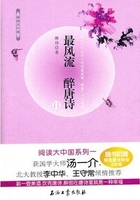听到他说加丽亚这样,我真吃了一惊,但紧接着,我心里袒护起她来了。是呀,许多人在她那儿碰了钉子,当然不会说她好话!至于美术学院的事,谁知道真相怎样呢?反正加丽亚跟“品质恶劣”四个字连不在一起。莫忘记,科长是在打通我的思想啊,他还会对我称赞她的好处吗,更何况她的许多美处只有我一个人认得出。
科长见我低头不语,以为我动了心了,便叫我回去好好想想。
怎么想呢?说良心话,他的道理没有一句不对;就是有一样,加丽亚是活生生的人,我爱她,也相信她会爱我,我曾想象和描绘了那么多我们将来共同生活的图画,如今一百步走了九十九了,我怎么甘心一刀两断呢?
我知道,如果我认真地去咀嚼科长的话,我自己的良心会受不住的,结果我还是两边下不了决心,那只会无限期地把事情再拖下去,如今从上到下全注意上这事了,哪还有拖延的余地?
我决定回家把事情说穿,跟妻一刀两断!
一想到马上要处理,我又害怕起来。妻的许多可爱的地方一下子又都涌到了我的眼前: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给我留下的好印象,到我们最近一次吵架中她的忍让态度,一场比一场鲜明地在自己脑子里重映开了。我不禁问自己:“我真没有冒失吗?我失去了她,真的不致后悔吗?……”
“果断一些!”我出声地对自己说,“照这样犹豫不决,什么事也做不成!”
然而,我还是决断不了!加丽亚呀加丽亚,你若不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是会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足吗?你害了我!
啊,不,幸福的机会,一生也许就只有一次,如果碰不上加丽亚,也许我今生都不会体验到和加丽亚相处时的愉快,你还是该来的。
另外我也想到,加丽亚尽管跟我很好,但从来没有明确表白过我们的爱情,万一她变了呢?我还是要先试探一下。
我悄悄走到加丽亚宿舍门口,胆怯地敲了敲门。
里边一阵脚步响,门开了。她披着头发站在我面前,笑道:“半夜三更,什么事?”
我说:“没事,我从来没到你这屋来过,看看……!”
“那就请进吧!”
她的墙上挂着两幅她的油画像,——一个是正面半身,一个是倚在大石柱子上的全身——和一张漫画像,下边各有一个简化的作者的署名。对面墙上,是一张许多穿着滑冰服的人的合影,加丽亚站在中间,周围有一群小伙子。她推了把椅子给我坐。我看到桌上面,台灯前边放着个未完成的半身泥塑人像,便问道:“这是我的?”
“你的完了!”她回身从书柜上拿下一个硬纸匣来,递给我说:“请自我欣赏吧!”
我打开一看,果然是戴着皮帽的、我的半身像。因为比我本人漂亮,有些不大像我了。我禁不住称赞说:“好,好极了!”
她笑道:“是人长的好,不是我塑得好。比如我吧,再好的雕塑师也不能把我塑成个艺术品!”
我说:“得了,不用塑,你本身就是件最好的艺术品!”
说笑了一会儿,我正打算把话转到正题上去,外边有人敲起门来。
“谁?”加丽亚拉开门,进来的又是那个穿蓝皮猴的(他又改穿中国式的绸棉袄了,还是蓝色的),他进来后对我点点头,便在桌的一旁坐下了。
我暗骂他来得不是时候,心想他一定有什么事,索性等他走了再说吧,便随手从桌上拿起本书来乱翻着。
见他的鬼,他也坐在那儿翻起书来了!我看看加丽亚,希望她设法把他支出去。
加丽亚看看我,又看看他,格格地笑起来了,说道:“真妙,你们怎么上我这儿演哑剧来了!”
我不由得笑了,他也笑了。
“咱打牌吧!”加丽亚打破僵局说,“赌倒茶的!输了的人给赢了的倒茶!”
我急得不得了,哪有心思打牌!可又不甘心出去让那家伙在这儿——我很后悔以前竟没想到上宿舍来找加丽亚,他一定常常来的!——就跟他们打起牌来。鬼知道怎么搞的,一上去我就输,还要给他倒茶,而且一点也看不出加丽亚对我比对他更亲热些,到第三盘,我把牌一推说:“我不玩了,困得很!”
“别丧气嘛!”加丽亚半玩笑地说,“人们都说赌场上失意,情场上得意呀!”
我觉着加丽亚这话大有深意,立刻浑身都舒畅起来,用胜利者的眼色扫了扫蓝棉袄,说:“好,打!”
可是外边也响熄灯铃了。
我恋恋不舍地抱着我的塑像走出屋,加丽亚送我们出来,悄悄对我说:“你回去看看塑像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
“调皮鬼!”我说完,轻飘飘地向宿舍走去,我等不及回去看,走到一盏路灯下就把纸匣打开了,伸进手一摸,摸出一张纸条,上边写道:
“人还像,只是不知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星期天下午三点,我去北海,你来不?”
一股暖流从心底冲上脑袋,我呼吸都困难起来!一时高兴,便抽出笔来在一边写道:“加丽亚,加丽亚,你就要看到我的心了!”
苦苦地思索了好几天,决定最后一次试试妻子,看还有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实在没有,那就让她恨我好了,也许那样更好些!若叫她带着怀念离开我,对她说来就更难忍受,对我说来,也会加深良心上的自责。
星期六的夜晚到来了。
天冷得出奇,北风吱吱乱吼,马路上冷冷落落,偶有几个行人,也把头躲在大衣领里边。悬在街正中钢丝上的电灯疯了似的乱摇着。
我到家时,妻已先回来了,正在火炉上煮什么,满屋都是甜味。她一只手拿着筷子,两眼直瞪瞪地瞅着火苗。
见我进来,她问道:“外边冷吧?”
我随便答应着,把塑像放在桌上。她凑到桌前,打开纸匣一看,便叫道:“好!”端详了一阵,又说,“可惜这人的技术不高,塑得有些走样了。”
我板着脸说:“艺术是要夸张一些的,你不懂!”
“干什么单单夸张这顶皮帽和围巾。看!帽子还歪着,”她笑道,“好好的人,弄得像个资产阶级大少爷。”
我说:“我本来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请原谅。”
“你不用凶,”她笑道,“我今后反正不跟你吵架了!真下了决心!”
我觉得她真的有点和平常不一样,暗暗感到有些蹊跷,但又不好意思再板着脸,便假笑道:“不吵了,哭起来还不比吵架更烦人?”
“也不哭了,傻瓜才吵架和哭!”她微笑着说,“我想明白了,那样能解决问题吗?不能!只表现自己软弱无能,反正两人要过下去的,干么不找个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光冲动毫无用处!”
“她是打算一辈子不与我分开了?”我暗想着,有点失措,脱掉大衣后,便拉了把椅子在一旁坐下,心里一边想主意,一边说些没用的话应付她,省得她发现我心不在,又伤心。
我问她:“煮什么?”
“酸楂酱,最近我……”她笑笑说,“我想吃,你不爱吃吗?煮好,咱们一人装一罐带到机关去吃。”
我不感兴趣地说:“算了吧,罐子不好刷。”
“我来刷。”
我便不再说话了。她也不像平常那样追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只一边搅锅里的酸楂,一边对着火苗出神。我觉得她有些异样,但没心情去关怀。坐了会儿,我说困了,便先睡下。
睡到半夜,一翻身,我觉出床在轻轻地颤抖,注意了一下,听到她在被底下抽泣。
“讨厌,和这种人一起生活就是哑巴也会发脾气!”我心想,不愿理她,扭过身去。
过了半天,她还不停,我忍不住了,回过头来喊道:“你有什么委屈的,说出来好不好,只是哭!别人老远回家来就是听你哭的?”
她不回话,哭得更响了。我觉着再在她身旁躺下去,浑身要烦躁得炸裂,便一撩被子,披上大衣下了床,拧开灯,从桌上抽出一本小说来,坐在火炉旁看书。眼睛看着书上的字,脑子里却想着其他事。我对自己说:“看来只有离婚才能从这种痛苦里解脱出来了,这算什么生活?每星期六都这样度过!科长光知道讲大道理,让他来过两天这样的生活看!……”
过了许久,我觉得又冷又困,她也安静下来了。我才又回到床上去躺下,一边盖被,一边生气说:“你考虑一下,这屋子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只顾耍脾气,别人怎么忍受?我们都是平等的人,我又没有压迫你。”
她沉默着。我躺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睁开眼,她已在地下缝东西。炉子周围烤着我昨晚脱下的内衣,干净的衣服放在我枕边。我心里鄙视地说:“真是一个不直爽的人,心里明明对我不满,表面上还这样做!加丽亚绝不会这样。”
我一边穿衣服,淡淡地问:“缝什么呢?”
她头也不抬,说:“手套,你的!”
“歇一会儿吧,我打算买呢!”
“我知道你不会戴它,但既做了,就做完吧!”她忽然口气转为凄然地说,“什么都应该有始有终不是?”
我走下地,见她两眼红肿得厉害,便说:“你瞧,昨晚你自己说的,再也不哭了,结果倒哭得更厉害了!”
“你放心好了,今后再不叫你看见眼泪。”说完,她轻轻叹了口气。
我讪讪地找些话来问她,她回答得很平静。我想:“她平静下来了,该找机会摊牌了。”
吃饭时,她突然说道:“我今天下午有事要回去!”
我说:“正好,我下午三点有个会。”
她隐隐地冷笑了下说:“碰得真巧!不过我下个星期不一定回来了。”
我说:“那——我去看你好吗?”
她冷笑道:“不必啦,我们那儿同志也多得很,这个家,也确实叫人痛心……”说着,她又对着窗发起愣来。
望着她那委屈、痛心的神色,我也很难过,心想:“快刀斩乱麻,一下子了啦吧!”便把口气放得极缓和地说:“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动感情,冷静地、理智地考虑一下再回答我好不好?”
她震动了一下,随即平静下来,两眼瞅着地说:“你说吧!”
“你是个好同志,我也爱你,可是,你考虑一下,你跟我性格相投吗,共同生活下去会有真正的幸福吗?你不要生气,你冷静下来想想,……”
“我知道你要提这问题了!”她似乎胸有成竹地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不?”
“好!”
“你坦白地说,你最不满意我的是什么?”
我脸红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咱们个性不同,我常使你痛苦,我也很惭愧……”
“不必拐弯!”她脸色苍白地直视着我说,“我们到底共同生活了许久,互相还是知道些根底!什么个性不同,我们开始不是相处得挺好吗?我替你说好了,我年纪比你大,我长得不漂亮……”
我忙解释:“你……”
“不用解释,不用担心我会受不住,我用不着人怜惜的!”
我急道:“你别误会,我早说了,我只是提个问题,叫你别冲动……”
“没有什么误会,我又不是孩子!”她顿住,眼睛一转,落下两颗泪来,她急忙转过身去,背对着我问,“我只问你,当初我说我年纪比你大,要你认真考虑,你为什么说考虑好了?……说什么,全怨我自己没出息……”
“你别急眼!”我说,“我只是问问,又没提离婚!”
“你怕负责任,怕我怀恨你,不敢提!”她转过身来,冷静地说道:“没关系,我主动提出来好了!我并不是要求好坏有个丈夫!我要的是真正的爱情,两人这样敷衍下去都没好处!以前我一直存着个重新和好的希望,现在我明白没希望了,不会拖的!”她说,从椅子上提起手提包,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又回身轻轻地把门拉上,就好像平常回去一样,一点暴怒的痕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