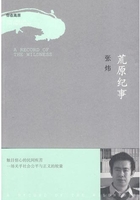夏丏尊先生死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了;但静静的想着时,我们仿佛还都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
他住在沦陷区里,生活紧张而困苦,没有一天不在愁叹着。是悲天?是悯人?
胜利到来的时候,他曾经很天真的高兴了几天。我们相见时,大家都说道“好了,好了”,个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泯没了愁闷,耀着一层光彩。他也同样的说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入愁闷之中。他比我们敏感,他似乎失望,愁闷得更迅快些。
他曾经很高兴的写过几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面的主张出来。但过了一会,便又沉默下去,一半是为了身体逐渐衰弱的关系。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的压迫和统制。他最富于正义感,看不惯一切的腐败、贪污的现象。他自己曾经说道:“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又道:“记得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刻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产时,不敢走入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均见《平屋杂文》)
这便是他的性格。他表面上很恬淡,其实心是热的,他仿佛无所褒贬,其实心里是径渭分得极清的。在他淡淡的谈话里,往往包含着深刻的意义。他反对中国人传统的调和与折中的心理。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早衰者,不仅在身体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甚么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得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
在《早老者的忏悔》里,他又说道: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来不得劲,只得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到疲劳,甚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
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这是他的悲哀,但他的并不因此而消极,正和他的不因寂寞而厌世一样。他常常愤慨,常常叹息,常常悲愁。他的愤慨、叹息、悲愁,正是他的人世处。他爱世、爱人,尤爱“执著”的有所为的人和猖介的有所不为的人。他爱年轻人,他讨厌权威,讨厌做作、虚伪的人。他没有机心,表里如一。他藏不住话,有什么便说什么,所以大家都称他“老孩子”。他的天真无邪之处,的确够得上称为一个“孩子”的。
他从来不提防什么人。他爱护一切的朋友,常常担心他们的安全与困苦。我在抗战时逃避在外,他见了面,便问道:“没有什么么?”我在卖书过活,他又异常关切的问道:“不太穷困么?卖掉了可以过一个时期吧。”
“又要卖书了么?”他见我在抄书目时问道。
我点点头:向来不做乞怜相,装做满不在乎的神气,有点倔强,也有点傲然。但见到他的皱着眉头,同情的叹气时,我几乎也要叹出气来。
他很远的挤上了电车到办公的地方来,从来不肯坐头等,总是挤在拖车里。我告诉他,拖车太颠太挤,何妨坐头等,他总是不改变态度,天天挤,挤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时等了好几部还挤不上。到了办公的地方,总是叹了一口气后才坐下。
“丏翁老了!”朋友们在背后都这么说。我们有点替他发愁,看他显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营养是那么坏,家里的饭菜不好,吃米饭的时候很少;到了办公的地方时,也只是以一块面包当做午餐。那时候,我们也都吃着烘山芋、面包、小馒头或羌饼之类做午餐,但总想有点牛肉、鸡蛋之类伴着吃,他却从来没有过;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我们有时高兴上小酒馆去喝酒,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在沦陷时代,他曾经被敌人的宪兵捉去过。据说,有他的照相,也有关于他的记录。他在宪兵队里,虽没有被打、上电刑或灌水之类,但睡在水门汀上,吃着冷饭,他的身体因此益发坏下去。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比别人自由些,只有半个月便被放了出来。
他说,日本宪兵曾经问起了我:“你有见到郑某某吗?”他撒了谎,说道:“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那么爱护着他的朋友!
他回家后,显得更憔悴了;不久,便病倒。我们见到他,他也只是叹气,慢吞吞的说着经过,并不因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而特别觉得愤怒。他永远是悲天悯人的。——连他自己也在内。在晚年,他有时觉得很起劲,为开明书店计划着出版辞典;同时发愿要译《南藏》。他担任的是《佛本生经)(Jataka)的翻译,已经译成了若干,有一本仿佛已经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译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参考,我答应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够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时,他已经用不到这部书了。我见到它,心里便觉得很难过,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补偿的事。
他很耿直,虽然表面上是很随和。他所厌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还不曾忘记。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代的浙江教育厅长,他便有点不耐烦,叨叨的说着从前的故事。我们都觉得窘,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
他是爱憎分明的!
他从事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学里教书。他的对待学生们从来不采取严肃的督责的态度。他只是恳挚的诱导着他们。
……我入学之后,常听到同学们谈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我记得最牢,感动得最深的,是说夏先生最初在一师兼任舍监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同学,晚上熄灯,点名之后,偷出校门,在外面荒唐到深夜才回来;夏先生查到之后,并不加任何责罚,只是恳切的劝导,如果一次两次仍不见效;于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着他,无论怎样夜深都守候着他,守候着了,夏先生对他仍旧不加任何责罚,只是苦口婆心,更加恳切地劝导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
总要使得犯过者真心悔过,彻底觉悟而后已。
(许志行:《不堪回首悼先生》
他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创办人之一,立达的几位教师对于学生们所应用的也全是这种恳挚的感化的态度。他在国立暨南大学做过国文系主任,因为不能和学校当局意见相同,不久,便辞职不干。此后,便一直过着编译的生活,有时也教教中学。学生们对于他,印象都非常深刻,都敬爱着他。
他对于语文教学,有湛深的研究。他和刘慧宇合编过一本《文章作法》,和叶绍钧合编过《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及《文心》,也像做国文教师时的样子,细心而恳切的谈着作文的心诀。他自己作文很小心,一字不肯苟且;阅读别人的文章时,也很小心,很慎重,一字不肯放过。从前,《中学生》杂志有过《文章病院》一栏,批评着时人的文章,有发必中;便是他在那里主持着的,他自己也动笔写了几篇东西。
古人说“文如其人”。我们读他的文章,确有此感。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每每劝他编成集子。《平屋杂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的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虽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读了后,也猜得出是他写的。在那里,言之有物,是那么深切的混和着他自己的思想和态度。
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只是平平的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决不急就。在文章上讲,是“盛水不漏”,无懈可击的。
他的身体是病态的胖肥,但到了最后的半年,显得瘦了,气色很灰暗。营养不良,恐怕是他致病的最大原因。心境的忧郁,也有一部分的因素在内。友人们都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在这样一团糟的情形之下,“合时宜”的都是些何等人物,可想而知。怎能怪丏尊的牢骚太多呢!
想到这里,便仿佛还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在耳边响着。他的忧郁的脸、病态的身体,仿佛还在我们的眼前出现。然而他是去了!永远的去了!那悲天悯人的语调是再也听不到了!
如今是,那么需要由叹息、悲愤里站起来干的人,他如不死,可能会站起来干的。这是超出于友情以外的一个更大的损失。
194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