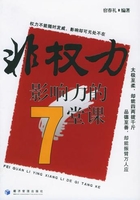文/李宏
岁月是一把梳子,往事大都经不起梳理。人生在梳齿间流连,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也在更行更远的时间里纠缠。
小时候家里穷,特想读书却无书可读。记忆中,每到新学期开始,我都会像盼过年似的盼着发新书。等新书发到手,还来不及用旧年画纸包上书皮,就已经从头到尾看了个遍。
母亲说,小孩子看书太多没好处,弄不好将来成了近视眼,会分不清稗子、秧子,连当农民都不合格。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多读点书也没啥坏处,长不了力气还可以长心眼,免得以后被别人牵去卖了还帮着数钱。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对土地有一种天然的依附情结,对读书求学则常常无动于衷。按惯例,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大多应该在懂事以后主动接过父母手中的锄头和扁担,然后理所当然地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日子。偏偏我却对读书情有独钟,也许,这是上帝的一次笔误吧我读初中的时候,四乡八里已有不少农民弃了土地出外打工,受他们影响,我的父亲也丢了锄头到镇上的机面房去学徒,活太忙时,父亲就叫我搁了书包去打杂。开始,我很不情愿,一来怕功课耽误太多赶不上,二来怕五大三粗的班主任动不动就抡耳刮子。可去了几次以后,我竟像着了魔一般,有事没事都往那儿跑,以至于管帐先生胡子爷想赶我走都不行了。原来,我在裹面用的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批做梦也想不到的旧书。我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出来,藏在墙角旮旯里,歇工的时候就悄悄揣一本带回家看,等到看完之后又揣回来换另一本。就这样,短短半年时间,我竟然偷偷摸摸读了二十来本大部头小说,有前苏联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遗失了的一封信》、《我的童年》、《在人间》和中国的《小矿工》、《红旗谱》、《战地烽火》、《虹》等等,那些早已残缺不全的书多半是破“四旧”的成果,与我们所学的课本有很大不同,沉迷其中,我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只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夏天,一场罕见的洪水冲垮了破旧不堪的机面房。房子倒了,机器毁了,作坊也消失了,父亲又扛起锄头回到希望的田野上。我却心有不甘,每天放了晚学仍到机面房的废墟上去转悠。在这里我又遇到了管帐先生胡子爷。眼前的胡子爷明显老了一大截,头发白了、乱了,腰背弯了、驼了,眼神也模糊了、浑浊了。他手里捏着自己裹的旱烟,问我有没有火柴借来用用。我说学生不允许带易燃物品,如果您需要,我这就给您买去。等我买了火柴回来,胡子爷已经走了,他坐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小捆旧书和一张纸条,大意是洪灾过后就只剩下这么些了,他也用不着了,留给我或许还能派上点用场。那一刻,我很意外,也很感动。我把书拎回家,整整齐齐地压在枕头下面,兴奋得彻夜难眠。
第二天,学校里到处传得沸沸扬扬,说胡子爷昨晚上吊自尽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来无去无,走得干干净净。我反驳说,胡子爷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同学们都笑我疯了,老师也说我莫名其妙,问我是不是起倒了夜说胡话。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但我坚信,胡子爷永远不会从我心里走远,因为,他留给我的远不止是一小捆旧书。
许多年之后,再次翻开胡子爷留下的旧书,我猛然发现,那一段往事,那一个人,早已变成岁月的书签,镶嵌在生命的年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