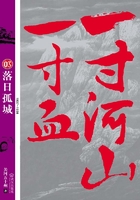可是,现在痛的人是她,那就另当别论了,别被她知道是谁干的,若有朝一日让她知晓,她定要那人生不如死,后悔活在这个世上,让他觉得连死都是快乐的。
她一点也不记仇,真的,只要别人没惹到她,没踩到她的底线,她可以左耳朵进又耳朵出,甚至可以风过了无痕,全当没看见。
啥?你要问她的底线是什么?那可就多了,掰着手指头算算,一,二,三,四,五,六……貌似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眼下,他们就已经触犯了她两项大忌。
其一,她这人,别的不说,就是最爱干净。其二,这点,是她最不能忍受的,她的痛觉神经很敏感,所以,她最怕痛了,一点小擦伤都能疼个半天,以前有哥哥姐姐们在的时候,都把她当宝贝一样的细心呵护,深怕有个什么闪失,尽量不让她去触碰危险的事物,因此,她可以肆无忌惮的在他们面前装可怜,耍无赖。
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人来当她的出气筒了,也没人来同她分享盗到宝物之后的喜悦,听她的絮絮叨叨。很多时候,明明知道她是故意的,哥哥姐姐们也只是笑笑的包容她的一切。虽然大哥很严肃,二哥很花心,三姐很妖媚,但是,她现在很想他们了。早知道就不应该那样做,真是笨蛋,话说现在可不可以反悔啊!还有四姐,平时总是温温和和的,脾气好得不得了,尤其是面对她的时候。
想到这些,舒妍冰身上的疼痛似乎没那么明显了。
看着自己裸露在的肌肤,上面是一条条血红色的伤痕,舒妍冰泛着水光的眼眸凝结成冰。Shit,别让我看见你,否则我一定把你整得连你妈都认不出来。
舒妍冰抬起左手对着摇挂上空的烈日,食指上的红宝石在强光的照射下,发出刺目的艳丽光泽。还好自己随身带着的空间储物戒还在,看来老天待她还是不薄的嘛!说不定以后还能靠着它联系大哥。想到这里,舒妍冰的心情不禁有些雀跃。
“呜呜!”这时一阵怪异的叫声从舒妍冰的侧面传了过来。声音里似乎有着强烈的不满,抗议自己被某个陷入自我YY意识的女人彻底忽略了。
舒妍冰听到这叫声,潜意识里有几分熟悉的味道。忙侧过脸看向身边,只见,一条浑身雪白,身长两米有余的巨型白狼立在舒妍冰的身侧不远处。
舒妍冰触及白狼散发着幽光的瞳孔,很镇定的把脸偏向另一侧,双手微失力的拍打着颊面,对自己说:“我一定是做梦!我一定是做梦!”
“呜……”又一声叫声从舒妍冰的身侧传来。制止了她自虐的催眠行为。舒妍冰把脸转向刚才的方向,发现那只通体雪白的狼依然屹立在那里,连半蹲的姿势都米有变过,长长的舌头还在那里一伸一缩的,散发着身体的余热。
“原来这不是梦!”瞬间,舒妍冰的眼里聚集了泪光,隐隐有黄河泛滥之势。
那只半卧的白狼看着对面女子的表情,散发出幽光的眼底顿时充满了戒备,直立起身子,紧紧盯住眼前的女子。
舒妍冰抬起泛着泪光的眼眸锁住望着她的白狼,一个猛扑,白狼尚未回神,便被某女的爪子抱了个满怀,嘴里还欢呼的直嚷嚷:“哇塞,白狼啊!以前只能在加拿大北部才看得到,居然在这里给我遇上了,毛好软好舒服哦!看你也没地方去,要不你就跟着本小姐混好了,包你吃香的喝辣的。”某女毫不羞愧的哄骗到,丝毫没注意自己现在的穿着似乎跟乞丐无意,不知她哪来的说服力。
白狼一个踉跄被某神经质的女人扑到在地,并未作何反抗,很乖顺的,在听到她对自己说出那番诱哄的话语后,眼底露出一抹无奈及笑意。这些是玩得正起劲的舒妍冰所没有看到的。
舒妍冰趴在白狼身上,闭着眼把脑海里存留的记忆疏通了一遍,半响后,睁开漂亮的双眸,眼底闪着寒光,对着白狼说道:“白狼,是你把我舔醒的吧!谢谢你哦,不如,我们去闯皇宫怎么样?”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舒妍冰嘴角轻扬,带着说不出的冷意。
等着吧!本公主回来了。
皇宫,巍峨屹立,是权利的尖端,谷望的摇篮,罪恶的深渊,奢华的代表,无数人穷极一生都无法靠近的地方,数千载的沉沉浮浮,朝代更替,依然有它存在的理由,这或许便是人性所折射出来的贪婪及谷望。
历史上,无论一开始打着怎样为民请命的旗号,最后都逃不过谷望的诱惑。当你站在权力的巅峰时,心底的恶魔便开始滋长,人性亦慢慢消磨,双眼看清的永远只是利益多少。是敌是友,端看你对他是否有足够的利用价值。
夜,已经很深了。浓墨一样的天上,连一弯月牙、一丝星光都不曾出现。偶尔有一颗流星带着凉意从夜空中划过,炽白的光亮又是那般凄凉惨然。
风,是子夜时分刮起来的,开始还带着几分温柔,丝丝缕缕的,漫动着柳梢、树叶,到后来便愈发迅猛强劲起来,拧着劲的风势,几乎有着野牛一样的凶蛮,在皇城的每一条街道上漫卷着,奔突着……
窗外的风,依旧刮着,卷浮起的砂粒,直拍拍地打在窗纸上,发出沙啦沙啦的声响。窗内,烛火还是那般跳跃,不时地爆起一朵亮亮的灯花,随后一缕黑烟就蜿蜒升起。
很显然,这是一个月黑风高夜,适合杀人抢劫,更适合做贼。
一个轻巧灵便的身影悄然跃到皇宫最高宫殿的屋顶之上,其全身裹在黑布里,与沉重的黑幕融为一体,只露出两只亮晶晶的双瞳,如鹰般锐利的查探四方。
半响后,黑影眼瞳紧缩的盯住远方一处唯一亮着灯的宫殿,再瞧瞧这距离,黑影忍不住在心里腹诽:臭老头,有钱也不是这么显摆的,把皇宫建这么大作甚,害她得这么辛苦的跋山涉水,这不是摆明跟她作对吗?哼……要不是看在你对这身体的原主人还算不错的份上,而自己貌似有义务帮她完成心愿,她才不会劳心劳力的半夜三更站在这该死的屋顶上吹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