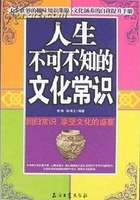鬼门关的称谓流变,也是岭南历史更迭前进的见证,其社会文化意蕴可从其名称的变化中探索到蛛丝马迹。
古时岭南鬼门关曾是通往钦州、合浦、海南、越南的干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段,至圭江登岸后,即经此关入南流江,再抵合浦出海。今日珠三角一带、北部湾经济圈和广西“沿海一极”的发展格局,也依赖此关的周转输渡。五代后晋赵莹等人的《旧唐书·地理志》和南宋王象之的《舆地记胜》都记录过其原称为“桂门关”,后来误传名称才变为“鬼门关”。元代廉访使月鲁,曾把它改名为“魁星关”;明洪武时恢复“桂门关”原名,宣德时又改为“天门关”,后来再为“归明关”。在民间,人们仍然袭称其为“鬼门关”。鬼门关的地名称谓,大体经历了桂门关——鬼门关——魁星 关——天门关的变更。
(一)“桂门关”与“南蛮史”
岭南(现在广西、广东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部分地区)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隔五岭,南阻大海,而桂门关就是进入岭南东南部之口。中原人对岭南基本一无所知或知之寥寥。直到唐代,岭南仍被看做“瘴疠”之乡,居住在此地的人被称为“南蛮”或“蛮夷”。孟浩然的《送王昌龄之岭南》有诗云:“土毛无缟纻,乡味有槎头。已抱沈痼疾,更贻魑魅忧。”南岭山脉的天然屏障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自唐朝宰相张九龄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才逐步得以发展。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与中原政权及其文化的隔膜尤为浓重。由于中国历代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即长江以北、黄河中下游区域的两河流域,“汉人优等论”尤为盛行。且岭南人不为汉化,敝帚自珍,高适《饯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岭南》诗曰:“彼邦本倔强,习俗多骄矜。翠羽干平法,黄金挠直绳。若将除害马,慎勿信苍蝇。魑魅宁无患,忠贞适有凭。”虽然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在北宋以后逐渐迁至长江以南,但统治势力对岭南可谓鞭长莫及,其文化渗透力也相对薄弱。
岭南负山临海,五岭横贯东西,挡住了来自北方的寒流,大部分地区多较潮湿,气候湿热。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长期阻碍了该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而其一些独有的民俗也得以保留下来。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就成了“夷俗”“蛮俗”“陋俗”和落后的象征。明王守仁亦言:“岭南之州,大地多卑湿瘴疠,其风土杂夷,自昔与中原不类。”从统治者的利益和主观意识看,岭南地区没有中原土地的肥沃,而且频发洪水台风,自然环境恶劣,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与开发,这使得岭南文化保持着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和独到的地域性。古隘名称讹传为奇特诡谲的“鬼门关”,与岭南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南蛮史”有着不可割裂的关联和渊源。
(二)“鬼门关”——贬官文化的象征
唐宋时期,岭南成为了政府安置流人谪宦的聚居地。仅唐代贬流至广东有史籍可考者,流人近300人(次),左将官近200人,皇亲国戚37人,宰相49人,还有一些达官贵人。而宋代被流贬者仅见于史籍者就有400多人次,加上无考者更无法计数。例如,沈佺期 (656—714年)、杨炎 (727—781年)、李德裕(787—850年)、苏轼(1037—1101年)、黄庭坚(1045—1105年)、李纲(1083—1140年)、赵鼎(1085—1147年)等官员皆曾被流贬至南下两粤。一些文人墨客途经鬼门关,留下了许多借景抒情的著名诗句。李德裕 《贬崖州诗》(一说是杨炎所写)云:“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宋人刘敞 (1019—1068年)《送人之岭南》云:“君去炎方远,行行万里余。渐惊南瘴酷,益见北人疏。山谷藏雄虺,溪潭养鳄鱼。秋风雁不到,何处俟归书。”
可见到了岭南,如同进入了一个毫无生气、黯淡无光的境地,与作别生期并无差异。这些来自中原的南下士大夫被流贬后日积月累的悲戚之情和流落异地的恐慌羞愧,都借由对“鬼门关”来抒发和升华,得到了些许的宣泄和释放。“鬼门关”这一由北方失意士人造就的恶称,逐渐取代“桂门关”,涵盖了岭南关口的“所指”,成为唐宋“南流史”的象征符号。
古代“贬官文化”产生的客观原因来自社会政治的黑暗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于唐代设置的“贬官”制度随着时间推移,由原来打击腐败的功能而慢慢蜕化成为朝廷专制势力铲除异己的卑劣手段。一些有才华而正直的文人在经历了官场斗争和势力欺压,政治上不得志后,只得借山水来抒郁明志。例如,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二次被贬时,成为宋朝官员被贬谪到岭南的第一人。他因文字狱被贬到海南儋州任昌化军长官,到儋州四年,时已66岁。在他的一首《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沦此,今斯言乃验》的七律中,颔联两句为“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以“过鬼门”表达其渴望遇赦北归的心情。
总之,唐代以前,岭南鬼门关仅仅由于其地势险要以及军事商贸的单纯地理概念为人所知,被称为“桂门关”(是指进入桂地的门户)。而到了宋代,“桂门关”与“鬼门关”已经发展成为了学界争议的公案。直至洪武 (1368—1399年)初年,“鬼门”被承认为误称,并恢复为“桂门关”。但人们为什么会将“桂”讹为“鬼”而不讹传为“规”“归”“桂”等字呢?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鬼”字就此流传并沿袭下来呢?原来,此关是古代前往岭南南部的必经之路,凶险多瘴,中原人在此多为瘴病所累,去者鲜有生还,因此被认为是踏上了吉凶未卜的凶险之路。民间传说,鬼门关对峙的两座石峰极像两扇鬼门,有大大小小的魔鬼在那里把守。如果有行人进关,魔鬼叫一声 “合”,“鬼门”马上并合,将行人榨成肉酱。妖魔吃了人肉后又把 “鬼门”叫开,等待下一批送死鬼。当然,这些说法只是源于人们对岭南地区的不了解和对桂门关凶险路途的畏惧,纯属杜撰恫吓之辞。
(三)“魁星关”与岭南科举制度的发展
元朝时,除了“鬼门关”之外,又有“老鼠关”之类的戏谑名称。元代台州人陈孚(1240—1313年)《老鼠关》诗云:“春风又送使旌还,笑掬清波洗瘴颜。从此定知身不死,生前先过鬼门关。”此戏称来去匆匆,并没有被人们沿用至今。历经科举制度的完善和中原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自唐代以来,唐宋科举文化有效地向岭南渗透,使得岭南书院继起,衣冠遮道,士人群体日趋壮大,南北文化交往从单向被动的方式开始转向为双边互动,南北文化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
尤其是唐宋以来,大批岭南士人离乡北上赴考、任职,路过关口,都对“鬼门关”避之不及。一种希望金榜题名、蟾宫折桂、大展鸿图和与北人争胜的理念蔚然成风,很多人都尝试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改变命运。到了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伊哷(别译为月鲁或永隆)以中奉大夫任广西道肃政廉访使,为了顺应当时士风,将“鬼门关”更名为“魁星关”。《星学大成》曰:“魁星有三,惟正魁颇验。若人行年星,限遇之,必占甲科;身命临之,进取必魁多士。”又曰:“巨蟹宫文华星,又名天魁星,主及第……文臣官列至朝参,武显边疆郎将位。”虽然是元人主政,不事科举,但是制度层面上的废止,并不能终结南人进取功名的热忱和科举文化渗入岭南基层的事实。例如,关口附近的“嶙峋挺拔而奉为学宫正神”的山岭,受其科举风行的影响,为了奖掖后学激励更多岭南士人,也更名为“魁星岭”。
所以,元代之所以会出现“魁星关”的名称,根源就是在科举文化的强劲冲刷下,两粤地区壮大的精英群体通过行动来影响政府、言说自我的一个结果。这是岭南士人希望借助修正地名,自觉地“以我手写我乡”、改变岭南落后面貌的一次努力。不过,这种努力毕竟不能摆脱来自中原汉文化的强势影响,也还未能续接上早已失落的民族本色命名,也只能依旧在汉族话语体系中“自说自话”。到了洪武初年,又被新政府复其原名“桂门关”。
(四)“天门关”——从地狱到仙境
道教南传,在其衍播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岭南土著文化融合,形成地方特色,产生“互化”效应。而“天门关”名称的产生与道教在岭南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儒、佛、道三教交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道教在岭南的传播,更多地与儒学和佛教的内容相兼容,这是道教南传突出的特征之一。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土。开始依附于当时已具有宗教性质的黄老道,同时吸收老庄学说发展义理,初时没有佛经行世,中土人士视之为斋徽祭祀方术的一种,佛教影响还不是很大。汉末桓灵之际,梵僧相继来华,开始了译经活动,佛学逐渐传播到中土,佛教日益兴盛。并且不甘依附于祭祀方术的行列,想要振翅高飞。中土人士才意识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不同,民族意识与习惯力量促使他们萌发抵触情绪,特别是固守传统宗法观念与伦理道德的儒生以及承继古代宗教习俗的道士,隐约感到一种精神威胁,于是儒、佛、道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斗争,同时又相互吸收。这种情形自汉末已经开始。
三皇五帝是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受当时条件所限,他们不一定到过岭南,但古籍中的记载,反映出中原与岭南很早就有往来,甚至有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帝王对边远的岭南是采取“南抚”政策——抚,就是抚御,从政治上说,既是控制,也是安抚。岭南得到“南抚”的特殊照顾,政治气候较为缓和、宽松,有着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南抚交趾”还有另一番意味,一般被看成是儒家教化南暨的象征,作为儒家圣王虞舜的南抚交趾,被冠以一种不同于北方正统儒学的极具道教色彩的形象,凸现了作为荒僻地区的岭南,与道教具有某种不解之缘。
秦朝以前,岭南主要处于无君和无礼治状态,虽然夏、商、周时期,岭南与中原的联系更具体,正如《吕氏春秋·恃君览》所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姿、阳禺、雏兜之国,多无君。直到秦末,赵佗建立南越国,岭南仍是自成一体,不以礼治:佗之自王,不以礼乐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推结其据为蛮中大长,与西欧、骆、越为伍,使南越人九十余年不得被大汉教化。“不以礼乐自治”就是不理儒家礼仪而另搞一套;“椎髻”就是“为髻一撮似椎而结之”,这与中原的束发戴冠全然不同;“箕据”就是席地把双腿交叉而坐,这种坐姿,为儒士所不容和耻辱,因而,陆贾斥之为“反天性,弃冠带”,王充视之为“背叛王制”。赵佗自己也检讨道:“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仪”。可见,南越王赵佗已经放弃中原礼仪,从越俗。
秦汉以降,岭南虽己被开辟为封建帝国的疆域,但封建王朝的统治长期局限在一些交通要道和郡县治所附近地区,其余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仍处于无君主的部族状态,如淮南王上书时说: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薛综上书时也说:“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表明古代岭南,远离封建统治权力中心,是一块天高地远、皇帝鞭长莫及的逍遥乐土,正如欧阳修所说:“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郑,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人们向往这块逍遥乐土,如桓玄为逃避权臣所忌,自求到广州任刺史;又如会稽山阴人杨方,为着“闲居著述”,“求补远郡”,最后到了岭南任高梁太守。岭南这种疏远儒学,不重礼治的特点,正好符合仙道逍遥自在的性格。
与儒学相比,道教无论思想或行为都带有异端成分。首先,就其思想而言,道教游离于政治之外,许悼云先生曾指出:“道家(也指道教)是不依附于政权和国家的,所以它在没有国家的环境中更具创造力。基本上道家从根本上讲是反体制、反国家的,国家力量不强,儒家体系就无所依托。”岭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原文化中心,是较难接受儒家思想体系的,秦汉以前,“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蔼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在中原行冠冕之礼时,岭南还是断发裸体,处于未开化状态。直到汉代,岭南依然是“不知礼制”。显然,依附于政权和国家的儒学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和发展,处在朴素的百越文化圈熏陶之中的岭南,倒是更多地接受了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荆楚文化,正如屈大均所说:岭南多有“屈宋流风”。
作为南楚余绪的岭南文化,对儒家思想涉足不深,在传承正统思想文化方面显得底气不足,也正因为受正统观念影响不多,岭南思想表现得较为开放和灵活,容易接纳和生成具有创新性和异端性的思想观念。其次,就其人员而言,大多数的道教中人都是疏离正统儒学的异端分子,他们都有奔赴岭南这块“化外之地”和“逍遥乐土”的欲望和行动。再次,就其修炼方法而言,基本上是个体行为,既简便又灵活,其外炼内服的方式也颇为独特,在儒士看来难免有点怪异和不可接受,而这恰恰是道教所需要的,又是岭南所具备的。达尔文说得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岭南这块“化外之地”,正适合道教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