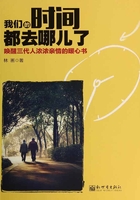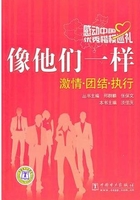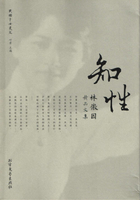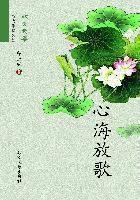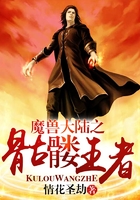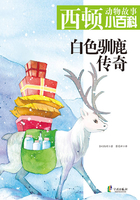正是草长莺飞的初夏时节,从乌海坐车去银川,一路的情景让人感慨。没有鸟语,没有花香,一幕幕的戈壁沙漠,还有贺兰山阙,空旷、苍凉与落寞,综合成一种莫名的悲壮。与莺歌燕舞、芳草萋萋的南国风光相对照,这里简直是又一个世界。一个让人遥想的世界,一个让人怀念的世界,一个让人禁不住顺风呐喊的世界。车在奔驰,思想在游弋,情景在转换:仿佛间看到蒙恬带领修长城的队伍在这里排成一条长龙;卫青风驰电掣的骠骑“甲光向日金鳞开”!浮想联翩之际,那“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杜甫《兵车行》。的景况,那“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蔡琰《胡笳十八拍》。的景况;那“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的景况,历历在目矣。这里的每一颗沙粒,也许就有一个悲壮的故事。
我到这里来,主要想亲眼看一看西夏的文字。西夏的文字,本就是一曲悲壮的故事。车翻越贺兰山,穿过古长城,在九曲黄河畔,在一片青翠的银川城之外,远远看到一座座突兀而立的土山,连绵比肩地散布在一望平沙戈壁之间。像山,不是山,山没有这种格调;像塔,不是塔,塔没这么高大。主人告诉曰:这便是西夏陵园了。好大的陵园啊,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好奇特的陵墓啊,一律由粘土垒成,虽比不上明陵、清陵金碧辉煌,但苍浑气象扣人心弦。
西夏出土的石刻——我说它是天书,便摆陈在西夏陵园的博物馆里。说它是天书,是因为它乍一看就是汉字,似曾相识,可仔细一看,一个字也认不得。字法和写法很像汉字的小篆,不过全都加了一些笔画或者去了一些笔画,加的多去的少,于是笔画比汉字繁得多。书写排列整齐,布局匀称,开张有度,笔画修长,煞是耐看。可是这文字,竟在泯灭的历史中沉寂千年,直到上世纪末才被发现。一个几乎曾经三分天下的强盛国家,一个令大宋头痛,辽、金不敢小视的西夏,一个前后历经十帝一百九十余年的王朝,在与蒙古铁骑摧枯拉朽的博弈中,忽然间花逝烟灭,党项人从此从历史上蒸发消失,泥牛入海无消息,成为千古之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消失了,可那匆忙掠过的影迹,总会在历史的天空里留下蛛丝马迹。这蛛丝马迹便是他们不可能完全带走,他的敌人不可能完全掩埋的文化。近代,经过考古发掘研究,人们终于从文化的层面揭开了西夏的面纱。这文化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知为什么留下来的那些像山不是山,像塔不是塔的实物——土丘,另一类便是陵寝中发现的那些石刻文字。
石刻不多,能看到的几块而已,而且是隔着玻璃才能看到。几块足矣,隔着玻璃看亦足矣,它是那个朝代的标本,是一个时代的木乃伊。我拍了几张照片,光线不甚好,影像不甚清晰,印象却很深刻。有道是书中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果然。虽然几块石片,却是一个时代的写真啊。我们走在路上,也许不经意间踢到一块瓦片,那瓦片上也许就有雕迹,有印痕,也许它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文物,一个被我们忘却了但又搜索不到的时代。就像当年的甲骨,人们用它当药引,不知碾碎了多少片,直到清廷国子祭酒王懿荣自己偶尔煎一次药,才发现这龟背上竟然有字,于是揭开了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的一页。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最终留下来的,只能是文化。诺亚方舟没有了,阿房宫没有了,党项人的国都一夜之间化为灰烬,而文化留下来了。文化遗存,使我们的遥想和怀念成为可能。
然而,时光是一条流淌的河流,任何的东西在无际广阔的时空里都不过是一个过程,文化最终也是如此。玛雅人的文化还能流传多久?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也只有中华民族的文明得以延续并繁荣。一个民族只有与时俱进,文化才能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