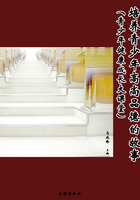鱼子酱涂抹在苏打饼干上,添上一片切片的白水煮蛋并撒上葱花,装到小碟子里,再备上一杯脱脂牛奶,那便是付北兴的早餐。纪琴做得很仔细。跟付北兴生活这一段时间,她很小心地观察他的喜好。她很悲哀伤地想:自己这是有“职业道德”吗?这样没自尊没心没肺地去迎合男人……什么事是不能细想下去的,仔细一想,日子就没办法过下去了。含混着,每天给自己爱的男人做早餐,看着他吃光盘子里的所有东西,那也未偿不是一种幸福。
把付北兴的早餐端到餐桌上,给他把牙膏挤到牙刷上,等着里练的付北兴回来。
人真是最善变的动物。这才几年,不过是普通人家出生的付北兴也便有了这许多富人的毛病。要晨练,要吃西式早餐,要健身保持久身材,还有,不允许纪琴给自己买仿品。他说:“要么不穿,要穿就穿正品!”纪琴当然知道正品好,可是正品是要钱的。
坐下来,阳光很好,照得一屋子都是暖洋洋的。纪琴没胃口,只给自己倒了一杯奶,想了一下,又拿出两片面包片,付北兴不喜欢她吃猫食。
抬头看了一下表,付北兴应该晨练回来了。进卧室收拾了一下,一转身的功夫,付北兴已经站在了她背后,宠溺地抱着她,问昨晚睡得好吗?纪琴微笑着拉开他的手,“赶紧吃吧,一会儿凉了!”
面对面地坐下,纪琴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那杯奶。付北兴倒是很有食欲的样子,抓起面包片,三口两口吃进去。他说:“晚上我去接端端,然后咱们去度假村度周末!”
纪琴拿纸巾帮付北兴拂去唇边的奶渍,说:“好!”端端进了全日制幼儿园,一周回来一次。
付北兴吃完早餐,换了衣服,纪琴帮他系一领带,拿了皮鞋,送他出门时,他抱了她一下,拍拍她的脸说:“晚上收拾得漂亮点,有礼物送你!”
纪琴脸微微地红了。她还不是很适应他的样子。他变了很多。从前的付北兴霸气,自我为中心,木讷,不会讨女孩欢心。现在的他却很绅士,也懂得制造出一点小浪漫,但是纪琴总觉得味道不一样了,现在的好,隔山隔水似的,看着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能拿在手里的是价值不菲的奢侈品,那并不是纪琴想要的。
纪琴不去兴安公司上班了,付北兴帮她弄了个设计工作室,接一些兴安公司下面公司的家装设计订单,因为有着做全职太太的惯性,纪琴也没心思做些什么,付北兴显然也没想让纪琴真正去设计什么,那设计工作室名存实亡地摆在那。
纪琴走到窗边,看着付北兴的银色的宝马开出去,心是没处放的。带着端端出去,付北兴和纪琴一人扯着端端一只手,三个人男的英俊,女的优雅,孩子聪明可爱,是让人羡慕的一家三口。但是纪琴知道,自己的幸福是偷来的,是不合法的,是没办法见天日的。
她总是做梦,被一个陌生女人扇耳光,那女人恶狠狠地骂:“你这个狐狸精,偷人家老公!”纪琴总是想张嘴说点什么,却什么话都说不出,甚至觉得自己连委屈也不必有。自己从前不听说谁家男人在外面养了小,也是痛恨的吗?现在轮到自己……
纪琴从噩梦里醒来,总要呆呆地坐上一阵子。付北兴在她身边睡得很安稳,他比七年前看起来舒服很多。男人年轻时,总有股子戾气,身上的棱角也都是分明的。年龄大了些,有了自信,也便成熟起来。
颜樱和朵渔并不知道付北兴没离婚的事。或许知道,她们都没问,她也便没有说。偶尔颜樱会问纪琴什么时候跟付北兴结婚,纪琴表面淡定地笑:“那张纸没那么重要,想结不就结了。”心里却兵荒马乱成了一团,怎么会不重要?自己真的不介意那张纸吗?
她一遍遍给自己催眠:“这样也挺好,得到那张纸的女人不照样没有爱,独守空房吗?自己得到的远比那张纸多。”可是,人总是得陇望蜀的动物,这样在一起,纪琴的心没着没落的。
付北兴从来不说他妻子的事,纪琴知道他也尽量不在她面前给那个女人打电话。但偶尔他们在一起时,那女人的电话会挤进来,开始付北兴会走到阳台,关上门,说好半天。后来,他的电话一响,纪琴就主动走开。
一次,付北兴接电话时,端端在客厅里玩飞机模型,纪琴拉着端端离开,端端正玩在兴头上,死活不肯。纪琴使劲一拽他,他大叫起来:“妈妈,你拉疼我了!”说完哇哇大哭。付北兴的脸色很难看了,急步走向阳台,说:“没有,没有,开着电视!”
纪琴把端端拉到卧室里,照着端端屁股拍了两下:“让你不听话,让你不听话!”端端越发哭得委屈,他说:“妈妈,你真的弄疼我了!妈妈,端端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纪琴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抱着端端使劲哭。付北兴开门进来看了她们一眼,纪琴以为他会说点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关上门出去了。
很晚回来,纪琴弯腰给他递拖鞋,问他吃了饭没有,他抱住纪琴,满身酒气。依旧是什么都不说,只是紧紧地抱着,黑暗里,纪琴急忙抹掉眼泪,她说:“我去给你热饭!”付北兴不让,就那样抱着纪琴,许久,纪琴抬头看他,他满脸泪痕。
谁都没再提那件事,但纪琴知道,那件事不过是个导火索,彼此都很客气,甚至是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某种平衡。
纪琴又开始失眠,焦虑,吃不下饭。付北兴很忙,却仍然抽空给纪琴买名牌包、买香水、买衣服。那些东西纪琴看了,收下,放起来,也只在跟付北兴出去时穿一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