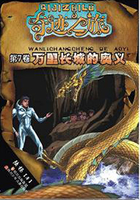肖鸿已经听到了哗哗的雨声,她决定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冬天的大雨很少见,加上大风,温度降得很明显。穿一身深灰色羊毛套裙,撑开折叠伞走进风雨。
汽车从身边驰过,车轮将积水压出清脆的刷刷声。车窗上的雨刷有规则地摆动,窗上的人脸变得模糊。到处有伞在移动。
她注意到了一个等车的女人。
为了躲雨,那女人离开站台,站到了小吃店的小屋檐下。她手里没有伞,她的头发湿漉漉地披在不肩头。肖鸿断定她是外地女人。直觉告诉她,那个女人完全孤立无助,却倔强地支撑着自己。雨雾的笼罩使天空变得昏暗,那骄傲的女人周身的寒光与痛小吃店蒸腾的热气形成了惊心的对比。她肯定什么都没吃,尽管早点铺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她面色苍白,眼珠有些红,眼眶含着倦意。她穿着件紫红色薄毛开衫,雪白的高领内衣把她的脸蛋衬得高贵冷漠。下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裤型优美流畅,有黄金分割的效果。她显得又冷又饿,却鹤立鸡群,对人间的痛苦不以为然。她觉得她是块热雾中的冰,硬撑着不让自己融化。她也像雨雾中的一团火苗,艰难地维持着自身的火焰不被风雨摧毁。
只有非凡状态中的人才有如此惊世骇俗的美,只有爱情。
肖鸿断定她刚从激情中来。她有一个情人。他们的爱情不合法。但是她和他相爱。她也许来自某个房间,在那里,她和他有一个小时的幽会。肖鸿不愿意把她的故事制造成一夜风流的通俗小说。把是个大美的女人,超越了恩怨、是非、得失,她的爱情不是享乐只能是无私的献身。她只给她一个小时,让她在一个小时中尝尽大喜大悲。她也许从遥远的地方来赴这个约会,当他沉浸在狂喜中时,她溜走了。生活无常,更何况爱!
爱情的全部光芒以一张难言的凄艳的脸浮现于雨雾中。太多的逼视与胁迫。一张爱情的脸如昙花一现,如雨水在地面汇集,玷污,流向不可知的下水道。爱情伤感。看不见的凋零。有谁说过?爱是伤害。寒气伤害那个女人,逼她就范,逼她低下高不贵的头。她被都市孤立着,被异乡的气氛吞没着。她明明爱他,为什么从他那里逃开?他们可以一起说享受逃亡者的快乐的,她为什么独自上路自我摧痛残?难道一切都只是为了不让心中的爱情流成雨雾中满街的污水?
为了不惊动她,肖鸿在站牌下站住了。这里离她有十来步远。肖鸿这时候完全把上班的事忘到了脑后。她想看清她。此刻,那个女人也注意到了她。立即,在昏暗的、大雨倾盆的清晨,两个女人的灵魂在某个关口互相吞没了对方。
当更猛烈的雨水扑在她的眼睛里她却毫无觉察任它们沿脸颊往下流时,肖鸿的心中涌起了崇拜感。那个女人在完善自己,爱情在她也许是无止境的矛盾,道德危机,谎言,自我断送。但她没有避开,就像在风雨中。肖鸿忽然想到了在丽水山区的水库看见的徐康的脊梁。英雄的脊梁。她投向他的怀抱,追逐那种崇高感,最后却离他越来越远。为什么?一张床上疏离的两个人和终身分离的两个心心相印的人意味着什么样的生活真相?如果当初肖鸿能静一静,让自己冷却下来,徐康会成为梦中白马王子,还是会成为陌生人?缘分是人制造的东西,最亲密的人是偶然的产物。承认这一点很难,事实却恰巧如此。
肖鸿看见了一只狗。
一只宠物狗,白不白黄不黄,脏兮兮的。毛又不长又厚,着水后紧紧贴在身上。脸被披下来的长毛盖住了,看不清眉眼。这决不是一只动人的狗。它说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缩着身子在街上疾走,身痛上冒着热气。
那个外地女人看见了它。此刻,她跟它一样,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把它抱在怀里。它多像无家可归的孩子。
但是,她只能目送它穿行雨中,消失在杂乱的人腿与水花丛深处。
感伤是致命的。她的脸上涌现出痛楚的神色和极大的悲悯。这一刻她彻底脆弱,仿佛就要倒毙。这一切逃不过肖鸿的眼睛。
肖鸿看见她的手移向衣袋,摸出一张IC卡。她要向谁求救?向她亲爱的人?
她将卡捏在手中。迟迟没有动手。
公共汽车开走的刹那,肖鸿从车窗里望见那个女人IC卡装回了衣袋。
清晨,独自站在雨中的外地女人和无家可归的狗提示了归宿的重要与渺小。
到了研究室,取了信件杂志,坐在椅子上翻看。所长走来,摘下眼镜说:太冷了,没什么事,回家看书去吧。
把东西收进书柜,肖鸿下了楼,朝36路车的站牌走去。
雨已经停了,但天空更加黑暗阴沉。路上行人稀少,商店显得很冷清。
清菏书店。一个好名字。公共汽车就停在书店对面。
肖鸿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男人提着一大捆书出来,拉开后车门,将书码在后排座位上。他对付书的样子叫她心疼。能大捆大捆买书而且有车送的往往不是读书人。读书人出手不会这么大方。
她想起他叫何雷。
何雷出现在这个阴暗奇寒的上午,跟那个外地女人构成了同一幅画面。这是什么兆头?
一切皆偶然。他买书就像买水果。但他出现在南大研究生考场上的时候却是另一种派头。在密密麻麻的人头中,那个穿白西服的男人分外显眼。肖鸿当时到南大去取新学期的课表,穿着一套纯白的西服套裙。这边的白与那边的白遥相呼应,那默契、那感觉简直是心领神会。当时何雷十分惊讶。这是什么样的巧合与游戏!双方都怦然心动。
当肖鸿反复回味着何雷的身影时,天空飘起了小雪,黑压压的让人喘不过气。空气中似乎飘荡着血腥味和潮湿的毛皮味。这是活禽市场特有的气味。
买只乌鸡回去炖汤吧。她这么想着,下了车,走进了一条不宽不窄的街道。
街道两侧摆满了竹笼子,里面关着鸡、鸭、鹅、兔子、鸽子……才看了两个笼子,她的视线就让屠宰场吸引去了,看得目不转睛。
宰鸡的是个年轻姑娘,看上去不满二十岁,十不分强壮。她是老板雇来的小工,杀一只鸡自己可以得五分钱。
姑娘的脸红扑扑的,脸颊处的红色被寒风点染痛得十分明显。她袖子高高卷起,一双莲藕般圆润的手臂不时着水,再让风一激,又紫又红。她哈着白气,嘴里哼着《知心爱人》,双手熟练地捏住一只鸡,用刀在脖子上一抹,随手扔进滚热的开水池。再抓起另一只,又一抹,一扔。再抓一只……约有两分钟功夫,她的手毫不迟疑地插进开水池,捞起烫透的鸡,再往滚筒式脱毛机里一扔。轰隆隆一阵响,鸡转眼间玉体横陈。
把鸡扔在案上,用刀在腹部切开,拉出内脏,就可以交给主人了。
没人跟她流水作业,她承担每一道工序。她做这一切时就站在烂泥污水中间,周身环绕着烫鸡的开水池蒸腾的热气。屠杀。血腥味。这一切之上是青春,是单纯。女孩的表情中没有恐惧,没有怜悯,只有职业的自信与愉悦。她看鸡鸭就像看某种毛坯,而她自己是艺术家。她下手极快,极狠,流畅,几乎无懈可击。
在她对面那排笼子后面,一家小吃店的三个姑娘蹲在门口洗菜。她们也是雇来的小工,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收拾得十分齐整,围在她们身边,说着挑逗的话。
她们不时扫眼去看男孩。她们的脸红红的,听到有趣的地方,就互相对对目光,拉扯一下,突然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那笑声清脆,放肆,无忧无爱虑,传染得肖鸿的心都热乎起来。
生命多么真切呀。肖鸿看着雪花灌进她们的脖子、耳朵。说一个女孩说:你好,你怎么不帮我们?
男孩支吾道:怕你们老板骂。
女孩故意叹口气:那你守在这儿做什么?
男孩道:哪个守你们了?你们也是,打把伞嘛。
女孩白他一眼:打伞?你来打呀?
男孩道:我是想打,怕人家笑。
女孩们嘻嘻嘻笑。
男孩又说:晚上去唱歌哟?
女孩头也不抬:没钱。
男孩说:我有。
女孩故意道:你有?怕在麻将桌上让人家扫光了!
女孩们又大笑。
肖鸿羡慕地看着他们说笑,心中有股暖意。
回到家,把买来的菜收拾好,肖鸿顺手拿过苏冉的新作《个人危机》坐在沙发上看。
苏冉在西方哲学研究所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她的披肩长发和纯钛架的眼镜体现了一派学者风度,对待个人生活却一反常态,从没少过闲话。三十五岁的苏冉像个时装大师,酷好奇装异服。她的眼镜仿佛有魔力,千奇百怪的衣服跟眼镜一配,立马帅呆。不知道的人说她文雅,实际上她内心狂放不羁。她认定某种东西后,根本不考虑别人怎么想。目前的风言风语围绕她跟拉萨小伙子的关系展开,成了社科院的一大艳闻。她才华横溢。在《个痛人危机》里,她用冷峻峭拔的语言分析了这一切后面的心理和道德机制。她和他没什么好谈的,也不需要谈。苏冉说文化背景般配的性关系只是交易。到了她这个层次,男人身上的光环已被看得入木三分,哪里还有戏?她只为原始意味的男子动心,在她看来,互相需要、互相渴求才是性爱的基础。她甚至细腻至极地描绘了知识女性与体力劳动者间狂热的两性生活。肖鸿不知觉中完全陷进了苏冉设下的陷阱。
《个人危机》中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