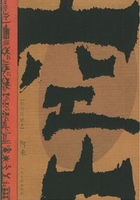1997年前后,出现了所谓亚洲金融危机,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因为亚洲的四小龙和日本是完全以城市化、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全球化为目标的,而且整个是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全球经济体系的扶助下发展起来的。当时,其繁荣一夜之间就如泡沫般爆裂了,这是什么原因?而且由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离中国非常近,一直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很多经验和模式都曾被搬到中国来,就引起了格外的警醒。同时中国也从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大家意识到: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并不是你想追求,你就能够追求得到的,比如经济发展、繁荣富裕。它受很多因素制约,比如说国情。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在美国、西方,它们现代化的前提就和我们不一样,它们先行一步,首先是能源,它们就有优势,它们已经把全世界的资源基地瓜分了,像石油、天然气什么,它抢先占了;还有人口的压力,它们通过开发所谓新大陆,殖民主义,已经成功转嫁危机了,过剩的人口也向外转移了——从欧洲向美洲、澳洲转移,而美国,本身是一个新大陆,它没有那些人口问题。但亚洲不一样,亚洲国家没有办法转移这些问题。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历史背景都完全不一样了。应该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它使很多人意识到,以前的目标是有问题的。于是一切归结到一点: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如果中国也想现代化,那么到底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面对这一问题,知识分子中的争论更加深入。而且是,在人文精神大讨论引发知识分子分化后,关于这一更重大的问题的讨论,导致了批判性知识分子内部也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我称之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左右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还是应该以西方为主导,对内倡导诸如自由、民主、法制、宪政等观念,来取代旧的意识形态与体制,对外则继续开放、彻底走市场经济之路。他们认为中国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学西方学得还不够,还不彻底,受到了原有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阻挠,以至“四不像”。所以要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而不是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四不像”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完完全全融入美国主导的所谓世界文明体系。他们还对所谓“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指出模拟复制欧美式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证据。而发达的欧美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也不愿看到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崛起,来分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赚取的红利。所以,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不管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知识分子都试图就新的问题和情况,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解决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方案。
这个阶段,我个人称之为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路线”进行反省、思索、讨论的“总体性反思阶段”。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反思阶段,当然,其原因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各种新的情况出现了,各种原来潜伏累积的问题暴露了。
于是,继从文学界、文化界开始的,就信仰啊、道德价值啊等展开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后,社会问题的讨论开始深入经济、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家等也开始介入,如当时的胡鞍钢、崔之元、王绍光、黄平、何清涟、秦晖、梁治平、朱苏力、贺卫方、刘军宁、韩德强、卢周来、任剑涛等,还有一些敏感的人文综合性知识分子如汪晖、李陀、徐友渔、王小东、萧功秦、南帆、韩毓海、旷新年等,以及原来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活跃的王晓明、朱学勤、韩少功等也加入进来。这个“总体性反思与争论”的阶段,后来被一些人称之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讨论”,其实质,就是围绕着在“新的情况下,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一条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而展开的。《天涯》由于原来就囊括了左的和右的所谓批判性知识分子,得以全面发动、介入、参与这次讨论。对于这次讨论,我个人的看法是,它实际上是一次全方位各领域的全面大讨论。从《天涯》所刊登的众多文章总结概括来看,应有尽有。比如说关于信仰的问题,参与者有张志扬、北村等;关于西方中心论的反省,参与者有张宽、崔之元等;关于中西文化比较,参与者有李陀、张宽、李欧梵、李锐、冯骥才等;关于理想与世俗的冲突,参与者有韩少功、朱学勤、史铁生、陈村、张汝伦、蒋子丹等;关于土地与人民的关系,参与者有张承志、张炜;也有关于公共空间与作家写作个人化的关系,像周国平、于坚、南帆、余华、李皖、吴亮都参与了;也有关于经济发展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像当时的何清涟、包括实业家像冯仑……他们都参与了。当时确实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反思。
我现在个人回忆起当时发起这些讨论的初衷,根据我当时的观察和事后的总结回顾,我觉得在这个总体性反思中主要有三个比较突出的讨论:第一个是“本土国情与什么样的发展观”的讨论。在当时强调经济发展至上、GDP至上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天涯》杂志是比较早地提出“什么样的发展”这样一种概念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是可持续性的发展,还是仅仅以GDP为指标,破坏环境、破坏生态的发展?这个其实就是涉及到本土国情的讨论。当时一些学者像黄平、秦晖、房宁、韩毓海、何清涟、韩德强、卢周来等,他们都就这个问题在《天涯》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另外与之配合,《天涯》还介绍引进了国际上的一些思考和资料,像华勒斯坦、斯蒂格里兹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主张可持续的发展,主张科学的发展观,探讨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第二个就是由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在《天涯》1997年第五期)而引发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当时参与者就非常多了。应该说这篇文章引发了中国思想界本身的一个分化。在1980年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经济建设、思想解放……知识分子的想法也基本是统一的,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啊。但到了这个时候出现了分化。对中国的道路究竟该往何处去,中国到底该怎么走,开始出现了一些争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其实只是其中的比较引人注目的两种声音。这次争论把几乎所有具有或自认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全部卷进来了,都参与了这个讨论。当然争论的场地不限于《天涯》,但《天涯》无疑是这次争论的主战场,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而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新的主张,比如说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也在《天涯》上亮相。
第三个比较突出的讨论就是有关生态问题的讨论。在2000年第一期,《天涯》发表了一篇叫作《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谈生态—环境?》的文章。后来反响特别大。这实际是《天涯》发起的一个讨论生态—环境问题会议的纪录整理。当时很多的学者和作家,像李陀、黄平、韩少功、陈思和、王晓明、南帆、耿占春、方方、苏童、格非等都参加了会议的讨论,其中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综合性问题,其实质是公平公正问题,一些人享受生态环境破坏的好处,另一些人则承担代价。这个讨论纪要发表后反响特别大,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成七八种文字。直到前年,像《自然之友》这样的杂志还把它拿出来重登。
在这个阶段的反思,还都是一种总体性的、宏观性的反思。配合这种反思,当时在韩少功的提议下,《天涯》推出了“特别报道”这样一个栏目。比如《亚洲金融泡沫的破灭》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韩少功本人写的,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做了一个深入的分析报道;另外像《中国:入关不入套》,应该说是中国最早公开发表的对于中国要不要加入WTO的一个质疑,这篇文章当时实际上是韩德强写的,但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使用真名,用的是化名,叫“绍人”。这篇文章最早是在网络上发表的,引起了极大反响。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社会精英抑或普通百姓中间,都认为中国一加入WTO,就相当于马上进入“共产主义”了,可以说是全民欢庆,万众欢呼,在这个时候对于加入WTO提出质疑,是非常罕见,也需要相当勇气的,这也算是“特别报道”。这些“特别报道”,都是配合总体性反思的,以一种不那么理论化的、相对活泼的、可读性较强的形式,来进行一种思考,并具有启迪他人与民众的作用。
在总体性反思达到一定程度后,学术思想界敏锐的部分人士就开始进入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和深入研究了。而恰好,这是就出现了一个“三农问题”。
正好就是2000年前后,总体性的反思阶段进行得差不多了,面临一个突破。而《天涯》与《读书》杂志几乎同时,“发现”了一个叫温铁军的学者。温铁军是一个“三农问题”专家,但很长一段时间不太敢出来公开发言,因为上上下下都在提倡“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若突然揭开真相说中国还有八亿农民,还有百分之七十的广大农村,那不是相当于揭自己的“家丑”吗?温铁军当时只是偶尔在一些小会议上讲讲话,在很专业的网络发点文章,而几乎就在同时,先是《读书》发表了他的后来引起强烈反响的《世纪末的三农问题反思》,接着,《天涯》发表了他的《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温铁军其实不过指出了一个根本的事实: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国家,农业是中国的软肋,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农村是中国的基础,“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而这些,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他还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不是个别人的现代化,是人民的现代化,是整个中国的、人民的、大众的现代化。
我个人觉得,在总体性反思之后,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之后,在知识界高谈主义、陷入名词游戏之时,一个具体的问题生生地切进来了,这就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一下子激发了兴奋与思考,中国知识界也得以走出主义的圈套与误区,开始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国土。“三农问题”开始,知识界的很多讨论开始进入了一种具体的、微观的问题的讨论,甚至开始进入了日常生活层面的讨论。
而《天涯》也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契机。《天涯》这本杂志,一直有自己的目标或者说是主导,就是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就是说不要局限于“主义”的讨论,还要进入具体的“问题”。这也一直是《天涯》编辑部的一个共识:问题与主义并重。光谈主义,没有问题,很可能流于空洞,比如说有一些杂志,几乎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中转站,内容空泛,热衷于介绍美国啊、法国啊一些情况,反而漠视中国自己的现实,跟中国读者隔得很远,当然他们的理论可能也是新鲜的,但是仅仅局限于一些理论的介绍,那就可能走向空谈主义。还有一些杂志,注重具体问题,但缺乏大的宏观的主义的关照,就变成专谈问题,没有主义,过于琐碎化、专业化,或者成了国策的、具体的战略探讨,没有广大的人文关怀,不能深入更多人的心里。而《天涯》这些处理、把握得比较好。
从“三农问题”开始,《天涯》将具体问题深化下去。比如当时曹锦清的纪录分析国情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著作《黄河边的中国》刚出来,《天涯》就马上组织讨论。曹锦清说:你要了解中国,你就必须要了解黄河,因为黄河是中国的发源地,是农业的发源地,黄河流域是中国最贫困的、矛盾最深、冲突最多的一个地方。《天涯》当时将《黄河边的中国》作了专题讨论,在国内的刊物也是第一家,韩德强、温铁军、房宁等都参与了讨论。后来,随着“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入,《天涯》又将这一问题延伸到“三农”理论中的忽略了的文化问题。确实,在人们讨论三农问题的时候,更多地是关注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农民作为主体、或者说是农民的“文化”问题被忽略了。2003年,人文学者王晓明到一些乡村去考察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乡村本土文化建设被忽视,农民被客体化,农民作为主体本身的文化被忽视。人们总以为,农村的经济问题解决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农民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都没有得到过应有的重视。这个讨论很快引起反响,吴重庆、薛毅、周立、石勇、梁卫星等都参与了讨论。而有意思的是,这次讨论的参与者不全是学者,还有一些现在就生活在乡村的人,比如梁卫星,他就是湖北一个乡村老师。湖北这个地方,是农村问题比较多的,出了像李昌平这样的人。梁卫星一个乡村教师,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些观点也很有意思,比如像吴重庆,他主张挖掘乡村传统的“儒学资源”来重建乡村文化。这个讨论进行了一段时间,很巧合地,最近上面提出了一个“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而《天涯》起码早了四五年时间就已经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