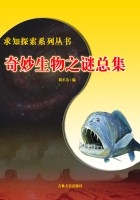太阳累了,来不及与月亮打招呼,如醉酒般红着脸颊,匆匆沉入西山休息去了。镰刀似的弯月虽稍感诧异,但想到自己的职责,仍准时爬上了天空,大地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纱。
密林深处,捕鼠协会主席猫头鹰先生坐在一棵被锯得离地只剩一尺的松树墩旁,直愣愣地看着松树墩上捕鼠协会的大印。这位德高望重的主席,为保护人类的丰收成果立下了汗马功劳,多次荣获“田园卫士”金质奖章。
开会时间就要到了,几把椅子空着,不见一个理事到场。要知道,猫头鹰主席他是最讨厌开会迟到的。
一阵“嗦嗦”声从草丛中传来。猫头鹰高声喊道:“喂,老蛇,老蛇博士,你可快点呀!”
捕鼠专家、捕鼠协会理事老蛇来到桌旁。猫头鹰主席起身示意让蛇坐下。
老蛇看到猫头鹰主席走路一拐一拐的,就问:“哎,你的腿怎么啦?”
猫头鹰主席听他这么问,摸着左腿,说:“哎——叫我怎么说呢?今天上午……”
正在这时,灭鼠学院捕杀系两位教授黄鼠狼和貉气喘吁吁跑到了会场:“哎呀,险些迟到了。”
猫头鹰主席清清嗓子,准备开会。
“猫秘书长还没到哩。”貉教授提示说。
“哟,真的还差协会秘书长猫女士呢。开会要做记录,她可是从不迟到的呀。”
“不等她,”猫头鹰主席说,“黄教授做记录吧。”
黄鼠狼教授正要答话,只见灭鼠研究所所长兼捕鼠协会秘书长猫女士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猫头鹰主席连忙迎上去搀扶着:“猫所长,你这是怎么哪?”貉教授连忙搬来一只椅子,让猫女士坐下。
猫女士艰难地抬起头。她两眼红肿,两颊挂着泪痕,未曾开言,已泪流满面:“昨天上午,我丈夫出去捕捉老鼠做标本,到了下午5点钟还没有回来。我们研究所的全体同仁出动,帮忙寻找,才知道他被人绑架,装上开往某地的火车站。那里的人们可是顶喜欢吃猫肉的呀。”说到这里,猫女士又后怕得几昏倒过去。将心比心,丈夫要被杀,哪个妻子不痛心呢?
猫女士接着说:“祸不单行哪——就在晚上,几个孩子见我悲伤,他们捉了几只老鼠。一家子草草吃下,这下更惨了。不等天亮,我的一儿一女在床上翻滚,哭爹叫娘地喊肚子痛。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是食物中毒。这是因为人类一味地用毒药杀鼠,才搞得我们误食后间接中毒的呀!不一会,我的儿子、我的姑娘全都断了气。我也头昏眼花,四肢发麻,腹如刀绞。幸亏我悲伤之中,吃得较少,才没有死去。可是,可是,我已经家破人亡了啊……”说到这里,猫女士顿时泣不成声。
黄鼠狼教授是个感情型的学者,尤其见不得女士伤心,他自然也泪流满面;貉教授虽然生性刚强,这时也耷下脑袋;猫头鹰主席同大家一起站起来,低着头。空旷的大会场显得悲哀、肃静。
三分钟默哀过去了,猫头鹰主席抬起头来,说道:“我的心情非常沉痛。要知道,猫家每年可生六七个孩子。全家每天只说吃十只老鼠,一年就可消灭几千只老鼠啊!可是,它们死了,永远离开了我们……”
猫头鹰主席宣布开会,他说:“自从上面提倡精简会议以来,我们开会很少。今天开会事先没有商量,请大家原谅。我召集大家来,是因为我决定辞职,辞去捕鼠协会主席之职。”
他的话如同投下了一颗炸弹,几个理事都惊呆了,一个个睁大眼睛望着这位能力非凡的主席。
猫头鹰接着说:“各位现在开始推荐选举新的主席。”他拿起那枚协会大印,在大家面前晃动,似乎要立即转交给其中一位。理事们瞠目结舌,身子直向后仰。
黄鼠狼教授再也忍不住了,说:“主席,你这是为的什么?难道说有哪一位不服从你的领导?”
“不,绝对不是。”
“那,你与老鼠们握手言欢了?”
“胡说!”主席先生发火了,“我永远不会饶恕鼠类。且不说它们传染鼠疫、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等可怕的疾病;且不说它们咬坏衣物、盗窃粮食;光是它们那种鬼鬼祟祟的样子,就够我厌恶。每个夜晚我都要捕食两三只老鼠,按每只老鼠每年吃粮六斤计算,一年内我就鼠口夺粮几千斤。以此成绩,我觉得我担任协会主席并不过分,我也感到非常自豪。”说到这里,他放慢了语调,“可现在,我不行啦,我不称职了。”
猫头鹰主席挪动了一下那条跛腿:“现在,许多人,各位,我说的是用两只脚在地上走的人,专门捕杀我的家族,把我们的躯体当作酒席上的美味佳肴。当然,他们也捕杀别的鸟类。他们的主要办法就是枪杀。什么单筒猎枪、双筒猎枪、低压气枪、高压气枪、洋枪、土枪、还有小口径步枪,品种繁多,无奇不有。搞得我提心吊胆、东奔西躲。我是上夜班的,应该白天休息,可他们正是白天出动。今天上午,我在森林边一棵大树上面休息,猛然间“砰”的一声枪响,我全身一颤,险些从树上跌落下来,我拼命地飞进密林深处。当我歇下来时,只觉得浑身发热口里发干,腿痛得厉害。一看,血顺着大腿一直流到爪子上。结果,我眼睁睁地看着老鼠却不能出击。现在,我不仅腿受了伤,而且神经也受了伤。一听到枪响,一见到猎枪,我就发抖。我这种状况,哪里还能胜任协会主席?所以,我必须辞职,至多当一名理事而已。“黄鼠狼教授听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辞职理由不充足。你说的情况,还没有我的严重。本来,我对灭鼠有一定的研究,我的身材,我的嗅觉,也适宜捕鼠。不是我黄某吹牛,老鼠藏进了洞穴,我也能够抓获归案。这几年,我也发表了几篇论文。可是,每到冬天,人们就捕杀我们,剥取毛皮,说是换外汇,创造经济效益,他们搞得太过分了,恨不得叫我断子绝孙。他们捕杀方法之多,你们无法想象:什么夹子、关笼、铁钩、翻板,千奇百怪,花样繁多。这些是明杀,还算好躲;暗毒可就难防了,嗅又嗅不出来,看又看不清楚,一吃就丢命。猫所长食物中毒,还属误食,人们并不是有意为之,可对于我们,他们却是专门研究,毒药下在我们家族最喜欢的食物里面,并且放在我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比如说今天,我就险些见不到各位。刚才赶来开会,实指望提前到达,帮忙布置会场,哪晓得走到路上,不留心踩着一个隐蔽得十分巧妙的夹子,要不是我年轻力壮,拼命挣脱了夹子,还有我吗?这不,腿子卡了一道青圈,肿得像棒槌。这些都不说,更恼火的是,我忠心耿耿为人类捕鼠,却要戴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说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说句良心话,偶尔确实会发生个别黄鼠狼偷鸡事件,可那只是我的少数同类饿极了才干的。我也经常对那些伙计进行教育。难道说,我们的灭鼠功劳就因为一两只鸡而抹去?难道说,我的这顶反动物帽子要带到棺材里面,永不昭雪?”
猫头鹰主席劝道:“哎,那是误会,人类终究会理解你的。”
“理解不理解,我不在乎,不过,我是肯定不能当主席的。你要交印,交给猫所长。”
猫女士瞪着黄鼠狼,说:“黄教授,你什么时候学会挖苦人?我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哪有心思接印当主席?”
猫头鹰主席见他俩都说得在理,也不好勉强,于是请蛇博士接印。
蛇博士想了片刻,才慢条斯理地说:“你们把问题摆出来了。我呢?日子也不好过。是的,我是捕鼠博士,我可以在老鼠洞里睡觉,我攻入它们的大本营不费吹灰之力,我的同类中的大肚汉一天可以吃掉上十只老鼠,只要是我们家族兴旺的地方,老鼠就少得可怜。正因为这些成绩,我通过了捕鼠博士学位考试。现在,你们要我当主席,我很高兴。可是,我已经性命难保了,还当什么主席?近年来,人们填塘造田,挖沟刨坟,再加上大量施用剧毒农药,使得我们无处安身。有些人见着我就捉,弄去做酒席上的美肴:配上鸡肉,就称为‘龙凤席’;配上猫所长的家族,就称为‘龙虎斗’。还有人见了我们就打,不打死不放手,说是‘见蛇不打,死了变马’。眼见我的家族要断烟火了,我还当什么主席?”
就剩下最后一位没有表态的理事——貉教授,参会者的目光一齐投向貉。
“你们莫作我当主席的指望,别让人把捕鼠协会的名声说坏了。”貉教授慢吞吞地说,“你们知道,我们貉又叫狸,但不管是叫貉还是叫狸,在人们心目中都不是好家伙。你说叫貉吧,只要是恶性一样的坏人,人们就拿我们开涮、贬损,什么‘一丘之貉’。叫狸吧,人们又硬要将我们和狐连在一起辱骂,口口声声狡猾的狐狸。狸和狐虽然同属食肉兽中的犬类,但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一,我们的身体比狐胖;其二,我们的四肢比狐短;其三,我们的尾巴没有狐的长;其四,我们的毛色棕灰,狐多为红褐。这应该很清楚吧!可面对那些好坏不分、胡拉硬扯的人们,我当这个主席有什么意思?!”
蛇博士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你当你的主席,管人家怎么说。”
“不行,不行。我是懒汉。”貉教授不好意思地连连摇头。这话不假,貉一般自己不挖掘巢穴,而是利用倾倒的树木或大树根部与地面的空隙,或者狐等野兽的旧空巢,或者空屋的地板充当巢穴。只要觉得住着舒服,就会在那里安家。特别是寒冬腊月,貉和熊一样,躲在巢穴中过冬,一住一个月足不出屋。
猫头鹰主席不知如何是好,捧着大印无法交出。他只得再次向理事们解释:“目前,鼠害成灾,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总得选出一个得力的、能力强、主动性也强的专家来主持日常工作啊?”
黄鼠狼教授把帽子往地下一甩,吼道:“干脆各取所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管它老鼠不老鼠,反正也不能怪我们,这是人类逼的。”
“胡说!”猫头鹰主席发了火:“亏你还是理事,竟说出这种话来。如今,残杀我们的人有,可赞颂我们的人也有哇!我提出的是交印,根本没说改行。这印,我不交了!“看见主席发了火,黄教授不做声了。这时,蛇博士开了口:“我有一个办法,也许有希望改变目前的局面。”
大家催他快讲。蛇博士很有信心的说:“人类有一个组织,叫做科学知识普及委员会,我们联名写信,请这个组织呼吁一下:再不要捕杀我们了!”
大家齐声称赞这个主意好。
信,当场由猫头鹰主席执笔写成,众理事签名,当天寄出。
直到今天,动物捕鼠协会还在等待人类科普协会的回信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