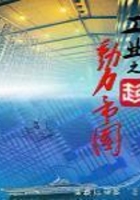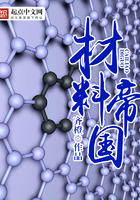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就是遇上东北三侠的那段日子。
大侠来的时候带着墨镜,头发不知是被吹风机吹得还是被飞驰的电动车吹得,一柱擎天的立着,我正在床上躺着看电视,见到他进来,一下坐了起来,将床头上的钱包和手机快速攥在手里,心里默不作声着“天还没黑呢?你就想入室抢劫啊?”
大侠指了指我对面的那张床,问我“兄弟,这张床有没有人住?”
像是有一辆时速300多迈的电动车从我身上驶了过去,把我的小心肝轧的七零八落,我是被大侠说出这句话时的腔调震住了,充斥脑子里的全是斧头帮,山口组,黑手党认真工作时的镜头,我那弱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短短的半分钟里,至少被KO了一百多次。
“兄弟,这张床有没有人住?”
“没有,没有,没有。”我绷着一身鸡皮疙瘩,玩命的点着头。
大侠指的那张床真的没有人住,所以我才告诉他“没有,没有,没有。”如果那张床真的有人住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对他说“大哥,你睡我这张床吧,我睡地上。”
大侠将床上放着的瓶瓶罐罐收拾到了上铺,在把最后一个可乐瓶放在上铺的那一刻,大侠就像一台正在高速运转的机器由于链条突然崩断而瞬间停了下来,如山一般矗立着,我虽然只能看到大侠伟岸的背影,但大侠一系列的肢体语言告诉我“怎么上面还有一张床啊?”
大侠一定是愤怒的,大侠心里此刻想着的一定是‘我为什么不直接睡在光滑的如同少女肌肤的上铺?又为什么非要花半个多钟头的时间把下铺上的一瓶瓶一罐罐挪到上铺,然后再睡在下铺上?’
关于这两个疑问,我当时没敢问,因为我担心在我提出这两个问题之后,大侠会像挪瓶瓶罐罐一样,把我从窗口直接挪到楼下去,不耻下问有时也要看看情况。
过了好久好久,大侠终于从深深的自责里走了出来,坐在了床上,夕阳的光从窗外透进来,在墨镜的两只镜片上轻轻晃动,大侠抬着头挺着胸,暗淡的黄洒在他身上,显得异常雄浑悲壮。
看着如此美妙的情景,不耻下问的优秀品性又像一头脱了缰的小野马,哒哒哒爬上了我内心深处的小山丘,我只是好想问大侠“大哥,天都这么黑了,您还戴着墨镜,还能看得见吗?”
这个疑问也像前两个疑问一样被我深深埋在了心底,我只是不知道当大侠回答我‘他戴的不是墨镜,是夜视仪’的时候,我该怎么把话接下去,那样的话岂不是向大侠证明我真的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毕业的学生?
过了好久好久,一个细微的动作终于打破了宁静,我看到大侠的身体轻轻抖动了一下,听到了大侠低沉而又略带颤抖的声音“兄弟,厕所在几楼?”
“一楼。”
大侠嗖的一声蹿到门口,像一阵风一样,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忙冲着正欲飞奔而去的大侠喊道“厕所里没灯。”
正欲飞奔而去的大侠似乎突然也想到了什么,嗖一声回到了床前,伸出两只手,一把将墨镜摘下,又嗖一声蹿了出去,还是像一阵风一样。
我一直觉得大侠在摘下墨镜的时候动作应该再慢点,最好是伸出一只手来,因为这样会很容易让我激起像郭襄看到杨过摘下面具时迸发的激动与惊喜。
“兄弟,刚才多谢了。”一只宽厚有力的大手搭在我羸弱的肩膀上,我感到屁股下的床垫瞬间下沉了半米多。
“没什么,没什么。”我在这一刻突然谦逊了起来,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的我会突然谦逊了起来。
“兄弟,QQ号是多少?”
“这也太直接了吧?我们才刚刚认识几分钟,就这样套近乎?虽然不知道你的家庭,你的背景,但最起码得让我知道你的性取向吧?”我看着大侠正义凛然的眼睛,又看看大侠搭在我肩上千斤重的手,突然就意识到,大侠其实是个可以信任的人。
我把大侠的号码打进了搜索框,然后看到了几个字‘我是小红帽’我偷偷看了大侠一眼,发现他正在看着我,他似笑非笑的眼神告诉我‘看什么看,我就是小红帽。’
我又看到了紧挨着‘我是小红帽’下方的一行字‘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记忆一直在这道忧伤里彷徨,彷徨的让我迷失了方向,错过了姑娘。’
我看着大侠,忽然看到了一袭黑袍的杜月笙,手拿两把大板斧,站在把悲伤逆流成河的悬崖上,指着河里的小混混,一脸忧伤的说“快把我的青春还给我。”
二侠来的时候,我和大侠正躺在床上打着魔兽,我清晰的记得二侠进门之后的那个表情,像是一个上了十几年高三的孩子在高考结束后走进了网吧里,又像是一个掉队多年的老同志一下又找打了组织,高兴与激动的泪水顺着二侠那张正宗的猪腰子脸哗哗往下淌,我们三人坐在波涛汹涌的浪花里,相拥而泣。
“兄弟,这张床有人住吗?”二侠指着大侠上铺的那张床问。
幸好二侠指的是那张床,问的是我,如若问的是大侠的话,我一定会听到一个自由落体的声音,还有二侠惨绝人寰的哀号,因为上铺的那张床写满了大侠伤心的回忆,已经逆流成河,成江,成海。
“没有,没有,没有。”我绷着一身鸡皮疙瘩,没命的点着头。
在大侠来的时候,我已经用过这个动作,虽然这个动作很酷,但追求标新立异的我还是不屑于重复,不过望着被二侠八块腹肌撑起的印有龙头的T恤衫,我当即就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把这个动作再重复一遍,这个动作虽说缺乏创意,但确实管用。
二侠把大侠挪上去的瓶瓶罐罐又挪了下来,每一个瓶瓶罐罐里都装满了大侠辛勤的汗水,二侠的每一个动作里都满载着对一个前辈深深的敬意,一直盯着怪物不放的大侠偶尔也会盯上正在辛勤忙碌的二侠一眼,在大侠满含深情却稍纵即逝的一瞥中,潜伏着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担心:你小子挪瓶瓶罐罐的速度千万不能超过我。
“兄弟,这张桌子有没有人用?”二侠指着墙角的一张桌子问。
我听到了大侠的鼠标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的声响,我又一次看到大侠在把最后一个可乐瓶放在上铺时的那副表情,眼睛睁的大大,嘴巴张的像河马,我听到河马在说话“怎么还有桌子啊?”
“没,有,没,有,没,有。”大侠把这六个字拆成了六句话,每一句话之间的间隔都很长,大侠一定很生气,生他没有把遮住桌子的那块布掀起来的气,只能眼睁睁看着二侠把桌布掀起来,把电脑放上去,我也很生气,生大侠为什么还不把鼠标捡起来,还不过来帮我一起打怪兽的气。
二侠一定是一个电脑高手,否则的话也不会把开机画面弄得那样热血沸腾,那样励志,黑黑的显示屏上出现了用3D文字写就的两行对仗工整的话“要想人前贵,背后得遭罪。”
二侠伟岸的背影把那一刻的我衬托的好渺小,我看到一个巨人站在了我面前,眺望着大海,我没有站在巨人的肩上,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身后,我看不到大海,甚至连大海的声音都听不到,巨人已经成了巨人,仍旧在拼搏,我却躲在巨人的阴影里,不断在堕落,巨人如若此刻回过头来的话,我一定会没有勇气注视巨人那双战斗不止的目光。
然而,巨人真的在此刻回过了头来,一脸微笑的望着我“兄弟,玩不玩CF?”
我摇了摇头。
然后,我听到了从巨人面前的那片海里传来了‘clear,over,fuck!!’的海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