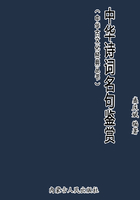巴金
俄国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在1855年开始的二十一年之间写了六部长篇小说(作者自己称为中篇小说)。其中影响最大、最好的一部就是《父与子》。这是六部小说中的第四部。1860年冬天作者开始写《父与子》,到1861年7月完成。小说发表、出版于1862年。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像它这样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的。
作者怎样想起写这部小说呢?据他自己说:
“我最初想到写《父与子》还是1860年8月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在怀特岛上的文特纳尔洗海水澡……”
“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基础,是一个叫我大为惊叹的外省医生的性格(他在1860年以前不久逝世)。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
“那个典型很早就已经引起我的注意了。那是在1860年,有一次我在德国旅行,在车上遇见一个年轻的俄国医生。他有肺病。他是一个高个子,有黑头发,皮肤带青铜色。我跟他谈话,他那锋利而独特的见解使我吃惊。在两小时以后,我们就分别了。我的小说就完成了。我花了两年的工夫来写它……这不过是埋头去写一部已经完全想好了的作品罢了。”
标题《父与子》就说明了小说的内容。作者写的是父亲一代和儿子一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写的是具有科学思想和献身精神的青年和标榜自由主义却不肯丢开旧传统的贵族之间的斗争。在新旧两代的斗争中,作者认为他的同情是在年轻人的方面。
可是完全和作者的预料相反,小说引起了那么多互相矛盾的批评和那么长久激烈的争论,小说给作者招引来那么多的误解。保守派抱怨他把“虚无主义者”“捧得很高”;进步人士却责备他“侮辱了年轻的一代”;年轻人愤怒地抗议他给他们绘了一幅“最恶毒的讽刺画”;上了年纪的人讥笑他“拜倒在巴扎罗夫的脚下”。在彼得堡发生大火灾的时候,一个熟人遇见作者就说:“请看,您的虚无主义者干的好事!放火烧彼得堡!”使作者感到最头痛的是:“许多接近和同情我的人对我表示一种近乎愤怒的冷漠,而从我所憎恶的一帮人,从敌人那里,我却受到了祝贺,他们差不多要来吻我了。这叫我感到窘迫……感到痛苦。”
作者痛苦地说:“这部中篇小说使我失去了(而且好像是永远地)俄国的年轻一代人对我的好感。”这对作者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恢复过来。他寂寞地死在法国。
我在1978年校阅我这个旧译本,再过五年便是屠格涅夫逝世的一百周年纪念。一百多年前的激烈争论早已平息,对作者的种种误解也已消除。九十五年前作者在法国病逝,遗体运回彼得堡安葬的时候,民意党人曾散发传单,以俄罗斯革命青年的名义向死者致敬,这是最大的和解了。
说到《父与子》,我同意屠格涅夫的话。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的身上,作者的确“用尽了”他“所能使用的颜色”。他对自己创造的典型人物感到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他认为巴扎罗夫是“一个预言家,一个大人物,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固然他写了巴扎罗夫的死,但他是把巴扎罗夫看做一个生在时代之前的人,因此把他放在和他格格不入的社会环境中,使他显得很孤单,还给他安排了一个过早死亡的结局。而且他写到巴扎罗夫死的时候,还流过眼泪。他甚至说巴扎罗夫是他的“心爱的孩子”。这都不是假话。然而作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改良派、西欧派。他不会真正理解巴扎罗夫,也不可能真正地爱巴扎罗夫。他只是凭着自己对俄罗斯社会生活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凭着他的艺术的概括力量,看到了一代新的人,知道这新人——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定要压倒过去的一代人物。他称巴扎罗夫为“虚无主义者”。他创造了这个词。他又在私人通信中解释道:“虚无主义者——这就是革命者。”这个词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普遍地被采用,用来称呼一切反对沙皇政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党派。民意党人司捷普尼雅克在他的着作《地下的俄罗斯》(1882)的开头就说“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名声自然将由他着作而长存于后代,但是只靠一个词他也可以不朽了。他就是第一个使‘虚无主义’这个词的人”。
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时候,巴扎罗夫这个新人刚刚诞生,一般人对他还很生疏。但是不久,这样的新人便大量出现,像“大自然是一座工厂”、“拉斐尔没有一点用处”这一类话已经成了“虚无主义者”常用的警句。他们是严肃地相信这一切,并且准备为它们献身。这般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到了七十年代,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就让位给另一代新人了,那就是“到民间去”的“民意党的英雄”们。然后,又出现了同工人紧密结合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战士……但是远在法国的衰老的屠洛涅夫已经无法理解而且也来不及在新的作品中反映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是在1876年脱稿的。他把年轻的涅日达诺夫(《处女地》的主人公)几乎写成了像他自己那样的人。然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在《处女地》后记中写的那一段话:“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他知道革命必然要来……而且要改变当时存在的一切。”也就是1883年民意党人在散发的传单上所说的:“也许他甚至不希望发生革命,而只是一个诚恳的‘渐进主义者’……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用他作品里的真挚的思想为俄罗斯革命服务过,他爱护过革命青年。”
屠格涅夫“想通过主人公的形象把迅速嬗变中的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加以典型的艺术概括”,他的六部长篇小说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写出了数十年间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艺术编年史”。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新人巴扎罗夫早已归于尘土,可是小说中新旧两代的斗争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对于这个斗争屠格涅夫是深有体会的,他本人就同他的母亲(短篇《木木》中的地方婆)斗争了一生。但是他母亲所代表、所体现的一切在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中已经化为灰烬,找不到一点痕迹了。旧的要衰老,要死亡,新的要发展,要壮大;旧的要让位给新的,进步的要赶走落后的——这是无可改变的真理。即使作者描写了新人巴扎罗夫的死亡,也改变不了这个真理。重读屠格涅夫的这部小说,我感到精神振奋,我对这个真理的信仰加强了。
(原载1979年8月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