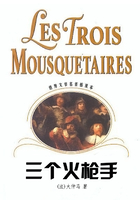江子
火
播火者欧阳洛首先是一名年轻的农民,他从小生长在江西永新的一个叫田南阳家村的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他家有七亩薄田,好歹也算是有田产的家庭,可是他家人口众多,共有九人,七亩薄田自然就不是大产。穷困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一家的命运。
青年农民欧阳洛出生于1900年。他在乡村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像所有的农民那样,他遵守古老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熟悉田地里的一切活计,也与无数大到牛羊小到昆虫之类的生灵保持天然友好的亲属关系。像所有农民那样,他对乡村谈不上热爱也说不上憎恨。他完全可以像所有农民那样活着,娶亲生子,没日没夜地劳作一生,老了找村庄后面山上的一抔黄土埋掉拉倒。没有人说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对。
然而欧阳洛同时也是一个读书人。他的父亲是一名教经馆的秀才,欧阳洛10岁开始跟随父亲读书写字。相比村里同龄的人,欧阳洛自然有了一个不同的文字世界。他除了是农民的后代,还是孔子的门生。文字有了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张望的勇气和能力。他渴望求索,渴望用自己的学识换得比农民更好一些的生活,渴望走出大山的围困,跟着水流去寻找人生新的可能。读过书的欧阳洛经常在农事间隙发呆。在田野中,山麓下,溪水旁,他孤单的样子让人不解。他在想些什么呢?
1922年,22岁的欧阳洛上路了。那是8月,天气酷热。走出家门的欧阳洛应该带着一个书箱,里面有他的换洗衣服和一些类似于《稀世贤文》《论语》之类的书籍。那是他的父亲的经馆教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考学的工具。也许还会有一些在路上应急的干粮,这里按下不赘。8月的欧阳洛应该穿着短衫。像那时候每一个出门远行的乡村人那样,他的手上也许绑着一条毛巾。太阳暴烈,他不停地用毛巾擦汗。可是汗水不停地爆出来,他的毛巾早已经彻底湿了。他的身体似乎要浸在汗里。他的汗衫已经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汗馊味,可他毫不以为意。梦想中的前程在鼓舞着他,他已经走得很累了,依然不肯停下来歇息。这个懵懂无知的乡村青年,对自己的未来心怀期待,对即将抵达的城市多少显得好奇而惶恐。他的将来,是要做一名传道授业的教书先生,还是到衙门里当一名公差?
经过数日的行走,他来到了江西省会南昌。凭着他父亲教给的文化基础,欧阳洛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了省城名副其实的一名学子。
然而,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川、滇、黔军阀战争爆发。直皖军阀大战爆发。今天穿黄色军装的军爷占领了城池,明天穿灰色服装的兵哥扬言要血债血还。北洋军阀吴佩孚扬言要武力统一中国—类似的杀气腾腾的声音在中国此起彼伏。整个中国军阀混战,硝烟四起,百姓流离失所。内战不已,列强趁火打劫。日本就山东问题向中国发出通牒。英美等势力国家在中国天津、上海等地盘踞。人祸不已,天灾也来助兴。宁夏海源地区发生8.5级大地震,数十万人成为死难者。水漫浙江,数万人无家可归……
混乱不堪、积贫积弱的中国需要拯救,不断告急的国势呼唤挽狂澜于即倒的英雄。几年前的五四运动余温依在,反帝反封建的声音已经深入民心。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即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本党纲领,其结果是迅速得到全中国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马克思主义像个幽灵,开始徘徊在中国大小城市的街头,《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红灯》这些新思想的杂志在各校园之间秘密流传。城市的偏僻角落或郊区地带,大学的隐秘据点,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集会在激烈进行。争论从来没有休止,因为很多理论需要厘清,很多事件的真相没有头绪。而门外的路灯下有人形迹可疑,那如果不是闻风而动的特务,就是集会安排的假装若无其事的放哨的人……
满口永新方言、就读于南昌省立第一师范的欧阳洛在课堂上显得魂不守舍。讲台上穿长衫的老师满口之乎者也,而讲台下的欧阳洛以课本为掩护在读着刚刚出版的《新青年》。而他的行李箱里从家里带来的《论语》还在,那其实是以《论语》封面作掩护的《共产主义宣言》译本。他开始热衷于参加各种秘密的集会,在会上开始小心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虽然他的永新方言听起来有些口齿不清。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聆听有着“江西三杰”之称的江西青年领袖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的演讲,用学校的作业本记下他们演讲的精彩部分。他们与他同龄,其中弋阳人方志敏与他同年,都出生于1900年,南丰人赵醒侬要大一岁,李大钊的北大弟子袁玉冰最长,生于1899年,却是兴国人氏,与他同是相距不到百里的邻居。他是不是借助与袁玉冰的近乡之谊与这些青年精英接近?方志敏、赵醒侬出版的《青年声》周报,欧阳洛是不是协助刻写过钢板?他们领导的反对江西军阀的斗争中,欧阳洛是不是在白天的街头游行的人群中高呼过口号,在半夜的路口偷偷张贴过标语?
欧阳洛像被一束奇异的光给攫住了灵魂。他经常感觉到自己全身像炭火一样烫。早年在田间地头的思考似乎都有了答案,他的视野再不是如在故乡永新被群山围困,而是无比坦荡,一望无际。他预感到一个大的时代正在到来,而他必须参与其中,成为推波助澜的一员。192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南昌两年的学习时光,他并没有长高,似乎更瘦了些,但他的精神海拔,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两年前显得村相的平头,现在换成了中分式,那似乎是上世纪20年代时髦的发式,隐藏着典型的革命者的决绝信号。两年的师范学习,这个永新山旮旯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已经蜕变成了做梦都喊着救国的愤青,出没于南昌街头的革命派,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完全成了一名新人了。
1925年6月,欧阳洛走在回乡的路上。名义上他是毕业返乡的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事实上他是一名接受了秘密使命的中共党员。他依然带着当年的行李箱,只是里面早期的《稀世贤文》《论语》早已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新青年》《红灯周刊》《中国青年》杂志。6月的天气已经很热,欧阳洛全身都浸在了汗水里。而他脸上已经不再像两年前初去南昌那样显得惶恐窘迫,而是无比的成熟、刚毅和自信。他知道,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欧阳洛先来到吉安,潜入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他用同样的师范生的身份取得信任。他用乡音打开缺口,他用行李箱里的红色杂志招募战士。有永新籍学生王怀、刘真、刘作述等十余人在他的引导下成为了他的盟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拥有了同一个精神父亲。几个月后,他率领着他的红色团队回到了永新,开始把故乡当做播种他的精神火焰的第一块试验田。
欧阳洛率领的师范生团队回来干的工作是办学—这当然是他们的本业。只不过他们把整个永新当做了一间教室,而他们的学生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或者县城的平民。他们给农民学生安排的初级课程是识字扫盲,可他们的教学目标是在永新这座农民夜校里让他们成为照亮黑暗的灯盏。整个教学过程循序渐进:他们给农民讲许多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道理,比如农民贫穷的真正原因,以及他们获救的可能。他们讲阶级,讲平等,讲现实的中国和可能的中国。欧阳洛说,要在黑夜里努力发现光。欧阳洛说,要用火焰唤醒火焰,灯盏点燃灯盏。经欧阳洛介绍,贺子珍、贺怡、贺敏学、贺灿珠、张荣锦等青年农民成为永新境内的第一批党员—那是永新这所夜校最优秀的学员。
然后整个永新南区北乡共有五百名农民学员领到了一张别致的毕业证书—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黑夜的永新,光明在传递,火焰在悄然潜行……必须让灯盏们有一个家,火焰们有一个故乡,欧阳洛牵头成立了永新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永新支部,后来又扩大为中共永新临时县委。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灯火故乡的掌灯人,成为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县委书记。
在欧阳洛的引导下,共青团、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会、商民协会等“学生会组织”相继成立。农民夜校的课程由易到难,由低级到高级,他们在全县开展禁烟运动,取缔赌博,禁止虐待童养媳,实行放脚,率领永新的民众迎接北伐军的到来,接受革命的洗礼。有一堂课是革命的必修课,他们把讲台设在广场,有近万名农民成为了这堂课的受众,而五花大绑的大土豪曾辉光成为了这堂课的教具。杀戮,现场讲授红色暴力美学,是这堂课的本质,也是永新这座农民夜校整个教学过程的高潮部分。课程的主讲欧阳洛在台上历数曾辉光的种种罪状,以此引导受压迫的人们公开向所谓的上层组织宣战。曾辉光被处决,整个永新为之战栗,现场振臂高呼的声音经久不息,敌人的血变成了埋在永新土地上的火种,从此,永新现代史上,底层民众开始了向所谓的上层贵族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抗争。
从1926年6月到1927年6月,仅仅一年时间,永新县党的组织建立并不断壮大,民运工作如狂飙突进,原本俯首帖耳的认命的百姓现在敢于爬上地主的门墙,田地里劳作的衣衫褴褛的农民赶回大会上高呼口号……
欧阳洛这个农民的儿子,熟悉农民的一切秉性。这个在南昌有着浓郁永新口音的青年男子,此刻如鱼得水地回到了他母语的怀抱。在永新乡村的田间地头,他接过满手泥土的农民递过来的旱烟,随即与农民拉开了家常,或者在农民家油腻的餐桌上,将主人热情斟满的一碗浑黄老酒一饮而尽。在农民中间他有很好的口碑,说他是毫无架子态度和蔼的一个人,虽然他已经穿上了先生才穿的长衫,可这一点也不会妨碍他与农民的交往。而在永新有钱人的眼里,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人,成了索命无常和恶魔的化身。几乎所有作恶多端的地主夜晚说起他来都咬牙切齿。几乎所有为富不仁的人都想除之而后快。
我相信欧阳洛有良好的演讲才能。这个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有相当好的职业素养,会把各种场合(会场、田间地头)都当做他的讲台。他的演讲深入浅出热情洋溢激情澎湃,可以让人瞬间茅塞顿开无所畏惧。我相信欧阳洛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领袖风范,可以让人毫不迟疑地把自己交给他成为他的随从。从白天到黑夜,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日出东方,星垂四野,欧阳洛和战友们走在故乡的大地上。他所经过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庄稼都想跟着他揭竿而起,所有的鸡鸣犬吠都仿佛是会场上的口号声……
1927年6月的一天,永新县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纠集土匪武装偷袭永新县城,对欧阳洛所领导的红色风暴进行报复。贺敏学等80余人被抓,正在教堂开会的欧阳洛在下水道躲了几天之后成功逃脱。
离开家乡后的欧阳洛奉命赶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他在他所熟悉的南昌街头穿梭往来,参加各种战斗打响前的秘密集会,把写着秘密指令的信函送到所属的地址。他见识了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叶挺等叱咤风云的英雄的风采,与战友们一起做着战斗前的各种准备。他戴上了区别于对手的红领巾,奔走在各个阵地之间,子弹扑扑地打在他背后的墙上他充耳不闻。听着午夜密集的枪声,他感到无比的快意,似乎是,他等待这一声枪响已经太久太久了。
整个中国,等待这一声枪响已经太久太久了。
八一起义最终宣告失利。欧阳洛奉命前往九江,然后转道上海。那是又一个8月,又一个炎热的夏天。为什么他的每一次远行都在炎热的夏天?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命运密码?阳光毒辣,汗水又一次浸透了欧阳洛的衣衫。徒步奔袭的欧阳洛已经疲惫不堪了。他衣衫褴褛,两手空空。他身无分文,饥饿难耐。他胡须拉碴,蓬头垢面。他的身体无力仿佛是辛亥革命前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他的脚步踉跄仿佛混乱无序的军阀。而他的一颗心依然是红的,年轻的,仿佛是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一颗红心,这已经是他唯一的财产和唯一的信念了。
前路漫漫。那条似乎永无终止的路,此刻成了捆绑欧阳洛的绳索,欧阳洛似乎成了在押的犯人。他沿路乞讨,长江的水已经差不多成了他唯一的养料。在路上,他的血管里充满了长江的回声。当他来到上海,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进食了。他的身体更瘦了,似乎只剩下一个影子。他晕倒在黄浦江畔。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有人认出了他来。他获救了。
就是这样的瘦骨嶙峋的家伙,依然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在上海,他先后担任沪东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为了重新恢复“四一二”事变后日渐消沉的党的组织,他脱下长衫换成了工人特用的短衫,以一名工人的身份打入英国人开办的怡和纱厂粗纱车间,在工人聚集的地方,开始了工人运动的策划和发动。纱厂的车间写着“严禁烟火”的字样,可欧阳洛偏要在这防火的地方播下火种。他不断地寻找工厂管理上的漏洞,然后企图打开更大的缺口。他不断拆除工厂虚拟的院墙,把各个工厂连接成一个整体。一次次罢工组织了起来,一个个党的组织像损坏了的机器一样得到修复,在上海的各个工厂阴影重重的地方,到处有欧阳洛点燃的火焰的魅影。上海,这座到处充斥着洋买办、国民党党棍、青帮流氓、冒险家的十里洋场,因为欧阳洛们的辛勤开垦,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摇篮。
1929年10月,欧阳洛又被派到湖北,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在他主持湖北工作期间,武汉纺织工人罢工。铁路、面粉、石膏、被服、码头、煤业、水电、米业、杂货、人力车等各业工人纷纷罢工。沉寂数年的武汉工人运动走向复兴。
从1925年至1929年,短短四年多的时间,一个永新乡间曾经的粗通文墨的农民,南昌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已经成长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名习惯在刀尖上跳舞的卓越舞者。他历经艰险却无所畏惧,他隐匿在人群之中不动声色。他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他在纱厂的账房里抄写账目一丝不苟。他的外表像极了一名普通工人,或者是落魄的读书人。可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狗一样灵敏的嗅觉,虎豹一样勇猛的胆魄和领袖才有的精神感召力。这个几年前的南昌城里土里土气的乡下男人,至今已成为了一个善于发起乡村农民运动、城市工人运动的双料政治明星,一个让国民党中央也为之战栗的红色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