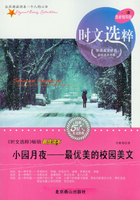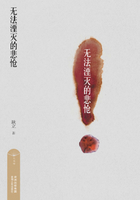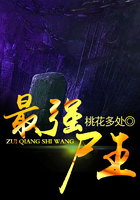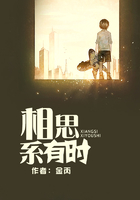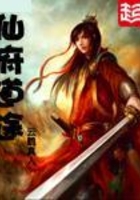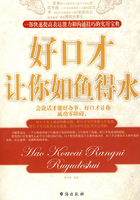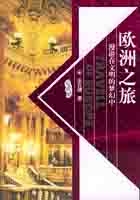《山海经》的原书是否有图画?
《山海经》最初是有图的,而且以图为主,文字只是对图的说明。
从《海外西经》的内容开看,其叙述方式是按照图的方位来进行的,如「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一臂国在其北……」、「奇肱之国再其北……」等。而对一些人、神或动植物的叙述,也是根据图画来描绘的,如《海外南经》:「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海内北经》:「犬封国曰大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大荒东经》:「有因民国,勾姓,黍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从其中的「方」字看,这无疑是对图的描绘。
又如《海外南经》:「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海外北经》说:「深目国在其东,为人举一手。」《海外西经》:「奇肱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有鸟焉,两头,赤黄色,在其旁。」难道长臂国的人永远是两手各操一鱼,深目国的人永远举一只手,奇肱国的人永远乘着有花纹的马?可想而知,这是对图画的描述。
再从今存的《山海经》各篇的叙述方法来看,其叙述方式正是按照方位,对图画加以说明。如「海经」各篇一开始总有固定的一句:「海外自××(方位词,如「西南」、「西北」等,下同)陬至××陬者。」以《海外西经》为例,首言:「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然后从「三身国」开始叙述,最后是「长股国」。与此篇内容大致相同的《淮南子·墬形训》里这样叙述:「凡海外三十五国,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肃慎民……三身民。」这种叙述上的差异只是因为看图的顺序不同:《海外西经》是从西南至西北,所以起自「三身国」,终至「长股国」;而《淮南子》正好相反,是从西北至西南,这样就是起自「长股国」而终至「三身国」了。《淮南子》是汉代的书,可见《山海经》的图在汉代还存在。
晋代的陶渊明曾作《读山海经诗》的组诗,中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的句子,说明他曾看到过图。从郭璞的注解来看,可以知道郭璞也曾看到过图,比如《海外西经》说「羽民国」身上长着羽毛,郭璞解释说:「能飞不能远,卵生,画似仙人也。」说明郭氏是根据图画来注释的。郭璞还有《山海经图赞》二卷,「赞」是一种文体,可见郭璞此书是专门为《山海经图》写的一部赞文。由此看来,《山海经》的图在晋代还可以看到。
现今《山海经》古图已失,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八,北宋舒雅曾绘制过《山海经图》,一共十卷,可惜今天已经失传。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山海经图大体都出于明清,比如明代王崇庆《山海经释义》中附图一卷;清代学者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中,有图五卷;清代学者汪跋绂的《山海经存》,附图三百余幅。
由此可见,《山海经》是有图的,而且图是主体,文是图的说明。作为一部地理书,「山经」描述地理时经常说「由某山向东多少里曰某某之山」,「又东南若干里曰某某之山」,这种记述方式,正是在尚未以比例尺表示距离之前,对地图的一种表述方法,相当于对图的说明。
最初的《山海经》图应当是地图。我国古代有专门执掌天下地理形势的职官,如《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就记载「司书」这种官的职务是管理国家的图书,而图书中就有「土地之图」,即地图。这种地图是由大司徒主持绘制的,《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提到大司徒这个官职,其任务是掌握国家的地图与人口之数,这样就可以靠着地图,周知九州岛岛之地域,了解各地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地理情况。而依靠地图管理国家的,是一种叫做「遂人」的官,遂人主管国都以外的地方。他靠着地图行走在广袤的田野上,到达郡县境内。而当时的制度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的组织,而遂人正是靠地图而对这些地方了如指掌。以上种种,均说明我国很早就有地图,而《山海经》作为一种地理书,最初正是对图的说明或注释文字。
对于《山海经》中所记载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飞禽走兽,宋代朱熹以为是根据壁画写出来的。《朱子语类》卷一三八:「问山海经。曰:一卷说山川者好。如说禽兽之形,往往是记录汉家宫室中所画者,说南向北向,可知其为画本也。」他在《晦庵集》卷七十一里又重申这个观点,认为古代有专门的图画之学,时人再根据图画来写出文字,作为对图画的说明,比如屈原的《天问》,即是作者根据墙壁上的图画所作的诗歌。而《山海经》的成书也是如此,墙上画的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禽兽,用文字写出来当然也就很奇怪了,但这并不是纪实,不表示在某地一定会有这种怪异的动物。
由于古图的散佚,后人纷纷补画了一些图,如上面提到的梁代及宋、明、清代都会补绘,但现存的都是清人作品。不过这些图从内容上看已不是地图,而是异兽仙人之属。如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明,清代学者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中有图五卷,分「灵祗」、「异域」、「兽族」、「羽禽」、「鳞介」五类,五类中并无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