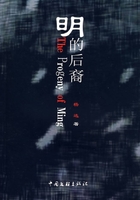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你该知道,这只是显像啊。”嘉蒂雅的声音中带着歉意。现在她裹着一件浴袍似的衣物,手臂和肩膀仍旧露在外面,一只腿也只遮了一小部分,但贝莱却视若无睹——他早已完全恢复镇定,觉得刚才的反应实在太蠢了。
他说:“我只是吃了一惊,德拉玛夫人……”
“喔,拜托,你可以叫我嘉蒂雅,除非——除非这有违你们的习俗。”
“好吧,嘉蒂雅。你别担心,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我绝对没有起任何反感,你了解吧。我只是吃惊而已。”自己的愚蠢反应已经够糟了,他想,可别再让这个可怜女子以为自己讨厌她。他当然不会起反感,其实……其实……
唉,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他相当确定自己绝对无法把这件事告诉洁西。
“我知道我冒犯了你,”嘉蒂雅说,“但我并非故意的,我只是没想到而已。我当然了解人人都应该顾虑到其他世界的习俗,可是有些习俗实在太古怪了。不,不是古怪,”她赶紧更正,“我不是指古怪,而是指陌生,你知道吧,所以很容易忽略,就好像我忘记要调暗窗户一样。”
“真的没关系。”贝莱喃喃道。这时她已来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每扇窗户都拉上了窗帘,其中的光线有点人工化,带有舒适且和自然光略微不同的质理。
“可是另一方面,”她一本正经地说,“要知道,这只是显像罢了。毕竟,刚才我在淋浴间的时候,同样没穿任何衣服,但你并不介意和我说话。”
“这个嘛,”贝莱希望她能尽快结束这个话题,“听见你的声音没什么,看见你却另当别论。”
“你刚好说到了重点。你根本就没有看见我。”她有点脸红,低下了头去,“你可千万别以为我真会那么做,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在看我,我还会这样走出淋浴间。这只是显像罢了。”
“难道不是一回事吗?”贝莱说。
“绝对不是一回事。你现在只是看到我的显像,你不能碰到我,也不能闻到我,对不对?如果你真正看到我,就能做到这些事了。此时此刻,我离你至少有两百英里远。所以怎么会是一回事呢?”
贝莱渐渐感到有趣了。“但我能用眼睛看到你。”
“不,你不能看到我,你只能看到我的显像。”
“有什么差别吗?”
“简直就是天差地远。”
“我懂了。”他这么说并不算敷衍。两者的微妙区别虽然有些费解,但其中的确自有道理。
她把头稍微偏向一侧。“你真的懂了吗?”
“真的。”
“这是否意味着你并不介意我现在脱掉浴袍?”她微微一笑。
他心想:她在挑逗我,我应该好好跟她较量较量。然而,他只是大声说:“不,那会令我分心。我们改天再试试吧。”
“那么,你介不介意我继续裹着浴袍,不换上正式服装?我是说真的。”
“我不介意。”
“我能不能直接叫你的名字?”
“只要你觉得有此必要。”
“你叫什么名字?”
“以利亚。”
“很好。”她舒舒服服地坐进椅子里,那张椅子看起来硬邦邦的,几乎像是陶瓷做的,但她一坐上去,椅面就逐渐下陷,最后将她整个包住。
贝莱说:“现在谈正事吧。”
她答道:“好,谈正事。”
贝莱突然觉得困难无比,甚至不知该如何开口。若是在地球上,他会询问姓名、阶级、住所,以及几百万个例行问题。开头的一些问题,他甚至早已知道答案,但这是进入正式问答的跳板——一来让对方熟悉他这个人,二来帮助他决定侦讯的策略,避免仅仅根据直觉来发问。
可是现在呢?他如何能确定任何一件事?光是“看”这个动词,他和这名女子就有不同的解读。还有多少词汇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天会发生多少次类似的误解?
他终于开始发问:“你结婚多久了,嘉蒂雅?”
“十年了,以利亚。”
“你今年几岁?”
“三十三。”
贝莱隐约有点窃喜。她很可能已经一百三十三岁了。
他又问:“你的婚姻幸福吗?”
嘉蒂雅露出不安的表情。“你这是什么意思?”
“嗯——”贝莱一时词穷了。一桩幸福的婚姻要如何定义呢?或者应该说,索拉利人认为怎样的婚姻才算幸福呢?最后他说:“嗯,你们彼此经常见面?”
“什么?好在答案是否定的。要知道,我们又不是动物。”
贝莱心头一凛。“你们的确住在同一座宅邸吧?我以为……”
“我们结了婚,当然住在一起。但我们各有各的住处。他的事业非常重要,占用了他很多时间,而我也有自己的工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以显像联络。”
“他常见到你,对不对?”
“这是不该谈论的问题,但的确如此。”
“你们有子女吗?”
嘉蒂雅猛然跳了起来,显得万分激动。“这太过分了,这是最下流的……”
“慢着,慢着!”贝莱用力捶了一下座椅扶手,“别这样为难我。我是在调查一桩谋杀案,你了解吗?谋杀案,而死者正是你的丈夫。你到底想不想见到凶手落网,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就问有关谋杀案的问题,别问……别问……”
“我得问各式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我想知道你是否对他的死感到难过。”他刻意恶毒地加上一句:“你看起来并不难过。”
她以傲慢的目光瞪着他。“不管谁死了,我都会难过,更何况他是个年轻有为的人。”
“既然他是你的丈夫,你的难过难道不会更多一点吗?”
“他是被指派给我的。好吧,我们的确按时见面,不过……不过……”接下来她说得很快,“不过,如果你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并没有子女,因为我们尚未领到配额。我不懂,这些事和我现在难不难过有什么关系?”
也许完全没有关系,贝莱心想。这取决于社会习俗,而他对这方面并不熟悉。
于是他改变话题:“据我所知,你对这桩谋杀案有第一手的资料。”
她似乎突然绷紧了神经。“是我……是我发现的尸体。我这么说对不对?”
“所以说,你并未真正目击凶案的过程?”
“喔,没有。”她压低了声音。
“好吧,请把当天的经过告诉我。你可以慢慢说,尽量用你自己的词汇。”他靠向椅背,准备洗耳恭听。
她说:“那是五时三二……”
“银河标准时间是什么时候?”贝莱立刻追问。
“我不确定。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想你可以查到。”
她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眼睛则张得很大。他注意到她的眼珠太偏灰色,并不能称为蓝眼珠。
她继续说:“那天他来我的住处。那是我们的见面日,我知道他会来。”
“他总是在见面日来找你吗?”
“对啊。他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人,是个优秀的索拉利公民。他从未错过任何见面日,而且总是准时抵达。当然,他不会待太久。我们还没有领到子……”
她没把话说完,但贝莱还是点了点头。
“总之,”她说,“你要知道,他总是准时抵达,所以整个过程都很安闲自在。我们会聊上几分钟;见面是一件苦差事,但他和我说话时总是相当正常。他就是那样的人。然后他便会去做他的实验,至于细节我就不大清楚了。他在我的住处设了一间实验室,以便在见面日使用。当然,在他的住处还有一间大得多的实验室。”
贝莱很想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实验。或许和所谓的胎儿学有关吧。
他又问:“那天他可有任何不自然的表现?例如忧心忡忡?”
“不,不,他一向无忧无虑。”她差点笑出声来,但在最后一刻忍住了。“他总是能百分之百控制情绪,就像你那位朋友一样。”她用纤细的小手指了指丹尼尔,后者完全不为所动。
“我懂了。好,请继续。”
嘉蒂雅并未说下去,而是悄声问道:“你介不介意我喝点东西?”
“请便。”
嘉蒂雅的右手在椅子扶手上滑了一下,不出一分钟,便有个机器人悄悄走进来,将一杯热腾腾的饮料(冒出的热气清晰可见)递给她。她慢慢呷了几口,然后放下杯子。
她说:“这样好多了。我能否问你一个私人问题?”
贝莱说:“你尽管问。”
“嗯,我读过不少关于地球的记述。我一直很有兴趣,你知道吧。一个那么古怪的世界。”她倒抽一口气,赶紧补了一句:“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贝莱微微皱起眉头。“凡是你没住过的世界,对你而言都是古怪的。”
“我其实是想说很不一样,你知道吧。总之,我想问你一个无礼的问题,但我希望至少在地球人听来不算无礼。当然,我不会拿这个问题问索拉利人,绝对不会。”
“什么问题,嘉蒂雅?”
“关于你和你的这位朋友——奥利瓦先生,对不对?”
“对。”
“你们不是彼此显像吧?”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们彼此看得到。你们两人都在那里。”
贝莱说:“对,我们实际上共处一室。”
“你能碰触他——如果你真想这么做的话。”
“没错。”
她轮流扫视他们两人,然后说:“喔。”
这声“喔”有可能是任何意思。恶心?反感?
贝莱起了一个促狭的念头,如果他现在站起来走向丹尼尔,然后伸出手,不偏不倚地放到丹尼尔脸上,那么她的反应一定很有意思。
但他只是说:“刚才,你正准备说明当天你丈夫来见你的情形。”他万分确定,她之所以把话岔开——不论她对另外那个问题多么感兴趣——主要还是因为她想避开这个问题。
她又花了点时间喝饮料,这才答道:“没有多少好说的。我看得出他很忙,这点我相当肯定,因为他总是在做有建设性的事,所以我也回到我的工作岗位去了。然后,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一声叫喊。”
她说到这里就打住了,贝莱只好主动提问:“什么样的叫喊?”
她答道:“是瑞坎恩,是我丈夫的叫喊。只是叫喊,没说任何话。那是一种恐惧,不!应该说是惊讶、是震惊。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他的叫喊。”
她举起双手捂住耳朵,仿佛想要阻挡记忆中的那个声音,与此同时,她身上的浴袍缓缓滑到腰际。她并没有注意到,贝莱则紧盯着自己的笔记本。
他问:“你的反应是?”
“我马上跑,跑去找他。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以为你刚才说过,他去了那间设在你那儿的实验室。”
“没错,以——以利亚,但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反正我不确定,我从来没去过,那是他的实验室。我对它的位置有个大致的概念,知道它在西侧,但我心乱如麻,甚至没想到要召唤机器人。任何一个机器人都能轻易把我领到那里去,但如果没召唤,它们当然都不会来。等到我好不容易找到那里,他已经死了。”
她突然打住,低下头哭了起来,这个举动令贝莱感到极不自在。她并未试图遮住脸庞,只是闭着双眼,让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向下流。她几乎没发出任何声音,肩头也只是微微颤抖。
然后,她张开了眼睛,泪眼汪汪地望着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死人。他浑身是血,而他的头……简直……全部……我勉强找来一个机器人,它又叫来其他同伴。接下来,我想是它们在照顾我,并处理了瑞坎恩。我不记得了,我不……”
贝莱问:“你说它们处理了瑞坎恩,这话什么意思?”
“它们把他带走,把一切都清理干净了。”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气愤,证明她是一位注重整洁的女主人。“房间给弄得一团糟。”
“尸体是怎么处理的?”
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想是烧了吧,跟其他的尸体一样。”
“你没有报警吗?”
她显得一脸茫然,贝莱恍然大悟:这里没有警察!
他说:“我想,你还是跟某人说了。这件事才会传开来。”
她答道:“机器人找来一名医生。我也必须通知瑞坎恩的工作场所,让那里的机器人知道他再也不会回去了。”
“我想,医生是替你找的吧。”
她点了点头。直到这个时候,她似乎才注意到浴袍正垂挂在自己的臀部。她将浴袍拉到适当位置,可怜兮兮咕哝着:“真抱歉,真抱歉。”
她无助地坐在那里,浑身发抖、脸孔扭曲地回忆着那段可怕的往事,令贝莱觉得很不自在。
她从来没有见过死人,也从未见过四溅的鲜血和破碎的头颅。虽说索拉利上的夫妻关系相当薄弱,她还是见到了一具死状甚惨的尸体。
接下来,贝莱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他起了想道歉的冲动,但身为一名警员,他这么做只是尽忠职守罢了。
可是这个世界并没有警务人员。她能否了解他只是在尽忠职守?
他慢慢地,尽可能温柔地说:“嘉蒂雅,当时你有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任何除了那声叫喊以外的声音?”
她抬起头来,虽然一脸悲苦,那张俏脸美丽依旧,或许还因而更具吸引力。她答道:“没有。”
“没有脚步声?没有其他声音?”
她又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没听到。”
“当你发现你丈夫的时候,你确定他是单独一人?现场只有你们两位吗?”
“是的。”
“没有任何外人来过的迹象?”
“我完全看不出来。总之,我无法想象外人怎么到得了那里。”
“你为何这么说?”
一时之间她显得很惊讶,不久却又沮丧地说:“你是地球来的,我一直忘记这件事。好吧,因为不可能有外人到得了那里。除了我之外,我丈夫从来不见任何人;他自幼如此,绝无例外。他当然不是那种喜欢见人的人,我的瑞坎恩不是那种人。他一向非常严谨,非常遵从习俗。”
“或许并非出于他的自愿。万一有个不速之客前来见他,而他事先完全不知情?不论他多么遵从习俗,也不可能避开那个不速之客。”
她说:“或许吧,但他一定会立刻召唤机器人,叫它们把那人赶走。他一定会那么做!何况如果没有受邀,谁也不会试图见我丈夫。我无法想象会有那种事。而瑞坎恩是绝对不会邀请任何人来见他的。这种事光是想想都很荒谬。”
贝莱柔声道:“你丈夫是头部受到重击而死亡的,对不对?这点你应该承认吧。”
“我想是吧。他……整个……”
“现在我并不是在询问细节。请你想想,那个房间有没有任何机械装置,可以让人透过遥控砸烂他的头颅。”
“当然没有。至少,我并没有看见。”
“如果真有那样的东西,我想你当时应该看得见。由此可知,曾有一只手抓着一件能够砸烂头颅的东西,而且曾经用力挥舞。换句话说,一定曾经有人距离你丈夫不到四英尺,所以那人的确见到他了。”
“不可能的。”她义正词严地说,“凡是索拉利人,都不会见任何人。”
“一个会犯下谋杀案的索拉利人,不会介意稍微见见人,对不对?”
(在他自己听来,这句话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他知道地球上有一桩案例,某个丧尽天良的凶手最后之所以被捕,只是因为他无法违反在公共浴室必须绝对禁声的习俗。)
嘉蒂雅摇了摇头。“你对见面这件事并不了解。地球人随时随地想见谁就见谁,所以你并不了解……”
她似乎再也压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她的眼睛也为之一亮。“对你而言,见面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对吗?”
“我总是视之为理所当然。”贝莱说。
“不会给你带来困扰?”
“怎么可能呢?”
“嗯,胶卷书没提,而我一直很想知道——我问个问题无妨吧?”
“问吧。”贝莱硬邦邦地说。
“你拥有一个指派给你的妻子吗?”
“我已婚,至于所谓的指派我就不懂了。”
“据我所知,只要你想见你的妻子,随时能够见到她,而她也随时能见到你,你们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贝莱点了点头。
“嗯,当你见到她,我是说当你想要的时候——”她将双手举在胸前,迟疑了片刻,仿佛在寻找适当的用词。然后她又试了一次:“是不是任何时候,你都能……”她未能说下去。
贝莱并未试着帮她。
她又说:“唉,算了。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拿这种事烦你。你问完了吗?”看来她好像又要掉眼泪了。
贝莱说:“最后一个问题,嘉蒂雅。暂且忽略没有人见得到你丈夫,假设的确有人见到他,谁最有可能呢?”
“这么猜毫无用处。谁都不可能。”
“一定有这样的人。葛鲁尔局长说他的确有理由怀疑某人,所以你看,一定有这样一个人。”
女子脸上闪现一抹极其勉强的笑容。“我知道他在怀疑谁。”
“很好,是谁?”
她将纤细的小手按在自己胸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