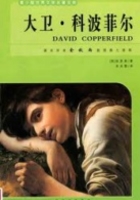松花江承载着无限的历史沧桑从北满大地上流过,它见证了松花江流域的一切千变万化,风云际会。松花江畔,从来都没有安静过……
毒辣的日光疯狂地烘烤着北沟屯,整个屯子就像个大蒸笼。屯子东头的泡子已经干得仅剩一摊摊的淤泥,几只已看不清颜色的猪拱挤在一起,身上满是湿漉漉脏乎乎的泥浆,在这炎热的盛夏享受着那不易的一丝丝凉意。有的小泡子水被蒸发干了,好多大小的鱼垂死地乱蹦着,直到晒死成了鱼干儿或被农户捡走。农家的栅栏是用柳条插的,被偶尔来的一点热风吹得微微颤动,耷拉着发蔫儿的柳叶,个个如文弱病态的黛玉。
北沟屯自入夏以来已经连续高温十多天了,今天是迄今为止最热的一天。
屯子的北面有条河,叫北沟河,是屯子里唯一的一条河,东西流向,最终汇入松花江。在东北,这样的河很多,不过,都是些小河沟子,水量并不是很大。
在这北沟河旁,是大片大片的水田。老烟袋沿着田埂走到地边的一棵大柳树下,撂下尖铲,用干瘪的大手正正头上的破遮阳草帽,眯缝着眼睛望了望他那向地主张汉章租的几亩几近干涸的水田,叹了口气,骂了一句:“这操蛋的天气,真他娘的不让人活了!才几天的工夫,又这德行了!”
老烟袋拿起尖铲横在地上,坐在铲杆儿上,背倚着大柳树,打开烟口袋,抽出别在腰间的大烟锅儿。
这支烟锅,黄铜质地,做工很精细。烟锅有普通酒盅般大小,烟杆儿约莫半米多长,头儿是用岫岩玉雕的烟嘴儿。这支铜烟锅,是老烟袋他爹传给他的。
至于老烟袋他爹在哪儿得的这把烟锅子,除了老烟袋他爹本人,就没人知道了。
老烟袋他爹也未对老烟袋提及过这把烟锅子的来历。
只见老烟袋把烟锅往树干上“叭叭”地敲了敲,掏出碎烟叶子塞满烟锅,用洋火点着,“吧嗒吧嗒”地猛抽了几口,显出无比舒服的神情来。
老烟袋抽了几口烟,缓缓地站起来,把烟锅放在地上,拿起尖铲大步走到河边,往手心吐了吐唾沫,把河沿与水田连着的垄台挖开了,河水顺着流儿进了老烟袋家的水田。
老烟袋拄着尖铲,用手抹了抹额头上的汗,自语道:“要没这北沟河,这稻子全都得瞎到地里。这年景,又是闹胡子,又是闹旱灾,天老爷不长眼啊!”
“二皮,你可加小心了,这河汊子摸不准哪儿就有陷坑,不准往里去!”
老烟袋忽然想起正在河汊子里洗澡的小儿子二皮,转头朝河里喊道。
“放心吧,爹!我就是这水里的三道鳞(淡水鱼的一种),扑腾得溜着呢,没事儿!”二皮嘻嘻笑着,探出脑袋,拍着水花冲老烟袋得意地说道。
这二皮今年十三岁,身体干瘦,脑袋较大,外号“大脑袋二皮”,人称二皮。其生性顽劣,却疾恶如仇,是屯子里有名的孩子王。二皮常常召集屯子里的一些孩子,或和自己差不多大,或比自己小得多的。常常自己扮成皇上模样,盘腿坐在土堆上,一帮孩子做文臣武将。然后纷纷跪拜,一本正经地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二皮会面露微笑,摆出高贵的姿态,单手一抬,说句:
“众卿平身!”“谢万岁!”“有本准奏,无事退朝!”类似于此例荒诞可笑事情,在二皮身上不胜枚举。
待水放得差不多了,老烟袋已经吸了三锅烟了,最后习惯地把烟锅往大树干上“邦邦”地敲了几下,扣净了残余的烟灰,用力地吹了吹烟锅,满意地别进了腰间。然后起身用尖铲挖土堵住了垄台上放水的豁口。
“又能挺上一阵子了……”老烟袋从嘴角露出一点微笑,轻吁了口气,而后叫二皮,“二皮!别扑腾了,走,回家!”
老烟袋说完,却不见二皮有回应。
“我说二皮啊,回家了,麻利点儿!没听着啊!”老烟袋又喊了一遍,这次喊得比上次喊得声音大很多,言语中略带火气。
可还不见二皮回应。这下老烟袋可真急了,感觉有些不对劲,抬眼向河里望去。登时看得老烟袋两眼发蒙,河里竟空无一人!河面静静的,仅偶尔能吹来一丝波纹。
人呢?二皮哪去了?!二皮咋就活生生地不见了,没有丝毫征兆,就这么蒸发了。老烟袋越看河面越恐惧,反复地大喊:“二皮!二皮!二皮!”最后直到喊得声嘶力竭。二皮该不是溺死到河里了吧?以前也有过孩子淹死的,要不是这该死的天气太热,也不会轻易同意二皮进河里洗澡的。
老烟袋愈想愈害怕,愈想愈自责。老烟袋也不敢多想了,自责地骂了自己一句:“李茂生啊李茂生,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咋就不会水呢,会他娘的狗刨儿也成啊!”老烟袋不会水,不知所措地发了一会儿怔,忽然又眼睛眨巴一下,把尖铲一撇,一路慌慌张张地小跑,看样子是到屯子里喊人去了。
原来这老烟袋姓李,名茂生。祖籍奉天(沈阳),在前清咸丰年间他爷爷那辈儿因生计,举家迁到松花江江北开荒,才在这北沟屯扎下来。以前他爷爷拼了老命在江北的荒甸子开了好多地,保管片片俱是良田沃土。可惜最后积劳成疾,得了痨病死于炕上。大片的地都均分给了两个儿子,长子李多福(老烟袋他爹),次子李多禄。可惜他二叔李多禄不争气,品行恶劣,满腹坏水,勾结胡子“大酱缸”抢了哥哥李多福的地契,占了三垧多地。无奈李多福只得给地主家做长工扛活,在李多福临死之际,给老烟袋留下了两枚银元和一支铜烟锅,并嘱咐他,日子再贫苦,再没钱,也不能卖了或当了这支烟锅。这烟锅子也就作为传家宝物一样传给了老烟袋。
老烟袋给他爹发完丧,就租了张汉章家的五亩水田和四亩旱田维持生计。
大地主张汉章性和善,对老烟袋的缴租日子也较宽裕。在历史上,中国地主的形象都不太好,这张汉章就是这么个好东家。再说这二皮,是老烟袋李茂生的二儿子,全名叫李凤昭;还有个长子,在县保安大队当兵,时年二十一岁,叫李凤暄。究竟这李凤暄是什么样的人,下文自有详述。
却说这老烟袋回到屯子不多时,便哭丧着脸,步履匆匆地带了五六个壮年汉子向河边行来。
老烟袋带着众人赶到河边,面冲着这几个男人,顺手就向河里指,焦急地说:“快快,二皮就溺这个河汊子里了!”
有两个男人刚要往里跳,突然有个叫张大柱的手指着喊道:“快看!那不是二皮吗!?”
众人都不禁一愣,顺指望去,哎呀妈呀,那不正是二皮嘛!这小子,干啥呢?只见那二皮躺在河对岸不远处的碧绿软绵的河沿草地上,跷着二郎腿,不大声地吹着口哨,手里摆弄着几个瓦白的嘎啦(河蚌,东北土话),神情甚是喜悦。
“二皮!你给我过来!”老烟袋厉声喊道。
二皮打了个激灵,一骨碌爬起来,看见这么多人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咋了,爹?咋来这么多人?”
老烟袋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气得有些哆嗦,质问道:“死崽子,你刚才干啥去了?!”
二皮一脸莫名,好像在说我没干什么啊,我哪都没去啊。
站在老烟袋一旁的张大柱微微不悦地叹了口气,说:“老烟哥啊,你这不是逗我们玩儿呢吗?二皮啥溺水了?看那舒坦样儿,这不好好的吗?咋地没咋地!整的这是啥事儿啊?”
旁边的三歪也说:“老烟叔(三歪辈分小),你说这大热天的,能把人晒化喽,看把我们爷儿几个累的,撒丫子跟你跑,来看啥事儿都没有,这扯不扯!”
其他几个也都开始埋怨:“就是!”
老烟袋压着火气,笑呵呵地说:“真对不住啊,我都被这死崽子整蒙了。”
“好了好了,我们得回去了,这天头,太热了!晒死人!”张大柱咧着嘴,直用手掌往脸上扇风,边说边转身要走。
见张大柱走了,其余人也都不悦地跟着回了。
老烟袋目送着,仰头喊道:“对不住了啊,赶明请爷们几个喝酒啊!呵呵。”
几个男人走了,老烟袋看了看仍傻站着的二皮,真是火冒三丈,喊道:“傻站着干啥?过来!”
二皮麻溜地渡了过来,趴在河边可就是不上来。
老烟袋一看二皮不上来,怒问:“咋不上来?!”
二皮笑嘻嘻地说:“不上,上来了你得打我!”
“快上来!没事儿你怕啥?!”
“不上!”
“上来!”
“不上!”
老烟袋气得左晃右晃,说:“好,你不上,是吧?我问你,你刚才去哪儿了?”
二皮一脸委屈,说:“我就在这河汊子里了,哪儿都没去!爹,你咋不信我呢?”
老烟袋点了锅烟,“吧嗒”吸了一口,说:“我那么喊你,你咋没听着?”
二皮眼睛一眨,翻了个身,长音地“哦”了一下,似乎想到了什么,说:
“那难怪了,我说您咋没找着我呢。呵呵,我搁水底下了,耳朵还塞了草叶子,那咋能听着呢。”
老烟袋吐了口烟,问:“水底下了?我在河沿待那么长时间,你咋不上来?!”
二皮“嘿嘿”一笑,往身边指道:“掏嘎啦。搁泥里摸着几个大嘎啦,就抠啊。滩泥太硬,费劲!好不容易抠出来,手指头都抠坏了。”
老烟袋面容稍缓,叹了口气,说:“你这孩子,为了几个嘎啦,搁水底下待那么久,吓死个人!好了,上来吧!”
二皮仍旧不动弹,看着老烟袋,眼睛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呵呵,上来吧,爹不打你,爹是那不讲理的人吗?”老烟袋被二皮弄乐了,说。
二皮眨巴眨巴眼睛,嘴一翘,乐了,光着腚就上来了。登上裤子,光着上身,拿破布衫子兜起那几个大嘎啦,“嗖”地蹿到老烟袋前面,嬉皮笑脸地说:
“爹啊,我前面先走了,让我娘给我煮嘎啦去喽!”
“驾!”就在这时,不远的大路上跑过几个骑马的人,俱身着麻衫布衣,骑得奇快,一转眼就过去了。
二皮止住了脚步,好奇地问:“爹,那伙是啥人?”
老烟袋晃了晃头,说:“不知道啊,这年月,谁知道是干啥的!干啥的都有!”
“快点儿!”大路上又传来了一阵叫喊声,这是一伙当兵的打扮,为首的戴个淡蓝色的大盖帽,手里头扬着把盒子枪。显然,这伙兵是在追刚才那几个人!
老烟袋看着这伙兵过去,对二皮说:“好像是保安大队的!”
二皮一听是保安大队,来了精神,说:“那我哥也在那里头喽?”
老烟袋“嘶”了一下,说:“嗯,可能在。”
二皮乐了,说:“哈哈,好!”
老烟袋微愣,问:“好啥?”
二皮喜悦依旧,说:“我哥老长时间都没回家了,啥时候能回来啊,这回能顺路回来不?”老烟袋往鞋底磕了下烟锅,突面露不悦,说:“走,别说他了,好像他没这个家了!回家!”
老烟袋一提到大儿子凤暄,就不高兴。自凤暄到县保安大队当兵,都四年了,没回过一次家。二皮他娘让老烟袋去县里看看凤暄,可老烟袋是个倔脾气,对二皮娘说,他是儿子我是儿子?!他不回家看咱俩,看看他爹,我倒要费劲拔力地看他去?妄想!二皮娘也是无奈,本想自己去看看凤暄的,可老烟袋死活不让。凤昭年纪尚小,自九岁那年就再也没见过哥哥凤暄。二皮很恋哥哥,逢人就说我哥是个当兵拿枪的,引以为豪。
爷俩回了家,二皮把嘎啦撂到灶台上,朝他娘说道:“娘,看,我抠的嘎啦,煮了吧,晾成干儿,待到过年吃!呵呵,我出去玩儿了!”
二皮娘“哎”应了一声。
老烟袋走进来,瞅了眼那几个嘎啦,自语道:“这个二皮,真不叫人省心啊。就这么几个嘎啦,瞧把他爹耍的。”
二皮娘笑了,说:“二皮又咋了?看你那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呵呵。”
老烟袋抓起个旧蒲扇,摇了起来,说:“你那儿子,淘得厉害!潜水里那么长时间抠几个嘎啦,惊动一帮人!今天没揍他,便宜他喽。”
二皮娘轻瞪了一眼,说:“二皮不还是个孩子嘛,你这当爹的,净说狠话!”
晚上,繁星满天,月如残玉。二皮翻过几道篱笆,来到了赵先生的家。
赵先生家屋里昏暗,只见炕上和地上的板凳上坐着十多个面庞灰扑扑的孩子,大到十四五岁,小至七八岁。窄窄的屋子里,靠墙的破桌子上斜立个小黑板,桌子上放着黄色的粉笔。黄色的粉笔?所谓的粉笔不过是来自岩层的画石,易碎,不耐书写。
赵先生二十三四岁模样,戴着副黑边眼镜,个子不高,偏瘦,小背头,长挂脸,身着一套很旧很旧的青色长衫,样子儒雅。这个赵先生上数五辈儿都是前清的读书人,可偏偏都是秀才,连个举人都没有,更别提进士了。唉,书香门第,秀才都放臭了。这北沟屯里就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白天劳作,只有晚上有闲暇时间。在当时洋油(煤油)很贵,所以农民睡觉很早。可这赵先生家的灯油是家家供给的,无非为了让孩子识个文断个字。
二皮推开门来到里屋,挤了个地方坐下。赵先生正在教《千字文》,前一段时间教的是《三字经》。旧社会的启蒙教育,也就是识文断字,都是以《三字经》、《千字文》、《颜氏家训》等为初级教材。
“同学们,我今天教给大家的是《千字文》。《千字文》是我国南朝人周兴嗣所作。下面大家来看黑板和我一起念。”赵先生说完,转身指向黑板上的几行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珍李柰,菜重芥姜!”
赵先生读一句,孩子们就无比认真地跟读一句。
放学了,二皮一把拉住翻篱笆的四蔫,坏笑道:“回家着啥急啊?四蔫。
下来!”
四蔫被二皮这么一拉,就骑到了篱笆上,硌得下体生疼,说:“二皮,硌死我了!你轻点儿拽我!”
四蔫慢慢地下来,表情微微痛苦,说:“干啥呀二皮?我娘让我下学就早点回家呢!”
二皮笑骂道:“熊蛋包!我发现赵先生家房檐子有老鼻子鸟窝儿了!咱给掏了吧!”
四蔫白了二皮一眼,说:“我才不和你掏呢!”
二皮急了,问:“为啥?”
四蔫语句不连贯,有些畏惧地说:“和你掏鸟窝子,我总分得少。”
二皮拍了下四蔫的后脑勺,说:“就你这熊蛋包,你有我掏得多吗?我那叫按劳分配!”
四蔫讲不过他,干脆坐在地上,说:“和你掏鸟窝还不如回家捏泥人。二皮,你让我走吧。”
泥人?二皮一听,颇感新鲜,凑过去,眯着眼问:“泥人?你会捏泥人?”
二皮微微摇头,表示不信。
四蔫点点头,说:“咋啦?不过刚学,捏得太砢碜,呵呵。”
二皮笑了,不屑地说:“就你?呵呵,还学捏泥人?”话锋一转,问,“跟谁学的?”
四蔫微诧,说:“你还不知道啊?”
二皮眉头一皱,说:“快说!”
四蔫拍拍屁股站起来,说:“那你得让我走。”
二皮不耐烦了,点头表示同意。
四蔫接着说:“在屯子东头大柳树下来个卖泥人的,和他学的。”
清晨,日光和煦,并不毒辣。二皮今天起得很早,这不,正蹲在院子里的菜园子中和泥。
老烟袋无意看见儿子此举,不免好奇,走过来就问:“二皮,和泥干啥?”
二皮没抬头,说:“呵呵,捏泥人。”
老烟袋乐了,没听说二皮会捏泥人啊?行啊这小子,还想学门儿手艺啊。
老烟袋问:“你啥时候会捏泥人了?”
二皮说:“还没会呢。”
老烟袋笑道:“呵呵,我当你小子会呢。还没会就和泥?”
二皮笑着反驳了一句,说:“不会才和泥学呢。”
老烟袋摇摇头,笑着说:“呵呵,我不和你说。你小子,小嘴儿巴巴的!”
说完,老烟袋转身走了。
屯子东头有棵大柳树,是屯子里最大的一棵柳树。有人推算,这树足足有百余岁了。此树根深干壮,枝繁叶茂。每到逢年过节,村民有在这棵大柳树上拴红布条的习俗,保佑家人平安。俨然,在村人心中,这就是棵佑福祉保平安的神树。
二皮兴高采烈地来到大柳树旁,还真看见个卖泥人的卖货郎。
这个卖货郎,看样子六十多岁,个子不高,方脸长须,戴顶破草帽,正盘坐在那聚精会神地捏着泥人。捏一会儿,便拿起旁边的烟锅吸上两口,然后又精神饱满地继续捏。在此人面前的地摊上摆了不少形态各异的泥人,个个栩栩如生。二皮见了,格外惊喜,异常兴奋地跑到捏泥人摊边,蹲在那看着那人捏泥人。
那人见二皮专神地看自己捏泥人,笑着问:“孩子,买个泥人?”
二皮用手摆弄摆弄摊上的各色泥人,说:“你的泥人捏得真好。”
那人“呵呵”笑道:“是吗?你这孩子真会说话。买一个吧?”
二皮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不想买,我想和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