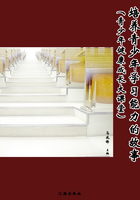白行之轻蔑地看着他:“你能有什么事儿。”
白浩有些不服气,想反驳。
坤叔劝慰道:“少爷,少说两句,今天人多。”
白浩没了言语,跟着白行之走进了舞厅里。
一辆车风风火火地赶来,只见一个急刹车,车子停在了舞厅的门口。一个大哥式的人傲气十足地整一下衣服,神气活现地走进了舞厅门口。
他走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门,每一道门的守卫都客气地朝他低头致意。
“咣”一声巨响,最后一扇打开了。里面坐满了人,每一个都是大腹便便、气度不凡的人,白浩和坤叔站在白行之的后面。
仁字袍哥白行之坐在中央,指斥道:“老九,你来晚了!”
义字袍哥老九丢了一个“歪子”理:“不好意思各位,堂口出了点事情。”
白行之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白行之环视了一下四周,开口说:“今天袍哥仁、义、礼、智、信五堂都到齐了。我想告诫大家,袍哥兄弟不能内乱,要维护袍哥定下的规矩,做正当生意,做正当买卖,才能生意兴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今天是我们从马帮,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当然大家也知道白某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都有赖于袍哥兄弟们长久以来的帮持。大家出力,我白某人自然不能亏待大家。我管理的朝天门码头、马帮还有舞厅,多少还是有点盈利。今天是分红的日子,这些钱大家分了吧。”
白浩起身赶紧拿起一个皮箱,潇洒地打开皮箱,将皮箱里的五袋钱抛向了空中。一摞摞的钱重重地落在了桌子上。
老九轻蔑地笑了笑,点燃了雪茄。
坤叔低声与白行之耳语着,白行之微笑着点了点头,转身道:“一人一份,大家应得的。”
礼字袍哥张千笑了笑,说:“白哥,您只要一句话,我们礼字袍哥兄弟们为你赴汤蹈火,但我们可不是叫花子,你拿那么一点钱给我们,兄弟们吃个屁啊!”
智字袍哥南爷也站了起来,不满道:“白老爷,你定的规矩,我们智字的袍哥兄弟可从来没有就范过。大家都尊重你,可你也别太过分了。”
“你说什么?要造反了是不是?”白浩激动地喊道。
“白浩……”白行之示意道。
信字袍哥奇二娃站了起来:“白老爷,我们为你出生入死,赚钱的生意您都掌管着,再说你的朝天门码头也是货运最为频繁的,每年发那么一点饷银给我们,你觉得你够意思吗!”
智字袍哥南爷痞气露着说:“白老爷,明讲了,我们不服。”
“啪”的一声,一把枪放在了桌子上,坤叔站了起来目视着大家。
大家都被他震慑住了。
“有人不服吗?”坤叔问道。
没有一个人说话。
白行之目视着五堂袍哥们,随手拿出一只雪茄,一旁的保镖毕恭毕敬地为白行之点上火。堂口里安静得连掉一根针都可以听见。
“按理说我白行之是仁至义尽了,赚钱的生意我掌管着,你们没有管吗?
五堂袍哥既然守的是码头,自然就有船夫脚力,于是‘拉滩帮’、‘梢船帮’、‘转江帮’、‘搬运帮’纷纷出现,各帮又有‘帮头’,垄断了码头,盘剥工人,无所不用其极,成为霸据一‘帮’的头目,这些人不是在座的大家吗?”
白行之向四处看了看,没有人说话。“我就想你们给我一个解释。昨天在黑石子的数名工人的浮尸是怎么一回事?”
“我对着五堂袍哥说了无数次了,我白行之要当正经的买卖人,我们处在两江围绕的地方,江是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北方的粮食、布匹、盐等重要物资都是通过大江运过来的。我们手里捏着的是各地往来的大码头,你们不会缺钱花的,我们处在江湖之中,但一定不能有地痞无赖之人的痞气!我们讲的是‘为兄弟两肋插刀’、‘袍哥人家不拉稀摆带’的‘耿直’和‘义气’!”
礼字袍哥张千直白道:“我们礼字袍哥知道海底的规矩,绝不会做杀人放火的事情。”
智字袍哥南爷拍着胸膛,豪气道:“我们智字袍哥也不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信字炮哥奇二娃站了起来,坦诚道:“白老爷,请你一定要相信你的袍哥兄弟们啊!”
“你们没有做吗?”白行之提高了嗓音。
义字袍哥九爷奸诈地笑道:“白哥,你现在追究数名工人的浮尸问题,我倒还真想问问义字袍哥洪五爷的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白行之的脸色似乎不太好看。
义字袍哥九爷理直气壮:“谁都知道有人送去洪五爷家的棺材上,还写着白公馆的挽联。”
白浩低着头。
所有人凝视着白行之。
白行之看了看一旁的阿坤,随即凝视着面前的五堂兄弟,内心复杂地掩饰着他的情绪。他想,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袍哥弟兄们还认我这个仁字袍哥白老爷吗?重庆江湖码头又有谁来主持呢?那将是一场尔虞我诈的血战啊!我真想退出江湖过我的平静的生活,可是江湖不平静啊,你不招惹他,可他要招惹你。让你一天都不安宁,甚至葬送于他们的屠刀下,这就是鱼龙混杂的江湖……
阿坤会意地点着头,白老爷吐出了浓浓的烟雾,认为是时候了,应该把话说清楚,告诉他们外面的传言是事实。
白行之突然高声道:“洪五爷……我派人杀的。”
一片议论声。
信字袍哥奇二娃诧异道:“洪五爷可是义字袍哥的舵把子之一啊,白老爷您这样的行为未免太过了吧?”
礼字袍哥张千将手中的盖碗茶一扔,指斥:“白老爷,袍哥以‘天伦八德’为号召,核心就是一个‘义’字,仗义狭义职能兴袍灭空,不可兴空灭袍啊!”
智字袍哥南爷不解地说:“都是滴血结盟的兄弟,你怎么下得了手啊。”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加入袍哥之时,我们的海底,也就是帮规,十条十款。出卖码头挖坑跳,红面视兄纪律条。”白行之道。
“灭弟灭兄斩头脑,骂娘骂母割舌条。”义字袍哥九爷道。
“越礼犯法自拔吊,奸淫恶霸刀上抛。”白行之接着道。
“第五拜兄要敬道,红面杀兄第六条。”义字袍哥九爷道。
“第九为人要正道;越礼犯法第十条。”白行之接道。
“洪五爷到底犯了什么事情啊?”礼字袍哥张千问道。
白行之霸气地扔掉手中的雪茄,高声地说:“我想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码头附近都陆续成立了各地的商会馆,比如湖广会馆、广州会馆,他们都是外地商贩在码头上自己建立起的帮派。翠微门是绸帮的仇得远,泰安门是粮帮的杨四爷,临江门粪帮的文哥,千厮门的纱帮王光辉,储奇门的药帮袁二爷,凤凰门的屠夫帮涂中天,南纪门的菜帮菜纪,当然还有洪崖门的船帮梁三哥,为什么我会对洪崖门堂口的洪五爷下如此重手?因为他与船帮梁三哥勾结起来了。”
“白哥,用词不当啊,这叫合作。”义字袍哥九爷说完就奸笑了起来。
“合作?用我们袍哥的码头贩运军火、鸦片吗啡叫合作?洪五爷的死我也是给五堂的人一个警告,不要被利益冲昏了头脑,有些钱是不该你赚的!否则……”白行之没说下去,只是冷冷一笑。
信字袍哥奇二娃有些胆怯地说:“白老爷,你不能不相信我们啊!”
白行之摇了摇头,指斥道:“相信你们?你们是人还是鬼呢?”
智字袍哥南爷诧异:“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白行之愤怒道:“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码头上的军火、鸦片是谁在贩运,啊?……又是谁在破坏我们定下的规矩?”
一个小兄弟从门外跑了进来,对着义字袍哥九爷的耳朵嘀咕了几句。
九爷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礼字袍哥张千坦诚地站了起来:“白老爷,我必须替我们礼字袍哥兄弟说两句话了,我们需要武器,我们需要军火。烟草、鸦片我们可以不运,但是军火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强大,有了军火没有人敢来侵犯我们。”
“好!至少你承认了你们临江门运过军火,还有谁愿意主动坦白的?”白行之拍手叹道。
礼字袍哥九爷黑着脸,抑制不住心里的怒火,从包里摸出一把枪对着白行之。
白浩和身后的四五个保镖同时举枪对准礼字袍哥九爷。
所有人都表情很僵硬地看着他们。
礼字袍哥九爷的眼睛死死地看着白行之。
坤叔上前用头顶住九爷的枪口,用手指了指,要他从这里开枪。
白行之知道九爷是心虚的,想吓唬吓唬人,他敢开枪吗?不敢。这是一场心理素质的比拼。他自信地看着阿坤笑了笑。
礼字袍哥九爷的手在扳机上颤抖着,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重重地将枪放在了桌子上。他看着白行之,说:“只准你州官放火,不许我们百姓点灯,你做得太过了,白行之——白老爷!总有一天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白行之上前拍了拍九爷的肩膀,藐视地笑道:“这就是心理素质的比拼和较量,当着五堂兄弟的面你输了,今天终于叫我一声白老爷了?你想警示袍哥们我白行之做人的标准,也想重塑重庆江湖袍哥的地位。我从来不会运鸦片,当然我也不允许你们碰鸦片,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赚钱的方法有很多,但不能害人。大麻是什么?它是会让你上瘾的,它在侵蚀你的大脑,它在腐化你的灵魂,它在统治你的精神。它可以让一个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它可以毁灭一个人,当你们赚着这样的钱的时候,你们的良心不会遭到谴责吗?”
白行之拿过白浩手中的枪,向天花板开了一枪!
“我知道大家对我有意见,因为我有这玩意儿,而我不允许你们有。”白行之对着枪头吹了一口气,“它是可以一击致命的,你们是我的兄弟,我不想看到兄弟之间的残杀。你们懂吗?你们懂我的苦心吗?我不想兄弟们打打杀杀,血流成河,如果大家都有了武器,那么我们不会再坐在一起,我们是敌人,甚至是仇人。”五堂袍哥仁、义、礼、智、信的兄弟们,各怀着自己的心计,都低下了头。
白行之回到书房,望着前妻林玄清的照片,上前轻轻地抚摸着,一会儿摸摸脸,一会儿摸摸眼睛,一会儿又摸了摸那张小巧精致的嘴。
“玄清……我有恋爱的感觉了,就像当初和你在一起的那种,你能理解我吗?你会怪我吗?她很漂亮,很像你,笑起来甜甜的,我想我真的是爱上她了,你是不是在笑话我啊?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居然对一个小女人动情了,而且还如此神魂颠倒。”
片刻,白逸芸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看着爸爸自言自语神魂颠倒的样子,轻轻的“嗯”了一声。
“逸芸……我给你说了多少次了,进我的房间要敲门。”
“我又不是故意的。”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情?”
“您怎么知道我找你有事啊?”
“快点吧,简单点,直接点。”
“哎呀,爸,你怎么这样说我呀!”白逸芸撅起了嘴,娇嗔地跺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