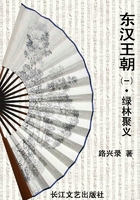现场瓦刀与砖块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用铁锨和泥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干砖泡进水里冒气泡也吱吱响,现场干活的人喧哗嚷叫,十分热闹。
仅半天时间,四眼窑洞的地基挖下去,又用砖砌上来了。工程进展顺利。
逢春四下看看,到处插不上手,只能将堆放在较远处的砖往渗砖的地方搬。他动手搬砖,何蓉蓉帮着一起搬。没有围裙,不一会儿蓉蓉的红格子上衣弄脏了,百谦看见了,说:“这女子,看把你衣服弄成这了!赶紧赶紧,甭弄了。”何蓉蓉笑着说:“没事没事,叔。”百谦说:“逢春,你还没吃饭,赶紧回去,等你妈把晌午饭弄好,你来叫大家吃。蓉蓉也赶紧回去。”
“蓉蓉,你先回去。我再努(停留)一会儿。”逢春对何蓉蓉说。
何蓉蓉不高兴,但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好嘴噘着走了。
快到吃晌午饭的时候了,逢春早已饿得满头虚汗眼冒金星,才在父亲催促下回家。他看见母亲正和几个邻家妇女忙着弄饭,婶子俊香也在。叔父家的双胞胎峰峰、川川站在一旁哼哼唧唧:“我要吃,我要吃呢。”奶奶赶忙把孩子拉开:“面还是生生,吃狗屁哩,赶紧过来,甭脏嚷人。”
锅台上支着压饸饹面的床子,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气。将和好的面搓成圆柱状,放进饸饹床子的圆孔里,再把柱状的木头杵子对准圆孔,用杠子压下——这工具采用了杠杆原理——呈线状的饸饹面就从床子下面网状的小眼眼挤出,直接进入沸水,煮熟,捞出来,从凉水中一过,晾在篦子上,拌少许熟油防止粘在一起。另外一个炉子上,中等大小的铁锅正煮浇面的臊子,主料是豆腐、葱、萝卜丁,闻起来挺香。
“逢春,你先吃些,早起吃了一碗煎水泡馍,饿到这阵儿了。饭马上就好,你吃了,再去叫你楦窑的人把活儿停下,回来吃饭。”母亲交代说。
楦窑的人回来,洗洗手,一人一个大老碗,用筷子抄上饸饹面,浇一大勺子臊子,或坐或蹲,“呼噜呼噜”吃饭。
“嫂子做的饭好吃,我能咥三碗。”一个帮忙的说。
“你咥嘛,尽饱。”清竹说。
干活的都是好饭量,一般人至少两碗,多的三碗四碗,好几篦子饸饹面一会儿风卷残云被消灭了。
“吃烟吃烟。”逢春拿上早已准备好的红盒子“宝成”牌纸烟,给放下饭碗的人散发。
烟点着,香香地抽着,干活儿的人满脸的惬意和满足。
“饭后一锅烟,赛过活神仙。美得太嘛!”
“饭吃饱,烟瘾过美,再吃住咥,要对得起主家这饭呢。”主事的匠人雷振才说,“后晌就要搭架子,百谦哥,搭架子的板凳、板子、绳啥的,都预备停当了没有?”
“停当了,没麻搭。”逢春爹说。
后晌,在楦窑现场,逢春看见叔父拖着石膏腿,一手拄棍子,另一只手拿铁锨和泥。
“二大,你甭弄了,你腿上有伤,坐下指挥,我来和。”逢春说。
“楦窑砌砖的泥好和,不搅麦秸,省劲,主要是掌握稀稠。这活不重,不过有技术哩,我能行,你恐怕弄不了。”叔父说,“架子搭起来了,渗好的砖要往上搬,你搬砖去。”
看着家人和亲戚邻居全力以赴为创建新家辛勤劳作,赵逢春只能竭尽全力干活儿。到了晚上,他的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不光给咱楦窑,还要在突击队干,非把娃挣日塌不可。”晚上,母亲在父亲面前怨怅,“逢春还没服下呢,能受得了这罪?”
“唉,没办法,生到这黄土地上,服不下也要服,受不了也得受。叫他给拴牢请假,娃还要进步,硬硬地不请。自家楦窑,亲戚邻居都帮忙,他不干说不过去,看着心疼也没办法。哎呀,我这腰也成硬的了,翻个身都艰难。”
果不其然,赵逢春累出毛病来了。
楦窑第三天,逢春在突击队带夜班。半夜收工,他觉得全身乏力,满头虚汗,汗衫紧贴在脊背上,走起路来步履维艰。
“逢春,你咋哩?”何蓉蓉及时出现在他面前。
“我不咋。”小伙子还要强撑,保住自尊。
“还不咋?我看你走路浪(踉跄)哩,我用架子车把你拉上。”何蓉蓉说。
“没事,不用。”逢春抹一把冷汗,再用手拍了拍脑门,觉得清醒了许多。
“我跟你厮赶着走。”何蓉蓉说。
“能成。”逢春在乡间土路高一脚低一脚走着,感觉头重脚轻,脑子一阵儿清醒一阵儿糊涂。
“逢春,我问你个事。拴牢叔把灵侠开除了,还扣她工分,这对不对?”何蓉蓉问。
“嗯?这事我也说不清。”逢春回答得很随意。
“你也不讲究是非黑白?还是突击队副队长呢!”何蓉蓉对逢春的回答很不满意,语气愤愤不平。
“那你说,这事该咋处理?”
“我说?要我说不能光处理女的。男的都不算犯错误,光灵侠错了?
这不公道嘛!要开除都开除,要扣工分都扣工分。”
“拴牢叔说,母狗不摇尾,公狗不上身,还说,哪达有棉花遇见火不着?”尽管是黑夜,逢春对何蓉蓉说这些话仍然感觉难以启齿,脸都红了。
“耶,耶,耶耶耶,这是啥话嘛!叫我说,纯粹欺负弱女子哩。我以前觉着拴牢叔啥都对,从这件事看,他也欺软怕硬,一碗水端不平。是不是男人都向着男人?”
“没有没有。拴牢叔没办法,胡搞的男人不是一个两个,有句话叫法不治众,拴牢叔说了,他会想办法照顾赵灵侠。哎呀,这事我说不清,这阵儿头昏得不行。”
走到何蓉蓉家门口,要分手,蓉蓉伸手摸了摸逢春的额头。
“哎呀,烧得太。你先回去,我屋里有退烧药,一会儿给你送去。”
“算了算了,半夜了,你赶紧回去睡觉,我没事。”
“还没事呢,烧得跟火炭似的!你回去甭关门,我一下下就来咧。”
果然,逢春进家不久,何蓉蓉送药来了,安乃近,还有索密痛。
逢春母亲也没睡,她让儿子服了药,说:“你发烧哩,蒙上被子,捂一身汗,就好了。”
回到小窑洞,清竹对丈夫说:“老何家女子对逢春咋恁好的?该不会有啥事?”
百谦睡得迷迷糊糊,说:“你操那闲心!赶紧睡觉,明儿还要早早起来拾掇饭哩。”
第二天,父母没有叫逢春起床。他睡到半早晌,一睁眼,看见何蓉蓉坐在床头。
“哎呀,这时候了!”逢春一下坐起来,揉着眼睛。何蓉蓉捂了嘴“哧哧哧”笑,逢春才发现自己光着膀子。“哎呀,你咋在这儿呢?”他赶忙寻找家织的白布衫,慌里慌张往身上套。
“我到楦窑的地方去了,看你不在,估计你还睡哩。你妈在前院忙着,你奶叫你二大家的娃缠住了,没人管,我就进来了。”
“咝——哎哟,我咋浑身疼呢?”逢春伸展一下腰肢,觉得全身不得劲,“不行,我要赶紧到楦窑那达去哩。已经迟了,这会儿才去,像啥话嘛!赶紧,蓉蓉你出去,我先把衣服穿上。”
“怕谁把你看着了!”何蓉蓉嘴噘着出去了。
逢春龇牙咧嘴穿好衣服赶忙往外面冲:“妈,你咋不叫我?迟成啥了!”
“你咋起来了?我刚才摸你的头,烧得厉害,继续睡去,楦窑那达人多,不少你一个。”母亲说。
“不行不行,我要去哩。”逢春说罢,舀一瓢水倒进脸盆,在脸上“扑哧扑哧”几下,再用毛巾沾了沾,赶紧跑出去了,何蓉蓉在后头追着。母亲在身后喊,让逢春吃点儿东西再去,他仿佛没听见。
按照修建砖窑的工艺流程,“窑腿子”砌起来,中间要搭起架子,支好两道弧状的“楦弓”,再在“楦弓”上铺“楦板”,这样形成洞状的模具——“窑楦”。紧接着,依托“窑楦”,将砖摆放成窑洞形状,再用很多磁片楔进砖缝隙,最后用泥浆浇灌。同一眼窑洞需分段完成,像逢春家这样的小窑洞一般分为两段施工。做完一眼窑,接着完成相邻的另一眼。施工过程中,“窑腿子”用木头顶着,以防止单方面受力或受力不均匀导致歪斜、倾倒。等所有窑洞都“楦”好了,再在上面压八九十公分厚的黄土,四周用筑土墙的方式夯实,和“窑帮”形成一个整体,护卫砖窑洞坚固耐用,历经数十年上百年而不衰。
楦窑工程即将完成,最后一眼窑洞砌最后一块砖之前,要贴上“合龙大吉”的红纸贴,悬挂红绸,燃放鞭炮,叫做“合龙口”,等同于盖房子举行上梁仪式。仪式过后,主家要宴请所有参建者以及拿着鞭炮礼物来祝贺的亲邻。
赵逢春家“合龙口”,老天不作美,乌云密布。“合龙口”的鞭炮刚刚燃响,天空传来深秋季节少有的惊雷,随后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窑顶上、脚手架上干活的人都赶忙撤下来避雨。
“窑底下敢不敢停人?”有人问。
“一般情况下没问题。大家最好避到邻家去,甭在新窑里头努。”雷振才说。
干活的人把衣服顶到头上跑出去避雨。
“振才,这大的雨,要紧不要紧?”百谦问匠人。
“没事没事,只要不下霖雨。万一下霖雨,就得到粮站借帆布去,盖上,下十天八天雨都不要紧。”雷振才说。
一阵狂风暴雨过后,雨小了,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楦窑合龙口,本来要在院里支八仙桌摆筵席招待大家,因为下雨,除了匠人和最重要的客人在爷爷奶奶大窑里摆一张桌子之外,其余人把各种菜舀到碗里,一人端个大老碗,或蹲或站,找没雨的地方分头去吃。
吃完饭,百谦带着人,拉着架子车,冒雨到公社附近的粮油收购站借帆布。不巧,收购站的两块大帆布已经被邻近杨家大队楦窑的人家借走了。
一直到晚上,雨还不停。借不来帆布,百谦和逢春舅父等几个人把家里仅有的几个塑料袋子,以及床单等物品都拿来盖窑顶,但基本不管用。
这些小东西经不起风吹,一小块一小块的,缝隙太多,往里面进水。找邻居或者生产队帮忙,最多能找来几块小小的塑料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逢春一家眼巴巴盼望老天爷开眼,千万不能下霖雨啊!
12.无情坍塌
第二天,雨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尽管不再刮风,也不再雷鸣电闪,但细密的雨线无休无止,表现出老天爷韧性的力量。逢春家新楦成的窑洞顶部出现无数小缝隙,从里面看透着亮光,这是因为砖缝里的泥浆被稀释,随着雨水流走了。
“老天爷呀,再不敢下,再下就瞎了!”来到现场观察的泥水匠雷振才说。
“这咋弄哩?这咋弄哩?”逢春的父母急得手足无措。
因为下雨,农田基本建设也停工了。尽管家人担忧暴露在雨地里新窑洞的安危,逢春还是捂着被子睡得天昏地暗,他不仅感冒,而且累坏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休整,逢春爬起来,洗把脸,感觉神清气爽。
“逢春,你出来,我给你说个事。”小伙子正享用母亲给他单独做的葱花辣子油泼面,何蓉蓉来找他。
“啥事?”逢春端着饭碗来到院里,何蓉蓉穿一件绿色有小白点的塑料雨衣。
“有好事。”何蓉蓉说,“今儿黑了到大队开会,去了你就知道了。”
“你不给我透点儿消息?”
“就不给你说,叫你急着。”何蓉蓉调皮地眨巴眼。
“不说算了,我才不急哩。”逢春故作矜持。他再次感觉到这女子的眼窝太有吸引力和杀伤力,特别好看。不知从何时起,赵逢春对于何蓉蓉套近乎已经不再厌恶,反而觉得心情愉悦。
“我说了,你咋奖励我?”
“叫我妈给你下一碗面,多泼些油。”
“耶,耶,耶耶耶,我肚子不饿。”
“那你说咋奖励?”
“我说,我说嘛,就……就就……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叫你咋样奖励我。算了算了,我说了吧,今儿黑了你要宣誓入团!”
“啥,你说啥?”逢春兴奋得几乎跳起来,“真的,你没哄我?”
“看你,我啥时候哄过你?你不相信算了。”
“信呢信呢,我信。黑了我叫你,一搭里去开会。”
果然,这天晚上雷庄大队团支部举行新团员宣誓仪式,赵逢春和其他4个男女青年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手宣誓之后,何拴牢让逢春代表新入团青年讲话。赵逢春上中学就万分向往共青团组织,曾为加入青年先进分子的组织作了积极努力,可惜他的努力被章老师扼杀了。回农村以后,他觉得主观努力不够,距离共青团员的标准还很远,但却很快被团组织接纳了。这个天大的喜事来得太快,让逢春喜出望外,十分激动。他当着全大队团员青年慷慨陈词,表示绝不辜负党组织、团组织对自己的期望,努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锻炼成长,争取早日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入团仪式上,大队革委会主任郭佑斌讲话,他照例念了一连串毛主席语录,青年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等。郭佑斌虽然没文化,却背诵了许多毛主席语录,而且记得很准,引用起来绝不出错——谁要把毛主席语录背错了,那是政治错误,弄不好会招祸。
回家路上,雨淅淅沥沥还在下。走到离家不远的那段村巷,又剩下两个人,何蓉蓉主动拉了逢春的手。
“路滑,差点儿栽了,你把我拉上。”何蓉蓉说,“今儿佑斌叔讲话还算‘咹’得少。我数了,只‘咹’了49下。”
“你咋是这?”逢春没有将手抽出,反客为主紧紧拉住何蓉蓉,“以后再甭数了,好好听讲话的内容,甭管人家‘咹’多少下。”
“听他讲话,我光能听着‘咹’‘咹’‘咹’,旁的啥也听不着。”
“你耳朵有毛病哩。”
“你耳朵才有毛病哩!哎,你说过,要奖励我。”
“我不知道咋奖励嘛。”
“努住,不走了,我教你咋奖励。”何蓉蓉拽了拽逢春的手,停下脚步,她跨一步挡到逢春面前。
“就这么。”何蓉蓉说着,踮起脚尖在小伙儿面颊上亲了一口。两个人头上都往下淌雨水,逢春感到嘴里有略带土腥的雨水味道,脸颊发烫。
“我没学会。”逢春说。
“你来嘛。”何蓉蓉的口气很有几分撒娇的味道。
“那,我真来啦?”赵逢春越发觉得脸上火烧火燎。
“你快来嘛。”何蓉蓉的语气更有黏性,颇具诱惑力。
逢春在何蓉蓉额头上轻轻一吻。
“不嘛,这儿。”何蓉蓉抱住逢春身子,努努嘴儿。赵逢春虽然看不清楚,但他感觉到了。小伙子鼓足勇气,把自己的嘴向何蓉蓉双唇探去。
两个年轻人真正地接吻了。先是犹犹豫豫地试探,再到认认真真地做,后来尝到甜头不忍舍弃。在整个过程中,何蓉蓉比逢春主动得多,投入得多。吻得比较深入了,逢春体味到跟何蓉蓉的吻是一股略带土腥的雨水味道,和经历过的柳雅平嘴里的烤红苕味道截然不同。
连阴雨下到第六天,赵逢春家新楦的4眼砖窑洞轰然倒塌。
那是因为雨水将砖缝的泥浆冲走了,无数砖头与砖头组成的窑洞缺少了黏合剂,因而也缺少了作为整体继续存在的合理性;那是因为尚未完工的窑洞无论顶部还是“窑腿子”都在雨水的作用下变软了慢慢也就变瘫了;那是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论社员家庭还是生产队集体都穷得没有诸如大块帆布、整卷的塑料薄膜等可以用来保护半成品窑洞;那是因为赵逢春的爹百谦这样的农民群众对于气候变化和宅院建设的成功系数缺乏科学的预见性;那是因为以乡间泥水匠雷振才为“总工程师”的窑洞建设队伍既没有像若干年以后的建筑单位有经过权威部门鉴定认可的资质,也没有相应的工程监理或者别的技术监督……坍塌无可避免。
坍塌不期而至。
坍塌不以逢春的父母担心、忧虑和向老天爷乞求而改变。
相连的窑洞倒起来像多米诺骨牌,像农村人将无数砖头排成和多米诺骨牌一样原理的“狗撵兔”,一个倒下去,其余的相继倒下去,没有任何力量能中止这个过程。
窑洞倒塌发生在清晨。百谦和雷振才、逢春的舅父等人就在现场,但他们无计可施。稀里哗啦的窑洞倒塌声让百谦蹲下身子捶打头颅紧接着一屁股坐到泥水里,逢春的母亲听到消息第一反应是号啕大哭:“爷哟,这该咋办呢?老天爷呀,你要人的命哩!呜呜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