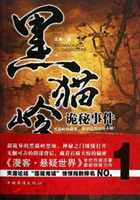“陈林,你在指挥学院的游泳池里刚刚学会的游泳,你就负责把握方向,我来负责动力推进!”我说道。“感动死我了,早知道会有这样的待遇,我早把脚给扎个窟窿该有多好?”陈林轻轻地游到了筏子的前面,还没有说话,欧文明同学便说道。
欧文明同学本来就是我们三个人中体重最轻的一个,所以在水里推起他来一点也不费力气。“别那么客气,我们三个换了谁被扎了,另外两个也都会这么做的。”陈林说道。
“那可不一定,如果是马斌的脚受伤了,我也懒得推他,他体重那么沉,还没有到达终点,咱俩肯定都被累死了。”欧文明同学说道。
“鄙视你。”我边骂边把欧文明同学的脑袋往水里浸了一下,让他来了一个辣辣鼻,欧文明同学便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煮熟的鸭子,净剩嘴了你!”我们三个边说边往水库中心走过去。
这水库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概念里的水库。据当地的老人们讲,这里原来就是一个天然的小湖泊,后来是日本鬼子就势造的水库,小鬼子被赶出中国以后,当地政府变废为宝,成了当地重要的水利枢纽。因为当初是依湖而建,所以这个水库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大。又据附近村子里的老人讲,此水库方圆达数十平方千米,水里不但多怪鱼,而且自古就是方圆近百里村子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最佳殉情场所!
我边在后面推,边把在村子里打听到的一些关于这个水库的传闻说给陈林和欧文明同学听,欧文明同学和陈林边听我的讲述,边配以适当的语气助词。比如,“喔”“啊”“唉”“嘿”“是吗”“不会吧”。当我继续讲道:“传说这个水库有一种鱼叫“巴里巴拉鱼”,这种鱼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专喜吃男人小弟弟,而且一旦咬住之后,任凭你怎么拽它,它都不带下来的,你就是把它的身子用刀子斩断,它的嘴也不会松开你的小弟弟。为此,科学家们专门抓了几条回去加以研究。几十年过去了一点成果也没有,也不知道是科学家们太笨了,还是这鱼太诡异了,一切都不好说。”
“为什么叫巴里巴拉鱼?这么奇怪的名字!”躺在竹筏上的欧文明同学好奇地问道。“问得好!”我说,“这正是我要跟你们说的。”
“这种鱼为什么叫巴里巴拉鱼呢?陈林?你想知道吗?”我故意朝前面的陈林喊道。“要说就说,不说拉倒,少吓唬我,我在四川老家就是捕鱼长大的,什么样的鱼我没有见过?什么巴里巴拉鱼?还鸡巴鸡巴鱼呢,我怎么没有听说过?”陈林的语气虽然很硬,但我能感觉到他开始有点害怕了。我甚至能感觉到,他裤裆里的小弟弟正在本能地开始伪装和缩小。
别他妈的再缩了,我心里说,本来就不大,万一缩回去,一会儿长不出来怎么办?
想到这里我不禁呵呵地笑出声来。“马斌,老子把耳朵竖得跟驴耳朵似的,你倒是说啊,怎么还有放半截屁的习惯?”陈林骂道。
“我不说是为你好,说出来怕把你给吓住。我如果真的告诉你,你听完之后,可千万不要后悔啊!”我故作悬念道。
“有屁快放吧,别一会儿把陈林给急死了。”欧文明同学嚷嚷道。“好好好,我来告诉你,这种鱼之所以叫巴里巴拉鱼,是因为它生活在水的表层,当它要对某一个人小弟弟发起攻击的时候,总会用身体一个特殊的发声器官,发出“巴里巴拉”的声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听到“巴里巴拉”的声音,那么他和他的小弟弟永别的时间即将到来!”
“陈林,你现在听到巴里巴拉的声音了没有?”我开玩笑地问道。陈林不说话。“马斌问你呢陈林,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听到巴里巴拉的声音了?”欧文明同学也随着问。
陈林还是不说话,死一般的寂静,忽然不远处有“巴里巴拉”的声音传来。陈林小声地说道:“马斌,你听,巴里巴拉的声音,你听,你听,真的是巴里巴拉的声音。快点告诉我,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是在说着玩的,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一种鱼是吗?怎么会有这种鱼呢?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是不是?”陈林都快疯了。
我也急了。“我刚才的那番话本来是要逗你玩的,以前我在团里的时候,也只是听说,我真的没有见过。”我对陈林和欧文明同学说的是实话。
即使这种巴里巴拉鱼不咬小弟弟,但它肯定应该是种奇怪的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鱼,我心里想,就我们现在的状态,别说是怪鱼了,你就是随便来一条草鱼,都能把我们吓傻,我们早已经手无缚鸡之力。
我们静静地往前推,“巴里巴拉”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要不我们绕道吧。”欧文明同学建议道。“你啥时候胆子才能大一回让我新鲜新鲜?
不就是鱼吗?怕个球啊。”我不屑地说道。
“你他妈的肯定不怕了,万一要是来了什么东西,你们两个转身游走了,把我留下来当鱼饵?想得美!赶快调头!”欧文明同学多少有点急,“不要让我对你们两个刚刚产生的一点好感再消失了。”
我和陈林不理会欧文明同学,只顾着往前推。“你们要是再不停,我就往下跳了啊,你们听见没有?我往下跳了,我要往下跳了……”欧文明同学一个劲地嚷嚷。
“要跳就跳,叫个蛋啊你,跳吧。”前面的陈林说道。“你以为我不敢……”欧文明同学的话还没有说完,只听轻轻的扑的一声响,筏子已经靠岸了。
“吓死老子了,什么他妈的巴里巴拉鱼啊,你这叫犯罪懂吗,马斌?”
欧文明同学一条腿着急地往下蹦,一边骂道。
“欧文明,不是我说你,就北方这种淡水水库里能有什么怪物?都怪美国大片,瞧把这孩子吓的。”陈林说道。“刚才那巴里巴拉的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我好奇地问道。
我们三个边说着话,边把自己的身子往岛上挪,我们这才发现刚才那“巴里巴拉”的声音,是海岛周围的堆积的垃圾与水波动发出的摩擦声。
当我们彻底把自己弄到岛上之后,瞬间就像散了架子似的,瘫软在沙滩上。“得赶快找点吃的。”我费了半天的劲才坐起来说道。“马斌,你还是人吗?我们休息一晚上,明天等太阳出来再去找也不迟啊。”陈林说道。
“你懂个屁!明天早上?明天早上黄花菜都凉了。”我说道,“你以为这个岛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吗?没准现在那帮家伙已经找吃的找了一大堆了!还等?野战生存?准确地说是野战竞争生存!这么屁大的一个地界儿,有五六十个人呢,五六十个跟我们一样的饿死鬼!”
“停!停!”陈林打了一个暂停的手势,“你不要激愤,我们现在就去找吃的行了吧?就现在!您老人家是爷,我们两个是孙子,行了吧?”
“你少跟我扯这些没有用了,这不是爷和孙子的问题,这事关我们三个死活,到现在还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代表欧文明同学鄙视你!”
“你鄙视就鄙视吧,你还代表欧文明同学,你得了吧你!”陈林说着拿眼瞅了一下欧文明同学。“代表得了,绝对代表得了,从今以后,马斌同志就是我的全权代表,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欧文明同学及时声援道。
“他的梁怡怎么不是你的梁怡呢?”陈林一见自己失势,便小声嘟囔道,“我们两个找吃的,欧文明同学怎么办?”陈林问道。“什么我们两个人啊,什么怎么办啊,咱们在这里又不是常住人口,咱们要架上欧文明同学一起走,走到哪里是哪里,要是把他一个人给放在这里,万一被狼吃了怎么办?”我开玩笑地说道。
“你说得也是,一个巴里巴拉鱼,都能把他吓成那样,何况其他的呢。”
陈林说。“现在趁我是瘸子你们就努力糟践我吧,”欧文明同学说道,“等我腿好了,看我怎么样一个一个地把你们给弄死。”
我们三个人边说边架起欧文明同学打算往小岛深处走去,我不经意地一回头。我和陈林给欧文明同学扎的竹筏子映入眼帘,那一瞬间,我从心里佩服我自己,我怎么就这么有才呢?“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裁(才)缝?”
我把欧文明同学交给陈林一个人先架住,然后跑到岸边把筏子拉了过来。
来,躺在上面,我用手指指筏子,对欧文明同学说道。
“这,这行吗这个?”欧文明同学问道。“别他妈的啰唆了,让你上你就上,你要是不上我上,你们两个拉我。”陈林说道。“呸!不要脸!”
我说道。
我和陈林又一人折了一根软柳条穿过筏子的两侧,分别拴在两个人的腰间,前腿弓后腿蹬。“走咧!”我喊了一声。木筏在我和陈林的拉动下,开始在沙地上缓缓移动起来。“知道吗?这让我想起一幅画来。”欧文明同学说道。“什么画?”陈林问。“《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真太像了。”
欧文明同学回答道。
“你终于有文化了一回,”我回头刺激欧文明同学道,“竟然还知道有这样一幅画?你还知道什么?”我问道。“我还知道今天晚上有暴风雨。”
欧文明同学说。
“暴你个大头鬼啊,这月白风轻的……哎,这月亮呢?刚才不是还挺大挺亮的吗?我还想拿它当烧饼臆想一下呢,这回可完蛋了。”陈林说。
“哎,哎,哎,这什么东西冰嗖嗖地往我脸上落啊。”陈林一边惊奇地摸着自己的脸,一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有暴风雨?”我回头问欧文明道。“因为刚才有几滴雨落在我脸上了,你再看看天上那一大片乌云,傻子都知道要变天,暴风雨?那是我猜的。”欧文明同学回答道。
“夏日天,孩子脸,说变就变,可这家伙变得也太快了点吧,”我说道,“梁怡也没有变得这么快啊。”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咔嚓一声,一个炸雷,便落在了我们旁边的一棵大树上。碗口粗的桐树,竟然被拦腰击断,我们三个人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棵树正是我们三个所要去的地方!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道,“我们就当做是孤岛七日游吧。”“我军新时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倒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陈林说。“我真不知道,我们除了自嘲还能做什么!”欧文明同学补充道。
“那就让我们踏着无数革命先烈开创的革命乐观主义道路,走得更远吧。”我边笑边对陈林和欧文明同学说道。“我们现在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先准备盛水的容器。”我建议道。
“什么意思?你要撒尿?”陈林问。“尿你个大头鬼啊,”我说道,“虽然这水库里的水是淡水,但里面不是还夹杂着味道鲜美的小癞蛤蟆吗?你想不想再尝尝?再说,七天时间可不算短,如果咱们饮用了不干净的水,得个痢疾什么的,那我们可真就白忙活了。”我解释道。
“哎,”陈林用手碰了碰躺在筏子上的欧文明同学说,“你发现没有?”“发现什么?”欧文明同学问。“我们的马斌同志,现在变得越来越成熟了,是不是被梁怡给破处了?怎么也不像我们这部小说上半部里说的那样,毛毛躁躁跟鬼似的!”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发现了,不但成熟了,而且还时不时地间接地教育我们两个人一下,也不知道都跟谁学的。”
“陈林,你能不能让欧文明同学歇一会儿?他现在可是病号,你这样不停地跟他说说说,会把咱们的病号给累死的,你信不信?还不赶快来摘点桐树叶,准备盛水用?”我挖苦道。
“要不要我给你们唱个歌什么的,给你们解解闷儿?”欧文明同学主动地问道。“你可拉倒吧,”陈林说道,“解闷儿?不把狼招来都不错了!
人家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啊。对不起了,我和马斌同志还想继续为革命做贡献,没有想过现在就去死!”
“你能不能唱一首流行的、简单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喜闻乐见的?”
我边摘桐树叶,边问欧文明同学道。“我还以为什么呢?就这么简单的要求?流行?简单?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欧文明同学清了清嗓子说道,“下面由我为陈林和马斌同志献上一首,全世界都流行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并且绝对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鸟人,”陈林骂道,“你都成那德性了,还唱《生日歌》?”“我不唱了,”欧文明同学停住歌声,把脸一扔说道,“就你们难伺候,难道我这首歌没有满足你们的要求吗?简单、流行、喜闻乐见?”
欧文明同学的话刚刚说完,就听啪的一声,又一阵雷电闪过,倾盆大雨一泻而下。真可谓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击袭。
“来看我的,我来给你吟一首诗吧,”于是,在狂风暴雨中,我大声喊道,“……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听我的,”陈林也说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听我的,”竹筏下的欧文明同学也来了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三个人像疯子一样大声喊叫着。
大雨如注,一点也没有停的意思,我们三个人却累了,为了寻求一些心理安慰,勉强地找了一个灌木丛躲了起来,说是躲,其实那灌木丛屁作用也起不到。欧文明同学早已经被我和陈林强行地盖在了竹筏子下面,那家伙还在下面边折腾边喊叫呢:“你们两个家伙算不算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个竹筏子三个人用不行吗?”
“你以为你是金庸笔下的大侠呢?知道得还不少,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呢,”我骂道,“你要是再在下面乱动弹,我和陈林就坐在竹筏上,把你给闷死,你信不信?”“一个没有鸡蛋壳大的东西,能盖住三个人?你是猪脑子啊。”陈林也说道。
“都怪老处男,这家伙忒阴险,”我说道,“事先连一点消息都不透露,我鄙视他!”“对,我跟欧文明同学一块儿跟你鄙视他,他这种丑陋的行径已经不仅仅是练兵方法的问题,我个人感觉他这个家伙小时候的思想品德课肯定没有学好,要不然,他的品德不会这么差。”陈林道。
“说得更大点,就没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怎么能这样搞呢?这种卑鄙的办法,跟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你说是不是欧文明同学?”我朝竹筏下面喊道。
里面连放个屁的声音都没有,我再叫,仍然没有声音。嘘!陈林冲我挥了挥手,示意我把耳朵贴近竹筏听。我冒着瓢泼的大雨,把耳朵贴到竹筏上一听,差点没有气得背过气去。
俺滴那个亲娘哟,欧文明同学竟然打起了鼾声,他竟然打起了鼾声,意思就是说他竟然睡着了!?这什么世道啊,刚才还说同生死共患难呢,这还不到三十秒就睡着了?让我和陈林刚才白白感动了一小会儿。今生今世,能交到这么恶心的朋友,也没有白白托生一回人不是?
雨渐渐小起来的同时,东方也露出了鱼肚白。“看见没有?”我对陈林说道,“今天是个好天气!今天是个好天气!”陈林没有说话,竹筏子却被欧文明同学掀了起来,这只可恶的非洲黑猴子,从里面露出头来,左看看右看看,那样子绝对是在看风景,而丝毫没有注意到,在他的旁边有两个大活人。
我的这个气啊,不禁又想起昨天晚上他打鼾的事,真想上去给他一老拳,把他的另外一个腿也打折。但我用一个理由说服了我自己不去揍他,那就是,像欧文明同学这么恶心外带不要脸的人,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空前绝后,我们就把它当恐龙化石保护起来吧。
饥饿感如潮水般袭来。“我很饿!”欧文明同学直不愣登地说道。我和陈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里说我们还饿呢。
“这个家伙,肯定是我们上辈子的冤家,这辈子的仇敌。”我骂道。
“你骂谁啊?”陈林问。“还有谁?老处男!”我回答。“对,他是该骂,”
欧文明同学说道,“科学研究表明,凡是三十岁以上男人没有结婚的,女人没有嫁人的,基本上都有点心理变态,所以说,老处男的行为可以从心理学上加以解释,但不管怎么解释,仍然让我觉得可恨。”
“不要埋怨了,发牢骚有个鸟用?还不如去河边捉两只蟹吃呢。”陈林建议道。“连他妈的火种都没有,看起来我们在未来的七天里,要真正地返璞归真了。”我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