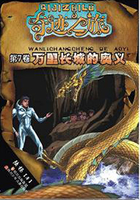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得厉害,额头的青筋一跳一跳的,两边的太阳穴也胀得难受。回想昨夜梦境无数,却没有一个记得清楚,唯一一个有些清晰的画面里我好像仰面躺在地上,一群面目模糊的人围在我的身边窃窃私语,不时地对我指指点点。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只是觉得头顶的天空是那么的高远,蓝得惨然。
到公司的时候,差一分钟八点,还好我跑得快,要不然又是一次迟到。刚进办公室,赵京就告诉我陈总刚刚来过,于是我放下皮包,直接去敲陈舒洋的办公室门。
推门进去的时候陈曦正和陈舒洋说着什么,看到我进来立刻闭上了嘴。陈舒洋看我进来就对陈曦说:“你先回去吧,你说的我会考虑的。”然后陈曦笑着朝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陈舒洋把桌子上的一张报纸捡起来叠好放在门口的报纸架上,转身回来时手里面端了两杯咖啡。顺手把其中的一杯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回头示意我可以坐下说话。
“昨天,谈得还愉快吧?”陈舒洋笑着问。
“还行,基本上能拿下海蓝和临江的点。”我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很苦。
老丁是海蓝支行的行长,刘云那老东西是临江支行的行长。昨天展胖子告诉我姓丁的玩得挺“嗨”,百分之百能拿下这个点,另外的刘云,我倒是更有把握,别忘了我手机里还有几张照片呢!他若是敢反悔,我立刻把这些东西发到网上,顺便发给西兰的几家报纸,标题都想好了,就叫“某行长深夜嫖妓实录”。
“很好,”老陈点了点头,露出满意的表情。
“陈总,这是昨天的发票。”我看老陈心情不错赶紧把昨天的发票拿出来。
“不用给我,直接去财务部报吧,没花超吧?呵呵。”
“没有没有。”
“南风,这几天挺累的吧?注意点身体,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谢谢陈总。”
转身出了总经理办公室,我便径直向财务部走去。昨天一共花了四千七百多,我开了六千的发票。这次我领的限额就是六千,也就是说,除了昨天花的,我还能净赚一千二百多。这事儿别的部的人也经常做,我想老陈肯定知道。我拿下的这两个点最低每个月也能拉进一两百万的保费,相较而言,我多拿的一千多块钱连个屁都不算。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把一个信封偷偷地塞给赵京,里面放了500块钱。
他打开看了一眼,然后小声说:“谢谢南哥。”
“你应得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赵京这几天一直跟着我来回地跑,鞍前马后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是,我是有些贪,可我知道哪些是我应该拿得,哪些是该分出去的。
今天是周五,下个周一正好是业务员进驻的日子,所有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差到时候搬进去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两台电脑了。
仔细地算了一下,我手里已经有十多个点了,每个月的任务,即便是再不景气也能轻松完成的。这就表明即便我下个月什么也不干也能够拿到全额的薪水和奖金。
正美滋滋的时候,突然想起刚刚在办公室的时候陈曦朝我诡异地笑。
也许是我看错了,但我总是觉得他那笑里面似乎蕴含着什么。
我一直不喜欢陈曦,他比我大三岁,身材瘦高,方脸,颧骨很高,眼大无神,两个眼珠子整日在眼眶里面逛来逛去的。他比我进公司晚上很多,但却比我的等级高,赚的也比我多。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的,陈曦上面有人,据说还是总公司里面比较位高权重的。这社会就是这样现实,要么有钱、要么有权、要么有门路。什么?你说你什么都没有,那对不起,无论你有再怎样出色的能力你都要从基层干起。
我烦陈曦绝对不是因为嫉妒他,而是出于对那种虚伪小人从最根本上的厌恶。那混蛋屁本事没有,溜须拍马倒是一等一的好手,背后打小报告也是他的拿手好戏,而且龌龊到经常对手下的女业务员动手动脚。
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突然接到齐朗的短信,约我晚上出去喝酒,说有事要和我说。齐朗这厮经常无缘无故地玩失踪,一消失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去了,打他手机要么关机,要么不在服务区。
我想了想今天晚上好像没事,就说好啊,下班你过来接我吧。
齐朗有自己的车,一辆二手的尼桑,虽然卖相矬了点。
“有半个月没看见你了吧?”我用牙嗑开一瓶啤酒递给他,“又他妈死哪去了?”
“昨天刚从上海那边回来,”齐朗接过去咕咚咕咚地干进去半瓶,然后打了一个很响的嗝,“出去考察点项目。”
“什么项目?”
“我打算开一个公司。”齐朗抓了一把盐爆花生米,一粒粒地往嘴里扔。
“做什么?”
“广告。”
“好啊!正对口。”我嘿嘿地笑。
我和齐朗是同学,一起在西大读了四年的广告学。
“操!不是开玩笑。”齐朗看着我笑,皱了皱眉头,然后把一粒花生米丢到我脸上。
我还是忍不住笑,这厮在此之前曾经干过很多行当,从开音像店一直到卖保健品,也算是老油条了,只是所有行当最后都出现惊人的相似,那就是从来都是稳赔不赚。想当年开音像店那阵子倒确实让我拣了不少便宜,没什么事的时候就跑到他店里看电影,从欧美一直到日韩,阅过的毛片无数,什么小泽圆、武藤兰、高树玛利亚,都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而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这厮的庐山真面目。
记得有一次,他不知道出去干什么去了,我帮他看店,正看一个电影,依稀记得是一恐怖片,刚看到那女鬼出来的时候,就听“哐”的一声,我抬眼一看门被踹开了,进来三个穿着警服的。还没等我说话他们就是一顿乱翻,接着从柜台后面拽出半麻袋毛片来。我当时真的傻眼了,腿肚子都转筋了。
“你是叫齐朗么?”其中一个警察问我。
“不是,”我摇了摇头“我是他同学。”
“齐朗哪去了?”
“我不知道,他刚出去的。”我觉得冷汗从后背涔涔而下,那是我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
“哦!”那警察撇了撇嘴,“那你出去吧!这音像店查封了,涉嫌传播淫秽色情。”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店门贴上封条,心里想这下完了,以后没有毛片看了。
我给齐朗打电话,但是一直不通,只好在店门前等。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齐朗那王八蛋才施施然地走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吃一根冰激凌。
“对不起,齐朗。”我有些愧疚,毕竟是我在帮他看店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事儿。
“操!我当什么事。”齐朗慢吞吞地舔完那根冰棍,把木柄远远地扔出去。走到门前看了看那两张交叉的封条,然后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前后不过15分钟,一辆警车停到音像店门口。还是刚刚那三个警察,一个个陪着笑:“你是齐朗吧!刚刚是误会。”说完一把撕掉贴在门上的封条,接着把刚刚拿走的碟片又都送了回来。
“麻烦你们下次搞清楚点。”齐朗翻了翻白眼,很嚣张地说。
我目瞪口呆,真的,当时只是在心里面一个劲地说:“我靠我靠我靠……”
“你来帮我,咱俩一起干。”
“什么?”我正在走神,没怎么听清他说的话。
“我说咱俩一起做这个广告公司,当初你不是一直想从事广告行业么?
肯定赚钱。”齐朗自信满满地说。
“操!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广告公司这么多,你凭什么说一定能赚钱?”
“我不凭什么,”他看我一眼,笑了笑,“你就说你来不来帮我吧?”
“让我考虑一下。”我觉得齐朗今天有些不一样,似乎是太严肃了一些。在我眼中他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家伙,似乎没什么他在乎的,即便明天是世界末日,他也会欢呼着叫嚣让灾难来得更猛烈些。
“好的,给你时间考虑,”他挑了挑眉头,喝了一口酒,“不过我可告诉你,是非成败在此一举啊!”
“靠,怎么说得跟要造反一样。”
“没什么区别,选我你可能当皇帝,不选,你就一辈子做你的放牛娃。”
我“嗤”地一笑:“造反还有被杀头的可能呢!”
齐朗白了我一眼:“吃饭还可能被噎死,你怎么还吃?”
“行啊!这成语用得不错。”我抚掌赞叹。
齐朗却还是一副白痴样:“什么成语?”
“你刚刚不是说‘因噎废食’吗?”
“孙子儿才说过。”
我顿时无语,这混蛋一向以不学无术为傲。
“对了,你猜我昨天看到谁了?”
我一直想把我在酒吧看到乔羽鸿的事说出来,好像不说出来就憋得难受。这感觉很像穿了一件华美的衣服却在黑夜里行走一样,我有时候甚至会想我他妈的是不是太八卦了。
“谁?”
“乔羽鸿,没想到吧!她在龙门上面的那个慢摇酒吧唱歌。”
“我早知道。”齐朗甚至连眼皮都没抬。
“我知道你什么心思,”齐朗接着说,“你要是想报当年的仇,我劝你还是算了,她现在跟三哥了。”
“三哥是谁?”我有些发懵。
“肖三,龙门的幕后老板就是他,黑白两道通吃。”
“当啷。”我把汤匙掉到了桌面上。
肖三我倒是真的听说过,据说是西兰的黑社会大哥,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他的一些传闻。其中有一条最夸张,说他一个人曾经拎一把砍刀放翻30几个,当时听了第一感觉是震撼,然后就觉得有点太夸大其词了吧!1vs30,只有在电影里面才能看到的。但不管怎样,肖三很牛逼倒是真的。
“怎么了?”齐朗见我一脸痴呆相。
我和他说了我昨天的事情。
齐朗沉吟了一下:“应该没事,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的心刚放下来,他的下一句话又把我搞得心惊肉跳。
“不过你以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你没听说‘最毒不过妇人心’么?谁知道乔羽鸿那女人是不是恨你恨得咬牙切齿呢?”
“我靠!”我发了狠,“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吗要怕她。”
“不只是她,据说白明和肖三也有一腿。”
“真他妈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哈哈,”齐朗突然指着我大笑起来,“我们的南大才子竟然会骂街,真不容易啊!”
“滚!别惹大爷我。”
2008年10月17日20:05,华联商厦顶上的电子钟显示出的时间比我的手机快5分钟。
我和齐朗正从路边的大排档里面出来,一人啃着一根烤玉米。
“去么?”齐朗含糊不清地问我,然后用下巴指向马路对面的一家桌球俱乐部。
“一杆十块?”
“谁怕谁啊!”
去到对面需要经过一座过街天桥,我们走过天桥的时候,齐朗突然在一个算命的摊子前面停下来。
齐朗向我眨了眨眼,小声说:“你不是对《易经》有研究么?看看老头是不是骗子。”
“喂,老头,你这是怎么测的啊?测一次多少钱?”
我头上的冷汗立刻下来了,哪有这么问的啊!而且占卜预测这东西是很玄妙的,一般都讲究心诚则灵,我只是懂一点其中最肤浅的皮毛而已,怎么能看出来人家是不是骗子?
“小伙子是第一次测吧?”那老头子花白头发,看着瘦骨嶙峋的,大黑天的还戴一副墨镜。
“对,”齐朗一边点头,一边把手伸向老头眼前,然后挥了挥。见那老头没什么反应,回头看向我,不出声,只是把嘴开合了几次。我仔细地看了半天才知道他说的是:是个瞎子。
“那你把你的生辰八字说一下,然后在这张纸上写一个字。”老头子说着把一张纸和一支笔放到齐朗面前。
齐朗说了他的出生年月日,然后四外张望一圈,在纸上写下一个“淼”字。
接着老头把墨镜摘下去,仔细地看齐朗写得龙飞凤舞的“淼”字。
齐朗眼睁睁地看着老头瞪着一双眼睛在那儿研究,顿时咬牙切齿起来,在我耳边说道:“操!不是瞎子,这老骗子。”
我早知道老头不是瞎子,因为我看见一份今天的报纸正放在他的右手边,而且还用一只笔在本期彩票中奖号码处仔细地标注了几个数字。
“啧啧,”老头子吧嗒吧嗒嘴摇了摇头,看向齐朗,“你要测什么?”
“啥都行,”齐朗挠了挠头,回头看看我,又转回去,“测测财运吧!”
别看齐朗这小子平时看起来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的,其实我知道他很信命。
“财运不错,从你这个字能看得出你很有门路,水采众长因势象形,是为八方来财之象。”老头一边讲解一边把手指来回地在那个“淼”字上划来划去。
我觉得这老头简直一派胡言,“淼”字有三个水,而水在八卦里面是为坎,为坎为险,一般六十四卦中同坎卦联系起来的都不是很好,比如屯卦和困卦都是和水联系到一起的。再怎么理解也看不出来有财运的象征啊!
“是么?那太好了。”齐朗一听,顿时高兴得喜笑颜开。
我看他那么高兴就没好意思泼他冷水。
“那再帮我看看我的寿命。”齐朗开始得寸进尺。
“这寿运嘛……”老头沉吟了一会儿,仰脸看齐朗,“小伙子,我这可是算一卦给一次钱,你这是第二卦了。”
“够两次的了吧?”齐朗掏出一张50的扔了过去。
老头却慢吞吞地把钱拿到天桥边的灯旁边仔细地查看,甚至还用鼻子闻了闻,研究了半天抬头问齐朗:“不是假的吧?”
齐朗几乎被急死,咬牙切齿:“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哦!我看也不像假的,”老骗子把钱揣进怀里,顿了一顿,“这寿运嘛……你想听好的还是坏的?”老头突然弄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好的怎么讲?坏的又怎么讲?”齐朗把身子蹲了下来。
“好的就是寿元旺盛、长命百岁。”老头眯着眼睛看齐朗。
“那坏的呢?”
“遇水则险,命犯流年。从你的八字上来看你的命格五行属火,而且火性太盛,但你方才写的字又是水性极强。六十四卦之中,水火既济,火水未济,是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前者坎上离下,小利贞,初吉终乱之象,所以说你开始时会一切大顺,但最终会功亏一篑,甚至可能搭上性命。后者离上坎下,未济:亨,小狐讫济,濡其尾,无攸利。意为水中捞月、镜里观花,总归虚无,皆为幻象。”
“南风,你说他算得准么?”我们走在街上,夜已经深了,吹过的风有些冷。齐朗有些落寞,可能真是被刚刚那老头说的吓到了。
“准个屁,你没看他身边的报纸上面写了一堆的彩票号码,要是准的话还能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这儿耗着玩?”
“对!我一早就看出那老东西就是一骗子,没瞎还带个墨镜。”齐朗听我一说立刻高兴起来。
“你刚刚怎么会写那个‘淼’字?”我有些不解。
“那字念‘淼’啊!”
“你不认识?”我惊讶。
“怎么了?我照着那上面写的。”齐朗伸手指向我身后。
我回头,只见一个硕大的广告牌子上面写着“飘淼宫洗浴中心”。仔细地盯着那个闪烁着五颜六色霓虹灯的“淼”字,一瞬间觉得天昏地暗的。我没告诉齐朗,刚刚那老头说的和我想的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