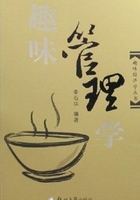二仁和狗儿把我舅和我小姨失踪的前后经过详细向我姥爷作了汇报,并要求我姥爷处治他们。
“我们该死啊,该死啊,老爷交给我们这么点事我们都没办好。”二仁呜呜哭着说。
我姥爷摆摆手说:“别说这些,你们愿意出事吗?这都是天意,天意啊。快起来吧。”接着就让我大姥娘给二仁和狗儿弄饭吃,“不管怎么样,不能饿着肚子。”我姥爷说。
二仁和狗儿感动得再次抽噎不止。
我姥爷说:“这事一定不要传扬出去,传扬出去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改改一个女孩儿家,好说不好听。”
正这么说着,来庆的媳妇闲姐儿从外边一路哭着来了。进门就扯起我大姥娘的胳膊说:“娘啊,怎么俺三兄弟和四妹妹就出事了呢?俺那娘哟,俺以后可上哪去找那体己的人哟——”
我大姥娘一下子甩开儿媳妇,冷冷地说:“你闭上你那臭嘴!谁跟你说的你三兄弟和四妹妹出事了,放屁!”她讨厌闲姐儿要甚于讨厌来庆,所以无论闲姐儿说什么她都不愿听。
我姥爷判断,事情让闲姐儿知道了全村也就没有不知道的了。果然,没过多大工夫,院子外面就聚集了许多人,村里的几个户长就走进院子,打听我舅和我小姨失踪的事。
我姥爷无可奈何,本来已经难以支撑,现在只好做出一副稳若泰山的样子走出去,满面笑容地对众人说:“没什么事啊,大家都放心吧,正是忙的时候,大家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然后让几个户长留下商量寻找我舅和我小姨的事。
户长是洞天村所独有的一种官职,它与后来的保长性质差不多。但最早却是我姥爷的发明。我姥爷之所以发明这种官职,完全是为了便于对村民进行管理。每个户长统管十户人家,我姥爷每年给户长的待遇是减少二成的租子,并在年底的时候组织全体村民进行优等户长评选,当选的户长奖励大洋五块,未当选的户长来年加收一成的租子,连续两年落选者,罢免户长职务。洞天村如今百分之九十的人家都是我姥爷的佃户,他的这一措施为管好村民壮大庄家的势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户长们在我姥爷的堂屋里对我舅和我小姨失踪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大家一致认为,我舅可能还在城里,我小姨可能被土匪绑票了。统一的看法是兵分两路,一路去城里找我舅,一路去石门山一带打听我小姨的下落。
于是吃过晚饭之后,户长们召集了一些青壮年,连夜兵分两路开始了行动。来庆也跟着去了城里。
人走以后,我姥爷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号称半仙之体的浑道士乔言胡。“为什么不找他掐算掐算两个孩子现在何处呢?”就打发人去把乔道士叫来了。
乔道士名言胡,四十二三岁的年纪,十五年前他在莒县天宝村给姓徐的财主做长工,竟与这财主的小老婆勾搭成奸,趁一夜深人静之际私奔到洞天村来了。那时,四门洞北门外玄武庙里的韩道士恰好作古了,这乔言胡无处栖身,就在得到我姥爷的同意后,夫妻俩不伦不类地在庙里做起了尼姑和道士。
但是刚刚作了道士不久,乔言胡就病了,这一病就是两年没起床。那个与他私奔的女人原本在他面前娇若小猫,男人一病她竟变了一个人似的,没钱买药她就上山去采,没饭糊口她就四处讨要。这倒让村里人受了感动,说这女人倒真是有情意的,男人病成这样,说不定哪一天就蹬腿西去了,她非但没有后悔跟了他,还整天乐哈哈地为他讨饭挖药,实在是难得呀。就改了以前对她的鄙视,在她上门要饭时便格外地多给些。我姥爷知道情况后,让人送去了两斗谷子十块银元,后来还亲自上门看望了一次。
这使得乔言胡夫妻感激万分,那女人竟跪下去给我姥爷连磕了好几个头。
乔言胡病到最后的阶段,人几乎就没指望了,他不吃不喝有十几天,只一丝丝的气呼进呼出。女人就为他张罗后事,用从武财主家偷来的布为他做了寿衣寿鞋,连送葬的白幡都扯好了。
但是十几天过后,乔言胡突然又好人一样了,他睁开眼气喘吁吁看着女人说:“哎哟俺娘哎,好远的路啊!”
女人惊喜万分,抱住他好一顿痛哭。然后就问:“你上哪了?直喊路远。”
乔言胡说:“我到四川峨眉山去了,是一位蛇仙把我请去的,她收我做了徒弟,教会了我前算五百年后算五百年的本领。”
女人说:“你甭胡说了,我不信。”
乔言胡说:“信不信由你吧。眼下你娘家出了一桩子事,不出三个时辰就有人来叫你了,你快准备准备去吧。”
女人说:“你又在胡说了不是,因为我跟你私奔,我娘家都不认我了,就是有事能来叫我?我不信。”
乔言胡说:“肯定来叫你,因为你爷要死了,临死之前他想见见你,你说能不来叫你吗?”
女人仍是将信将疑。
但是到了下晌,她娘家果然来人了,说她老父已经上了灵床,非想见见女儿,他们是来请她的。
女人回头看看床上的男人,一下子心服口服了。
说来也怪,乔言胡原本大字不识几个,自此以后竟懂得了阴阳八卦那一套,凭着掐捏手指的各个关节,就能算出人的生死祸福悲欢离合。一时间他的名声被人广为传扬,就有许多人前来找他,或问前程,或求婚姻,或寻失物,或解灾祸。乔言胡再也不用让女人四处讨饭了,前来求他的人所带的钱物不仅让他夫妻二人有了饭吃,还可以每天晚上炒上俩菜对饮几盅。
我姥爷从没找乔言胡掐算过。他的神通再大也在我姥爷的掌握之下,他脚下站着的是我姥爷的土地,我姥爷的一句话就可决定他的命运,怎么会轻易找他掐算呢。乔言胡自然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当叫他的人说是我姥爷请他时,他表现得极为惊讶又高兴。他女人则对他说:“庄老爷这么看得起你,你可一定得尽心尽力给他掐算好啊。”
乔言胡坐下来,喝过两杯茶后开始掐算我舅和我小姨失踪后所在的方向。他说:“少爷丢于申时,四小姐也丢于申时,看来他们是同在西南了,是让歹人暗算了呀,性命倒是没事,但主破大财。”
我姥爷说:“他俩都在西南方向吗?”
乔言胡说:“一点没差。只要你们说的时辰对,人肯定在西南。”
我姥爷说:“要是叫土匪给绑票了的话,那可真就破大财了。”
乔言胡说:“恐怕是。我再掐算掐算,看有没有贵人相助。”说完低下头又掐起了指头。半天,显出惊喜之色,说,“好,好啊!有贵人相助,有贵人相助啊。只是这个贵人身处何方没有找出来,不过天意注定有贵人,不知何处也自来啊。”
乔言胡告辞而去,我姥爷亲自把他送出大门口。乔言胡几次回身恭手请我姥爷留步,我姥爷停下步子请他走,乔言胡却又站下了,他低声说:
“今晚亥时您一定注意,有动静。”
我姥爷略一吃惊:“有动静?”
乔言胡说:“我掐算着有人送东西来。”
我姥爷说:“好,我一定注意!”
这一晚,我姥爷和我大姥娘没有睡觉,他们等待着亥时的到来。但是亥时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实在太漫长了,他们喝着茶,感觉今晚比平时任何一个晚上都难熬。就开始议论着我舅和我小姨平日里的许多事情,说着他俩如果真是叫土匪绑票了的话,估计会要多少钱,还说到了我小姨的婆家,说改改被绑票的事如果传到他们的耳朵里,这桩亲事怕是要出麻烦了。
“出麻烦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丢人啊。”我姥爷说,“只这一件事,我这大半辈子的脸面就全丢光了。”
如此一说,一股难解的愁绪就沉沉地压向了我姥爷和我大姥娘。二人唉声叹气。
但最终还是我大姥娘劝解我姥爷,说你也不用过于发愁,改改的婆家离咱这里那么远,一时半会儿上哪知道啊,等成亲以后知道了,咱也有话说:怎么着,谁家愿意出这样的事啊,出了这样的事俺那闺女就不是原来的闺女了?
我姥爷说:“话是这么说,就怕改改……”
我姥爷没有把话说完,但我大姥娘一听就明白了。实际上她也正在为此担心着,女人最重要的是贞节,如果坏了贞节,什么都完了。可她同样也不愿把话说出来,仿佛一说出来就成事实了。
二人一时无话,屋子里静得让人紧张。
我大姥娘要扶我姥爷到床上去躺一躺,我姥爷说:“咱就这么坐着吧,这么多年了,像这么面对面单独坐上大半夜的时候还真是没有呢。”我大姥娘点点头,心里生出了对我姥爷的几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