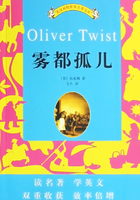我舅庄来福在往沈阳给我写信之前,我并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从民国初年走过来的舅舅,所以刚刚接到信的时候,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这个在信封上标明“老舅庄来福亲笔”的人到底是谁。看了信才知道,他原来是我一位远方哥哥的舅舅。说是我舅也没错。
我舅庄来福给我写信的目的是想让我帮他完成一个心愿。他说他已经九十五岁了,近来忽然预感到没有几天活头了,但有一个多年的心愿未了,那就是请人帮忙把他及其家族的传奇故事写成一本书。他说以前他之所以没有让自己的心愿变成现实,一是因为自己是地主出身,长时间受到“专政”根本不敢乱说乱动;二是觉得那些事涉及的人很多,虽然他们大多不在人世了,但其后代都在,有的还都混成了人物,他怕说了以后会招来官司;三是有些事是属于家丑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家丑,他怕自己还健在的时候说出来有辱先人不说,自己也不好在村里做人。现在所剩时间不多了,一切也就无所谓了,反正自己没有亲生儿女,两个老伴也都早早地离他而去了,只要自己闭了眼睛埋进土里,就算天塌下来也与他无关了,所以,他才决定赶紧行动,千万不能延误了时机让那些精彩绝伦的故事随他进了棺材。偶然知道了我是写书的,便从我那位远房哥那里要了我的地址给我写信,想求我帮他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吐为快。至于意义,他说能让后人娱乐娱乐,或让后人了解一下过去的历史,也就足够了。其他的他没想太多。我一看非常高兴,因为平时想找一个愿意讲述真实经历的人采访采访特别难,现在送上门来了,自己绝对不能错过。所以当即跟领导请了假,坐上火车回了老家沂水。
当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沂水西南部一个叫洞天的村子,正准备打听庄来福住在哪儿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了虽不洪亮却也听得清楚的喊声:“你是大外甥吧?一看你穿着军装我就猜出来了。老舅在这儿等你好几天了!”我巡着声音找去,只见村头的一棵古老的柿子树下站着一位拄拐棍的老人,他有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骨瘦如柴,面皮松皱,残发枯乱,眼窝深陷,整个人犹如被风干了一般。猛然一看,以为见到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具木乃伊。一阵恐惧当即袭上心头,心想,这就是那位给我写信的舅舅庄来福吗?想象中他应该是矮墩墩胖乎乎又慈眉善目的(因为我太太爷爷是地主,就长得矮墩墩胖乎乎又慈眉善目的),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既然都成这个样了,他还记得多少过去的事情,又能讲得清多少过去的事情呢?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说起话来也咬字清楚,无半句含混。对于早年间那些事情,他连具体细节都能讲得出来。而且他的心境也达到了超然物外的境地,对于他和几个女人的风流韵事,对于他们庄家的发家史,以及我老姥娘和一个和尚的私情,我姥爷和我大姥娘、和长工老马媳妇、和固家女儿的故事,他都不作半点隐瞒和修饰,照实讲来,不亢不卑,无讳无避,淡然如水,而且从不拖泥带水、丢东忘西,还像说书似的,颇有几分艺术性,着实令我刮目又感叹。
“民国十五年七月十六,我和你小姨去沂水城赶大集,叫人家给绑了票。绑票的是谁呢?开始以为是土匪,后来才知道不是,是石门村的老刘家。老刘家为什么要绑我们的票呢?是因为我们家有一块风水宝地他们想霸占。可老刘家怎么会知道我们家有一块风水宝地呢?是有一个姓柳的老头和老刘家有仇,为了报复老刘家施的借刀杀人计!”
说完这段开场白。他“滋”地一声喝下了一盅我带回来的沈阳老龙口酒,又接着说第二段开场白:
“我们老庄家在民国十五年以前,那是非常兴旺啊,土地除在本村有几百亩外,在外村、外乡、外县还有很多。各种买卖铺子也有好几家,牛羊二百多头,打杂的、跑外的、放牧种菜的长工三十多个,佃户就不说了。可是自从我和你小姨被绑了票以后,我们老庄家就完了,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只一年多的工夫,我们家就死掉了六口人。后来你姥爷跟我闲谈时有个结论,说:‘出了那么多事儿死了那么多人,不光是因为小人暗算,还因为你个小兔崽子生性好色,搞了不该搞的女人,埋下了祸根啊!’我当时不敢顶撞他,心里说,你也别说我,你要不和你嫂子(就是我娘)胡搞有了我,我连世界都不见,我搞谁去?你要不和长工老马的媳妇胡搞得罪了老马的儿子大马,大马能把农民暴动‘暴’到咱家来?你要是不娶老固家的小闺女,让她夺了我娘的管家大权,咱家能争来斗去的乱成一锅粥?咱爷俩啊,是半斤八两,席上地上,背着抱着一样沉,谁也别说谁,谁也难辞其咎!”
又是一盅酒下肚之后,我舅的讲述开始进入正题。他先从跟我小姨去赶沂水集被人绑票开始讲起,中间有插叙,有倒叙,一直讲到我姥爷在“土改”中被枪毙,他在“文革”中被批斗,两个老婆——喜哥和靠儿——让红卫兵逼得先后上吊自杀为止。
三天时间,我和我舅没有离开过只剩两间破房子的庄家大院。
我因为年轻,没感觉怎样。但是我舅庄来福却累得不得了。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人也似乎更瘦了。
不过我舅很高兴,是“一吐为快”后的那种高兴。他拉着我的手说:
“我终于了确一桩心愿了。你回去以后根据舅舅讲的慢慢弄去吧,估计舅舅是等不到书出来了。不过不要紧,只要在书出来以后,你到我坟上烧一本就行了。”
我说:“舅舅你别这么说,你没事的,一定会活到一百多岁的。一定能看到书出版的。”
他摇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我连你写的手稿怕也看不到了。”说完这话他让我扶他上床躺下,然后很满足的样子闭上了眼睛。
我以为他困了,就悄悄退出屋子,去洞天村周围及位于村子东头的四门洞里看了看。
回到庄家大院时,天快黑了,我想看看他醒没醒,然后叫个三轮车和他一起去乡驻地的饭店里请他吃个饭。同时跟他谈谈这本书的创作想法,告诉他“土改”和“文革”部分可能不往书里写了,这两段与前面的联系不大,可以另外成书。可我拉开电灯走到床前,喊了好几声舅舅他都没有反应,仔细看看时,他的脸已经变得惨白,用手一摸凉如冰人,再试鼻息,连一丝呼吸都没有了。
我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