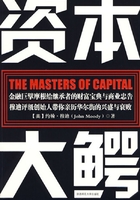五月的秦淮河岸,火红的石榴花开得灿烂明艳,碧绿的艾叶长得葱郁茂盛。文人学士考试的贡院,与对岸楼台林立的妓院仅有一江之隔,这是明代南京城特有的风景。
端午节这天,秦淮河岸上异常热闹。赛龙舟、挂灯笼,一时间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到处都是欢歌笑语。贡院里的书生们也被这节日气氛感染了,暂时把烦恼抛在九霄云外,出来寻欢作乐。
夜幕低垂时分,陈定生和吴应箕一起来到秦淮河边观赏节日盛会,以排解漂泊异乡的忧愁。可是走了半天,也没见着一个熟人。
陈定生心中纳闷,问道:“在这样的节日里,为何连一个同社的朋友也没碰到啊?”
吴应箕答道:“想必他们都在灯船上游玩呢。”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水榭说道:“这是丁继之的处所,咱们正好可以在此登临远眺。”
两人边说边来到了水榭前,问道:“丁先生在家吗?”
仆人出来迎见,说道:“原来是陈相公和吴相公啊,我家主人去参加灯船会了。不过家中已经备好了酒席,主人临走时吩咐,凡是有客人来,尽可以随便进来坐一坐的。”
陈定生笑道:“你家先生可真有趣儿。”
吴应箕也随声附和道:“可见主人是个十分好客之人。”
说罢,两人便移步至水榭内。陈定生提议:“咱们在这里雅聚,为了避免打扰,得想个办法拒绝闲杂人等入内。”吴应箕点头称是。
于是,陈定生便吩咐仆人取个灯笼过来,提笔在上面写道:“复社会文,闲人免进。”
吴应箕道:“若是同社的朋友到了此处,该请他们一起入会赏玩。”
“正是这样打算的。”陈定生笑着说道。
仆人对他俩说道:“公子,你们听——远处有吹弹之声响起,灯船朝这边驶过来了。”
陈、吴两位顺着仆人手指的方向,果然看到了一艘灯火通明的船儿向这边驶来了。陈定生定睛一看,发现这船上坐的不是别人,原来是侯方域偕同新婚夫人李香君,相依相偎;旁边坐着柳敬亭、苏昆生,两人在吹拉弹唱,别有一番情致。
陈定生道:“那灯船上,好像是侯方域啊?”
吴应箕道:“侯方域是我们复社一员,应该请他入会的。”
“他旁边的那个女子想必就是李香君了,也要邀请她吗?”
“李香君拒绝接受阮大铖的妆奁,早已在南京传开。她如此大义凛然,也应该算是我们复社的朋友,应该请她入会的。”
“如此说来,那船上的柳敬亭和苏昆生也是复社的朋友了,他们当日也坚决不肯做阮大铖的门客呢。把他们一起请到这里来,肯定会更加有趣。”
两人商定后,吴应箕便向灯船高声呼喊侯方域的名字。侯方域听到声音,抬头向水榭上望,见是陈、吴两位,心中十分惊喜。于是,就接受了邀请,偕同船上另外几位一起来到水榭上。
互相拜见后,陈定生笑道:“你们四位来了,这个才算不虚有此名。”
侯方域心中不解,问道:“为何是‘复社文会’呢?”
吴应箕指着门口的灯笼笑着说道:“请看那里。”
“原本不曾知道今日要会文,看来我来得正是时候。”侯方域笑道。
“‘闲人免进’,我们未免唐突冒犯了。”柳敬亭说道。
“你们都不肯做阮大铖的门客,怎么不是复社的朋友啊?”吴应箕连忙解释。
“难道香君也是复社的朋友吗?”侯方域接着问道。
吴应箕答道:“香君拒绝妆奁这件事,只怕我们复社人还比她略逊一筹呢。”
陈定生调侃道:“以后咱们得改口称香君为‘社嫂’了。”
香君莞尔一笑,说道:“不敢当!”
大家依次坐定。仆人拿来酒盏,供他们玩乐。他们随意谈笑,气氛十分温暖融洽。这时,河岸上的船只多了起来,张灯结彩,富丽堂皇。多数都是王公贵族、巨商富豪或是翰林学士们的游船。相比之下,侯方域一行所乘的游船就显得寒酸简陋了许多。
“夜阑人静,灯船都散去了,我们作篇诗赋吧,也算是不辜负‘会文’之约。”侯方域说道。
“好是好,只是不知道以什么为题目啊?”陈定生接言。
“端午节是祭奠屈原的日子,咱们就做首‘哀湘赋’,以示纪念吧!”吴应箕应道。
“依我看,咱们几个人不如就根据眼前的风景作诗,每人吟成一联,最后联成一首诗。”侯方域建议说。
陈定生和吴应箕都表示赞成,并推举由稍年长的陈定生来开头。这时,柳敬亭笑道:“三位相公作诗,我们三个在一旁陪着打盹吗?”
“是啊,我们也得找点乐子吧。”苏昆生开口说。
“不用急,自有任务分派给你们。”陈定生又接着说道,“我们每联成四句,各自饮酒一杯,你们就负责唱个曲助兴。”
“有趣,有趣!这样一来,我们就是诗文、美酒、笙歌样样俱全了。”侯方域拍手叫好。
大家兴致都很高,不知不觉,便联成了十六句诗,还开玩笑说明天要拿去刻印出来。吴应箕感慨到:“我们作诗引出许多感触,他们吹弹也奏出无限凄凉,这其中的滋味,恐怕是其他人不能体会到的。”
苏昆生向柳敬亭说道:“自古良辰美景亦逝,花好月圆难逢。我们要趁着这好光景,及时行乐啊。如不这样,我俩负责唱曲,陈、吴两位公子负责劝酒,让眼前这对才子佳人再尽一尽兴。”
“这个没问题,唱曲本来就是我们分内的职责。”柳敬亭爽快地答应了。
“我与吴兄本是东道主,也正想向这一对新婚燕尔表示下敬意。
刚好得了这样一个机会,一定得尽心尽力。”陈定生笑着说道。
吴应箕赶忙指挥大家按次序坐下。侯方域和李香君坐在酒席的最上面,陈定生、吴应箕坐在左边,柳敬亭、苏昆生坐在右边。
侯方域温存地对香君说道:“今天承蒙各位的好意,我们两个并排而坐,又可以吃一回交杯酒了,这可真是有趣啊。”
香君莞尔一笑,心中也十分满意。大家各司其职,奏乐、劝酒,一时间又热闹起来。
忽然,杂役前来报告:“前面又有一只灯船驶过来了。”
陈定生惊诧地问:“三更半夜了,怎么还有灯船啊?”
这时,大家也纷纷起身,走到栏杆处眺望。
苏昆生道:“大家仔细听,这船上音乐旖旎靡丽,想必是在寻欢作乐吧。”
原来这船上坐的是阮大铖。他原本打算早早地出来游乐赏玩,但是又担心碰见复社的那一拨年轻人,让他受辱难堪。所以苦苦熬到了半夜,才敢抛头露面。他看见丁家的水榭上还亮着灯火,就吩咐小厮去打探一下,看看上面究竟是什么人。
小厮领命,登岸看清楚后回来禀告:“老爷,那门口挂一灯笼,上面写着‘复社会文,闲人免进’。”
阮大铖惊叫道:“不得了,不得了!快快熄了灯火,停止奏乐,咱们速速离去。”说完,就命人驾着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楼上的人还在眺望,见这条船刹那间变得漆黑一片,鸦雀无声,刚来没多久就匆匆离开,更觉它形迹可疑。
“这真是件怪事,赶紧派人去看个究竟。”吴应箕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不必了,我虽然老眼昏花,不过还是看真切了,那船上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臭名昭著的阮胡子。”柳敬亭讲道。
“怪不得呢,我说这船上的音乐怎么与别家不同,原来是他呀。”苏昆生接言道。
陈定生一听说是阮大铖,便怒气冲天,骂道:“好大胆的狗奴才,这贡院之前,岂是他能来游玩的地方?”
“让我追过去,扯掉他的胡子。”吴应箕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正要转身下楼。
侯方域拦住他,说道:“算了,算了!他既然已经躲避开了,我们也不要得寸进尺,再为难他了。”
“侯兄,不是我们得寸进尺,而是他太过分了。”陈定生没好气地讲道。
柳敬亭过来劝解:“船都远去了,咱们也不要再追了。”
“只是便宜了这阮胡子。”吴应箕忿忿不平地说道。
香君也觉得这件事情不可闹得太过分,就和颜悦色地说道:“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散了吧,我家中还有妈妈在等候呢。”
大家便依言互相告辞了。陈、吴两位留在丁家,准备借宿一晚。
侯方域、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便一同下了楼,登上来时的小船。
这时湖面平静,阒然无声,只有他们的小船载着美人向烟花深处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