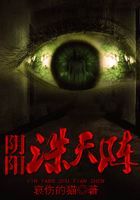洛夫
夕阳无限好,好就是好,没有什么“只是近黄昏”的。黄昏固然可视为一种终结或死灭的暗喻,但也预示了另一个新的开始。
入夏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到这阳台上来过,似乎过了几个世代,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栏杆旁多了几盆花,除了那株正在做开花准备的圣诞红外,其余都叫不出名字。当然兰花我是认识的,但兰花品种繁多,总不能看见凡是像韭菜样的东西都叫兰花吧。这里唯一熟识的就是那温温软软的夕阳,仍像去年那么亲切,其温度恰到好处,如果在寒冬,真可以捧起来洗一把热水脸。说它温软亲切吧,它又偏偏锋利得如一把刀子,从隔壁楼顶水塔旁斜伸了过来,正好把我那靠近墙边的投影从中切成两半。偶然侧脸一望。吓了一大跳,这人居然只有半个影子!
不知为什么突然生出这种感觉,久未登楼,一登楼便把自己弄得如此惊疑不安,像在草丛中踩了一条蛇。
这些都不必去说它。
有一点想必你是同意的,我们的岁月消逝虽快,但毕竟美好过,那长长的夏日,璀璨而明亮,接起来就是一串闪烁发光的珍珠项链,所有的生命都丰盈甜美得像一只水蜜桃。每一朵花都恋爱过,每棵树都怀过孕,每条河都唱过歌,每片云都在天空写过诗。都市烟尘滚滚,雨过,也睛过。许多窗口摆着各色各样的盆景,到了晚上就换成各色各样的灯火,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生命在忙碌中充实、成长,随时都有奇迹在我们附近发生。大地是如此慷慨,西瓜之后是荔枝,荔枝之后是芒果,芒果之后是柳丁,力量是如此丰沛;篮球之后是棒球,棒球之后是足球,足球之后是省运。吸进去的是甜甜的果汁,流出来的是成成的汗水;稻谷多得没有地方堆,烟囱里飘出成群的蝴蝶;一夜之间便有一株树从平地升起:昨天这里还是一片荒烟蔓草,今天就出现了挖土机、打桩机,以及把天空分割成一小块—小块的钢管鹰架,等你环岛旅行一趟回来,矗立在你面前的已是一座吞吐千人的大厦。喏!顺着我的手指瞧,就在那大厦的背后,落日正在西沉,多么动人的景色。夕阳无限好,好就是好。纵然黑夜接踵而至,众人仍忍不住驻足仰视,希望它在明天更加辉煌。
现在,我正靠着栏杆在看落日。“独自莫凭栏”,与其说这是一句词,毋宁说是一声叹息,一句警语。记得有一次,在一座尚未完工的12层大厦楼顶的栏杆旁,就曾看到一块用红色油漆写着这5个字的警告牌。这位建筑商竟是一位雅人,比起那位一天到晚不停地播送那首《总有一天等到你》的流行歌曲的棺材店老板风趣而厚道多了。(你一向反对文学的实用价值,这句李后主的词今天不是已派上用场了吗?)但对我这种既不轻易感伤而性格又已定型的中年人来说,靠着栏杆反而能产生安全感,可以静静地瞧着一群灰鸽挨着头顶飞过而不会为之心惊,可以嘲弄地唱着:流水落花秋去也,天上人间!
我今天才知道,独自凭栏看夕阳是一项多么富于知性的经验,绝不浪漫。夕阳无限好,好就是好,没有什么“只是近黄昏”的。黄昏固然可视为一种终结或死灭的暗喻,但也预示了另一个新的开始。我很欣赏李商隐这两句五绝,但听多了那些悲伤意味过浓的诠释,便直皱眉头。
作者简介
洛夫,1928年出生于衡阳市衡南县相市乡,世界华语诗坛泰斗,台湾著名的现代诗人。出版诗集《时间之伤》
和《灵河》(1957)、《石室之死亡》(1965)、《因为风的缘故》(1988)、《月光房子》(1990)、《漂木》
(2001)等三十一部,散文集《落叶在火中沉思》等六部,评论集《诗人之镜》等五部,译著《雨果传》等八部。
【心香一瓣】
诗歌被誉为文学闺秀、文学精灵等,这是因为它们往往只用寥寥数字便传达出无穷意境。好诗歌,就如冰天雪地里的数点梅花,散发着傲人的芬芳。
诗言志。每首诗,都在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的心情。同样的风景,不同人有不同的心境,写出来的诗便大不一样。
夕阳无限好,悲观忧伤的人叹道“只是近黄昏”,乐观向上的人看到的却是新希望的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