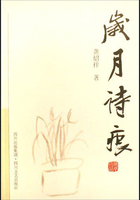当年掀起过一股美学热,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高尔泰先生。他是美学家,也是艺术家,20世纪90年代初寄居美国。这几年,他跟中国最密切的联系是出版了回忆录《寻找家园》。书中牵涉到一些现实人物的故事,曾引起轰动。抛开争论不谈,以书论书,这是一本很坦诚的书。身为画家,他的文笔竟如此了得,写景写人栩栩如生,别具画家之眼。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尔泰在苏州一所艺校学画。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开放,自由散漫惯了的他渐渐感到身边有些人不太对劲。比如一个女同学叫唐素琴,对他表达过爱慕之情,但他实在没办法接受。因为,她是个“正确得可怕”的人。唐素琴最感兴趣的是数学,从小学到中学,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她本想工作两年后考清华理工科,但组织根据需要安排她学美术,她就高高兴兴地来了。她说,祖国的需要就是前途。
1955年“肃反”运动时,一些本来很要好的同学突然跟高尔泰翻脸。在一次会议上,他的信件被同学拿来质问。他嘟囔着说,脑子里想什么是他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这时唐素琴发言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很奇怪,当时的会议气氛很恶劣,但会后同学们又跟没事人一样,恢复了昔日的友好。
1957年,唐素琴当上模范教师,常常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依旧正确得可怕。但是这么正确的人,因为家人有国民党背景,到了“反右”的时候也不行了。那段时间,传闻她差点自杀。她跟高尔泰恢复联系后,高尔泰发现她整个人走了样,过去长得挺好看,现在被岁月和斗争磨蚀得非常糟糕。
二十多年后,总算太平日子来了。高尔泰到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带着妻女去唐素琴家做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当上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过去那种龌龊境况全然不见。她的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现象,母子俩争论起来,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她依旧正确得可怕。
高尔泰最悲惨的一段生活是在酒泉夹边沟农场度过的。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他在那个劳教农场待过一年。他说,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有些东西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进门时就被没收了。没被没收的东西,对于持有者来说,生前是个累赘,死后成为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夹边沟是个盐碱地,什么作物都种不好,大家一天到晚饿得要死,都很憔悴、褴褛和衰老。不管你是老中青,不管你什么背景,过了一段日子,大家的样子都很像。有一个叫龙庆忠的人,永远穿着一件蓝皮袄。他把衣服照顾得很好,蓝皮袄始终保持着初来时的光鲜,于是老被批评说影响劳动,但他坚持不改。他是独子,自幼丧父,母亲千辛万苦把他养大,却因农村户口而不能陪他住在城里。“反右”运动中单位“右派”名额凑不够,硬把他划成“右派”。蓝皮袄是母亲在他出门前做的,他天天穿着,弄得干干净净,这样才对得住母亲。
高尔泰深受感动。后来,他有一段时间没能跟龙庆忠见面,但劳动时远远看见过那件蓝皮袄。有一天晚上,他到医务室换纱布,黑暗中穿过球场,看见“蓝皮袄”在前面走,便马上追过去。他一看,竟是另一个人。那人告诉他,龙庆忠已经死了,后来穿这件衣服的人也都死了,衣服传到他手里时已几易其主。
高尔泰离开夹边沟后,到他向往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刚到那里,他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天,一位所里资格很老的画家在资料室门口看见他,非常热情地打招呼,然后急速忙乱地掏钥匙开门。老画家跟他说,因为××原因迟到了,还伸出手表让他看时间。从无时间观念的他没细听也不想看,只是傻乎乎笑着示好。但是老画家固执地要他看表:“你看,不到五分钟,是吧!”他连说“是是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又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位女同事。她一手抱着一摞书,一手拖着一根枯树枝。寒暄之后,她说这根树枝已经枯了,是风吹下来的,她是顺便拾的。其实,这不用说,一看就知道。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解释。后来他才发现,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研究所的人都彼此监视,上班迟到或者走路手里拿根树枝,都可能让人觉得不对劲。
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不能不提常书鸿[7]先生。他为敦煌的保护与研究下了大力气,做了很多实在事,也帮了不少人。可是他挨批斗时,打他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他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高尔泰回忆道:“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他个儿高,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反右”运动中,有一张大字报无中生有,说高尔泰半夜说梦话,大喊“杀杀杀”。当时他在一所中学教书,写大字报的人是一位地理老师,平常沉默寡言,和他无冤无仇。多年后,他故地重游,人事景物全非,唯一的旧相识,就是造谣批斗他的地理老师。“他已很衰老,白发稀疏,腿脚也不大灵便。见到我他非常高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坚持要我到三楼他的宿舍里喝一盅。显然,又见友人,他有一份深深的感动。二十一年过去,兰州市容变化很大。但皋兰山和黄河都还是老样子,从楼窗外望出去,沉沉晚烟凝紫,风景略似当年。老人说起往事,神色有些黯然。那年老婆子饿死后,儿子去’引洮上山‘,也死了。退休下来没处去,只好赖在学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默默地对饮。”
1958年,高尔泰的父亲在毒日头下背着灼热、沉重的砖头赶路,从跳板上跌下来死了,时年五十八岁。父亲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来。母亲和二姐收尸时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批斗,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多年后,他回高淳看望姐姐。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姐姐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说,那是1958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他们父亲的凶手。那个老人“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檐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我对这个人几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同时,我也就更远地飘离了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厚土”。
这是否表示高尔泰能够原谅过去,开始宽容了?他说:“有人说我出国前后,文风判若两人,从激烈到平淡,表明叛逆者经由漂泊,学会了宽容与妥协。这是误解。宽容、妥协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辈,一无所有,不是可以学得来的。是在无穷的漂泊中所体验到的无穷尽的无力感、疏离感,或者说异乡人感(也都和混沌无序有关),让我涤除了许多历史的亢奋,学会了比较冷静地观看和书写。”
隔远之后,冷静会带给你不同的视角,让你想起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你在其他生命眼中是什么样子。高尔泰说,当年他们在荒漠上追赶一只被捕猎夹夹断了右腿的羊。羊逃跑时,毛血模糊的后腿、臀部和下腹部在沙石上拖着摩擦,那条断了的腿在地上拖得稀烂,但羊没有停下来。“这个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对任何其他动物都毫无恶意、毫无危害的动物,唯一的自卫能力就是逃跑。但现在它跑不掉了。爬到一个石级跟前,上不去,停了下来。突然前肢弯曲,跪地跌倒,怎么也起不来了。”羊抬头望着他,他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他能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
当年在敦煌,高尔泰写了一些东西:“写人的价值,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透过书写,他才能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他写作时非常紧张,总要把房门闩住,门外一有声音就会吃一惊,猛回头,一阵心跳。那些文章在“文革”中全部失去,且大都成了他的罪证。他说:“但我无悔,因为写作它们,我已经生活过了。”
(主讲梁文道)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中国变革镜像
何伟(Peter Hessler,1969-),美国作家,曾任《纽约客》驻京记者,多次获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1994年首次到中国旅行,前后在华旅居十余年。著有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
信仰在个人层面一派萧条,宗教组织相当弱势,而警察和官员也同样罕见,只在有机会捞一把的时候适当出现。
很多书名噪一时,书评都说好看,也非常畅销,但你看完会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美国作家何伟的这本《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却会让你觉得好像很多赞誉还不足以说出其独特之处和真正价值。比起之前的《江城》《甲骨文》,这本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这是一本现代中国作家写不出来的书,并不单单因为作者是美国人,采用外国人视角看中国——当然这个元素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如果像何伟一样深入地在中国民间待上一段时间再去描写,大部分中国人会有包袱。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没有很鲜明的主题,由三篇长文构成:第一篇是何伟沿着长城在华北、西北一带开车漫游的经历;第二篇是他在北京近郊怀柔渤海镇三岔村居住了几年,跟村民打成一片的经历;第三篇是他跑到浙江丽水市,记录了那个地方从山地变成新兴工业市镇的变化过程。书中涉及的主题,如中国的农村状况、荒凉的西北地区、工业城镇发展等,很多中国作家、记者、学者也会去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会有包袱。我们在中国生长,熟悉这里的文化、背景、历史、生活习惯和社会运作原理,已经有了很多自己的判断。我们总希望用看到的东西来佐证早就有的判断,写作时总有得出某种判断的倾向和冲动。
何伟不一样,他是外国人,描写所看、所感时,不那么急躁地下判断。他不是没有判断,只不过对他来说,判断不是最重要的。他跟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那么关心中国应该怎么样、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中国该往何处去。他不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忧国忧民,因为这不是他的国,也不是他的民。这不是说他对中国没有感情,恰恰相反,他对中国非常有感情,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句话有时候像笑话,可是你真的看完此书,会得出这个结论。他能够尊重笔下那些中国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对他们有一种同情。
何伟谈到中国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比如医疗问题。住在三岔村时,有个他看着长大的小孩得了一场病,他非常担心,带着孩子去北京不同医院看病。他的外国人身份,有时让他得到医院比较殷勤的照顾,有时则相反,因为医生觉得这个外国人是不是想来挑战他们的专业知识。在求医的过程中,他看到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医院对乡下人的野蛮无理,对生命状况的不闻不问,还有粗暴、官僚等问题,这让他很愤怒。但他对中国朋友的感情大于对这种体制的愤怒。
在谈及一些我们看来牵涉制度问题的话题时,何伟并不太在意问题有多坏。比如他看到一些工人应聘时不断抱怨制作人造皮革的化学物质有毒,想争取更高的工资,却遭到人力资源经理毫不留情的反驳,说如果你不想在毒烟中工作,去当老师好了。这位经理吐出来的每一个字几乎都会得罪人,但工人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应。这种应聘方式跟美国完全不同,中国工人绝对不会谈什么“成为团队的一分子”“成长的机会”“有高度积极性和创意的人才”,而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人力资源经理的评价则尖锐得近乎残忍,“人力资源”更接近其字面意思,工人只是“资源”而已。对于中国人面对种种限制和困难仍努力迎上去的勇气和毅力,何伟表示尊敬。他以一种比我们更包容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同胞。
其实,何伟笔下能够大做文章去批判中国怪现状的地方非常多。比如他参观所谓的成吉思汗陵墓——那个墓当然是假的,成吉思汗哪有什么墓留下来。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女导游,两人聊到了希特勒。他问,你觉得希特勒是好人还是坏人?女孩说,我认为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在历史上留名。这个女孩所表达的感觉和情绪,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对此,我们忍不住要发一番议论去批判和剖析,但何伟只是很平静地写出来而已。
何伟还写到一个调配染料颜色的工人小龙。小龙和许多城镇工人一样,是励志文学的主要消费者。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叫《方与圆》,是一本阐明在现代社会如何处世的畅销书。书名来自“内方外圆”的古语,作者将其运用到城市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教大家如何通过说谎得到好处,如何操纵同事,如何声泪俱下又不过火地在上级面前哭诉,如何做一名后共和主义时代的马基雅维利[8]。看这些东西我们会觉得很灰暗,会批评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和价值虚无问题,但何伟没有。他唯一有点价值评判的话是说,《方与圆》这本书“得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何伟发现,中国人在回应快速变化的社会时选择并不多。像丽水一家工厂里的陶氏姐妹,我们可以用最经典的异化理论来谈论她们的工作状况,那就是把自己完全掏空,只是手部在工作,大脑一片空白。这就是中国“世界工厂”背后的真相。对此,何伟并没有批评太多,只是描述这些中国人并没有太多选择,好像只能顺从而已。他说:“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转变的反应。这不是现代化的问题,至少并不全然是。我从来都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为什么人们急于逃离贫困,并且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和改变怀有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