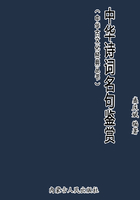阿马蒂亚·森这本书是对自由主义身份观念的一次雄辩。近二十年来自由主义常常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最早来自于一种政治哲学即社群主义。社群主义者认为一个人的身份不可能是社会真空的,它有一些既定的条件和文化背景,限制了他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所以一个人身份并不是由他来选择的,而是要他去发现的。阿马蒂亚·森认为这种想法具有严重局限,因为所谓身份的意义其实来自于选择,而选择要看不同的处境。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任何一个国际机场的洗手间都是按照男女分的,不是按照黄种人、白种人跟黑人来区分的,也不会分成中国人使用还是外国人使用。因为在上厕所的时候,你是一个穆斯林还是一个佛教徒,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是爸爸还是孩子,是个中产阶级还是贫民,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同处境,常常使我们必须在那个特定的处境下应用一个我们觉得最恰当的身份。但阿马蒂亚·森认为,恰恰是这样的思想盲点阻隔了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的沟通与理解。
诚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会受制于某种文化身份,但是太过强调这种身份,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忘记理性的重要。一旦踏上理性之路,你就不可能再坚持始终用一个中国人的方法来思考问题。比如近几年一些人对民主价值提出批判,认为是西方世界强加给各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阿马蒂亚·森举例说,全世界自古以来到处都有不同的民主元素,比如曼德拉[5]曾在自传中写到,少年时代他在家乡看到的地方会议程序是最纯正的民主,无论是酋长还是平民、武士还是医生、店主还是农夫、地主还是劳工,每个想要发言的人都发了言,发言者的身份也许存在等级差异,但他们每个人的话都被认真聆听了。
阿马蒂亚·森说,曼德拉对民主的追求并非来自西方社会的任何强加,毫无疑问,他对民主的追求是源于他自己的家乡非洲,不过他的确反过来把它强加给了当时统治南非黑人的那些欧洲人--不是欧洲人把民主强加给本地人,而恰恰是本地人把自己的民主观念强加给了欧洲人。
这本书也涉及今日世界各地因宗教引起的冲突,比如从恐怖分子的圣战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文化,而伊斯兰文化内部也存在多种差异,有些穆斯林在历史上是非常宽容的,但是今天出现了极端的基本教义派,该如何解释呢?依据伊斯兰教义,哪一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呢?其实,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而是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
要了解一个穆斯林,不能从单一角度下定论。几个穆斯林对政治事务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但他们可能都是好的穆斯林,都有正确的伊斯兰信仰。对于政治问题看法的差异,跟他是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或好的穆斯林没有多大关系,很可能是别的政治文化观念影响了他的判断。
我们不能够期盼一种文化或宗教观念能够决定我们对所有事情的看法,这只会把人囚禁在一个狭小的牢笼里。常常有人说,中国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必听从别人的意见。这种说法本身,也是一种牢笼或命运的幻象。
阿马蒂亚·森说,过去很多反对英国殖民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也常常说西方优于我们的无非就是物质、经济、政治,但是我们的精神文明远远超过他们。他认为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一种殖民遗产,就因为太把西方殖民者当成一个对象了,才会这样强调彼此的差异,强调自己的某种精神力量。
试想,这只是印度特色吗?我们和其他亚洲国家是否也如此?[6]
(主讲梁文道)
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
拆解中国左派精神
河清,原名黄河清,当过下乡知青,1987年赴法,获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左派首先要具备的素养是要永远保持一种批判精神。左派在英文中另有一个表达:Progress,是进步的意思。左翼人士常常被认为是进步分子,因为他们总是对当下的社会状况提出质疑并想要改变它。
《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的作者河清留法十年,对西方社会相当了解。这本书编入了他翻译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7]的一些文章。他一方面站稳左派立场,狠批当代的全球化倾向[8];另一方面又回过头来捍卫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
河清提出的很多观点我都赞同。比如他说西方媒体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带有很多歪曲和偏见,这些并不直接受国家和政府控制,而是被很多商业财团操控。我以前也提到过,目前约有五大财团垄断了全世界几乎一半的报纸、电视、电台、出版社、电影公司和唱片公司。试想如果这些集团想达到某些目的,宣扬一些政治主张,它们有没有能力利用旗下的媒体去造势?或者反过来威胁国家和政府呢?这是完全可能的。
有钱有势的商人甚至可以通过媒体影响政府,让政府实施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政策或路线。就这一点而言,作者认为西方媒体其实很不客观。接下来,他批判了最近几年的全球化现象,基本上沿用了布尔迪厄的思路。
布尔迪厄是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他的批判十分尖锐,不仅批新自由主义,甚至也狠批法国的所谓国家精神。连传统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文化精神在布尔迪厄看来也不过是一种伪装。他认为像我们这些自称是文化人的,只不过是垄断或占有一些文化资本并以此来为自己取得了一定社会地位而已。
河清认为,今天的中国不应该盲目地跟随西方搞什么市场开放,市场开放、经济改革甚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都是很危险的行为,中国应首先找回文化的主体性。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没有独立精神了,我们的表层政治、经济理论、文化概念的合法性和价值基础都来自于西方,甚至连纪元都在用西方的。他为我们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时间而感到悲哀。
他还认为媒体不应该过度渲染情人节、圣诞节,而应强化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更不宜宣传年夜饭去饭馆吃。上海亚太经合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上唐装亮相,马上在全国带起一股民族服装的风尚,这样的做法才是好的。
但令人惊讶的是,作者一贯的左翼批判视角,对国家文化及本民族传统这些东西却没有进行任何分析。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是怎样构成的?河清所推崇的布尔迪厄这些西方左派大思想家,常常会批判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或精神价值观,因为很多情况下那都是国家机器、统治阶级或部分精英制造出来的控制民众的工具。但是作者面对中国类似的问题时,却好像遮起了半边眼,视而不见了。
(主讲梁文道)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Global Era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克里斯托弗·休斯(ChristopherR.Hughes),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国际关系问题。
前几年反日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很多外国记者看到有那么多市民百姓上街抗议日本,都觉得很惊讶。他们心想,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各地的经贸往来如此密切,改革开放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怎么还可能会有这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呢?这种惊讶背后其实隐含了一种假设,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下,一个国家的全球化程度越高,民族主义的情绪会越淡薄。
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近乎于一种封闭、落后、保守的意识形态,跟面向国际、面向世界、开放门户的风格是彼此不相容的。但现实并不如此,《ChineseNationalismintheGlobalEra》(《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专门谈这个问题。
作者休斯是有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资深讲师。在过去十年中,他出了很多文章和书籍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这方面的专家。他的这本书,书名点出了两个要点:一是中国民族主义,二是全球化时代。这两样东西休斯认为不仅不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的,而且必须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它。
他首先谈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认为其根源可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时候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像张之洞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中国要向世界各国学习,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跟他们往来,但是骨子里头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是不能变的。
休斯认为,这也是今天中国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下的某种态度:我们可以跟大家做生意,可以跟大家保持经济上的往来,但是中国的主权思想、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不可动摇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尊严是必须牢牢捍卫的。
与此同时,休斯指出,民族主义也是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老百姓为什么愿意被一个政府统治?他们一定要认同政府,觉得你可以统治我们,我们听你的,这叫合法性。其中一个合法性的理由是,我们认为政府带领我们走向了民族独立自主,维护了我们的民族尊严。所以民族主义向来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脊梁。
民族主义的脊梁遇到了现代开放的世界,该怎么办?休斯认为,邓小平的民族主义理论就是我们一方面对外开放,讲究和平崛起,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开放并不影响我们民族的独立自尊,而是反过来助长了我们的民族尊严,让我们更加肯定自己,回到世界舞台。
休斯在谈论“民族主义”时,并没有尝试为它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他把民族主义看成是复杂的、可以操作的,每一个人都尝试用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大家说出话可能并不一样。就官方而言,像办奥运会这类活动,原本是世界主义的、不分国家的,但是由我们来办了之后,反倒能让世界看到今天的中国人是何等开放、自豪。
休斯还有一点观察我觉得很有趣,他说当我们把爱国主义跟民族主义完全统一、结合起来的时候,也会面临一些困难和矛盾。比如办奥运的时候,我们既要打开国门欢迎全世界的人,又要维护国家的荣耀与骄傲,要去反驳别人对我们的种种攻击和扭曲,这中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恐怕是当前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主讲梁文道)
别对我撒谎
撼动世界的记者
约翰·皮尔格(JohnPilger),优秀的战地记者、作家与制片人,两度获颁英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年度记者”(JournalistoftheYear)。
想要写好一份调查报道,通常需要记者具备几种素质:一是专业能力,文笔需有相当功力;二要足够敏感,能够从一些细节推敲出整个事实全局的拼图;三还要有勇于挑战主流认知,挑战社会共同的成见;最后,你还要有耐心。
怎样才算有耐心呢?《别对我撒谎》[9]提到一位2004年去世的、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记者。他用了十二年时间去调查一起“空难”事件的真相,最后揭露出英美两国的秘密阴谋,非常震撼。花十二年写一篇报道,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有的记者做到一定程度,也许会被认为“不爱国”,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年的红主播爱德华·默罗[10]。他在麦卡锡大搞“白色恐怖”时,勇敢地在新闻节目中揭露“麦卡锡主义”的虚伪面目和他那种混淆是非的逻辑观念,最终把这个因“反共”而臭名卓著的国会议员推倒。
当时麦卡锡在国会主持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11],致力于找出美国社会各界的“共产党”,说这些人不爱国,想颠覆美国,所以都是非美分子。默罗在任何人都怕被扣帽子的恐怖氛围中站了出来,批判麦卡锡对言论自由、个人自由的压制。按当年的说法,默罗就是一个标准的“非美分子”。但时至今日,我们又对他如何评价?
书中还收录了以色列女记者阿米拉·哈斯(AmiraHass)的报道《全面封锁》。阿米拉·哈斯长期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占领区做采访,巴勒斯坦人居住区被互相隔离、分别包围在以色列国土之中。也就是说,如果想从巴勒斯坦的A处到B处,必须穿过以色列的国土,经过很多的检查站,而以色列士兵一定会想办法为难你。
难到什么程度?一位巴勒斯坦老太太在耶路撒冷病重,希望她的家人能来看她,可是孩子们都住在加沙走廊,折腾了一个礼拜才能过来,来了几个小时又要立刻赶回去。后来她死了,把她的尸体运到加沙埋葬又折腾了一礼拜,整个过程饱受以色列官僚主义的压迫。她的这些报道完全站在同情巴勒斯坦的立场上去写,所以很多以色列“右翼”分子威胁说要伤害她的性命,认为她太“不爱国”了,你明明是以色列人,怎么反过来帮着巴勒斯坦人说话呢?
说到“不爱国”的罪名,不能不提到2006年10月7日在莫斯科寓所被枪击身亡的俄罗斯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12]。当年普京总统对传媒控制得非常紧,安娜却是敢于挑战当局的记者中最勇敢的一位。她大量报道了车臣战况,描述车臣老百姓怎样被俄军屠杀。她的《车臣不义之战》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事件。
1999年11月16日,一个叫爱思雅的女子准备把丈夫的遗体运回家乡,入土为安,同行的还有几个孩子及两位长辈,总共开了两辆车。他们在经过一个俄军哨所时被拦了下来,俄军官兵二话不说就开枪扫射。爱思雅哭喊着说:“看在真主的份上救救我们!”那些军人却说:“根本没什么‘真主’,你们这些车臣混蛋!去死吧!”车上的老人和孩子全部身亡,两辆车也被炸毁。第二天,俄罗斯的官方媒体报道:“我军勇敢地消灭了两车‘恐怖分子’。”安娜质疑当局:“你们这样对待车臣老百姓,叫他们怎么去爱戴你们?怎么融入俄罗斯?”然而最后,安娜自己也死了。
(主讲梁文道)
法槌十七声
西方名案沉思录
萧瀚(1969-),本名叶菁,北京大学民商法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近年来,在历次公共事件如孙志刚案、SARS事件、黄静案、佘祥林案中发表时评,引人注目。
1875年,美国人雷诺德被法院判决犯有重婚罪。他已经结过一次婚,居然又结了一次,理由是他是一个摩门教徒,根据摩门教教义,一个人是可以有几个太太的,但美国法律又明确规定不能重婚。这件案子在当时的美国引起轩然大波[13],很多人包括陪审团都在争论:“人到底能不能重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