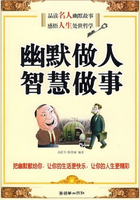四月,巴黎的天气温和宜人。回来小半年,心情已沉淀,仿佛有种寂灭后的泥洹之感。母亲那边最后也没有去成,因为离开时的自己太糟糕,而且,她可能也并不想见到我,因为我从小到如今的不争气。所以我只简单地打了一通电话告诉她我不去上海直接飞法国了,母亲的回复没有令我意外,她说路上注意安全。
以前我总是努力着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现在我不求闻达,不求多少人喜欢我,不求多少人维护我,我只求自己心安。
周六的清晨,我背着绘画工具去一处景色优美的近郊写生,那里有一座教堂,是早期哥特式风格的,周末的时候会有不少人来祷告。教堂附近有一所年代久远颇具名声的小学,学校的老师时不时会带学生出来做课外活动,有一次有孩子跑过来看我在画什么,看了一眼就失望地说:“你画得不好看。”我笑了笑,我又重新开始画画,用左手画,从零起步。
今天天气很不错,现在还太早,中午的时候应该会有不少人来这边的草地上野餐和享受阳光。
我找好景后,架好画板,拿出画笔和颜料,开始慢慢描绘起这金红朝阳下的波光丽景。
我起初来法国,学了一年语言后就开始进修绘画,因为我从六岁开始画画,有基础,自己也喜欢,但大二那年右手不能用后,不得不转去传媒专业,学影视广告。于是我在法国的一年半绘画学业作废,从头念起,因为影视广告跟绘画同属艺术系,跨度不是很大,所以这次转专业除去对不能再画画有遗憾,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困难。其实起初那几年,最大的难题是我自身的状态。
下午回宿舍,远远看到马丹太太朝我招手,干枯的头发在风中飞扬,蜡黄的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马丹太太等我走过去,就笑眯眯地跟我说:“Anastasia,亲爱的,有人来找你,是跟你一样的东方人,长得很漂亮,他等了你一上午,现在还在,就在宿舍后方,你快去找他吧。”
在这里我并没有相熟的东方人,就算有也都只是点头之交,没有熟到会上来找的。
“谢谢您,马丹太太。”我朝宿舍后方走去,心中猜测着究竟会是谁。
当我看到站在草坪上、背靠着一棵法国梧桐树在玩手机的叶蔺时,有些惊讶,他一身白色干净的便装,略长的头发已削短,看上去精神许多。
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他也抬起了头。
“什么时候来法国的?”我走近他率先开口,连自己都没想到竟然可以做到如此平静,也许是真的什么都放下了的缘故。
“昨天。”
“哦,来玩吗?”我本来想他来法国可能是来参加什么时装活动,但想起来巴黎时装周3月份就已经结束。
叶蔺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又淡淡地开口:“有空吗?陪我吃顿饭?”
“好。”我说,“不过我得先把东西放下。”我指了指身后背着的东西。
“我等你。”
我笑着点了点头。
回到宿舍,我的室友正抱着吉他在调音,她是新加坡华人,中文名叫梁艾文,我们基本都用中文交流。
“Anastasia,早上有人找过你,他等了你一上午。”
“嗯。”
我放下东西,去卫生间洗手,出来后又听到她问:“你见到他了?”
“嗯。”
“我以为他走了呢,说实在的,他长得可真帅,是你亲人吗?”
“不是。”
“男朋友?”
我对这种试探并不是很喜欢,但还是可有可无地答了:“不是。”
“Anastasia,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梁艾文放下吉他跑到我面前,样子很兴奋,“既然不是你的男朋友,那么我去追求也OK吧?”
我不禁好笑,倒也挺实际地提醒她:“他可能马上就会回中国。”
“距离不是问题。”梁艾文摆摆手,一副无关紧要的模样。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不像开玩笑,不过——“我不知道他的号码。”
梁艾文看了我一眼,有点不高兴了,走开时喃喃自语道:“哎,穿着黑色西装的王子啊……”
黑色西装?
我不解,叶蔺穿的是白色的,哪来的黑色西装?我摇了摇头,否定内心的某种猜想。
跟叶蔺的晚餐,我带他去了离大学不远的一家意大利餐厅。
“这家的菜还不错。”我说。
“你常来?”
我笑了,“怎么可能,这里消费挺高的。我是以前在这儿打过工。”
叶蔺望着我,表情一直有点深沉。
“这段时间比较忙,否则我会带你去逛一下巴黎的。”我实话实说,我在重新学绘画,加之马上要毕业,我的毕业作品还需要修改,我还想在毕业前出去旅游一次,地点已经选好了,是一座古老的城镇。
“我要结婚了。”
我微愣,“嗯。那恭喜你。”
“简安桀,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你的这句恭喜。”叶蔺冷声说着,眼里有一股倔强。
“但是,叶蔺,我能给的就只有这句恭喜了。”
他忽然一手按住了额头,笑了起来,“你是真的不在意我了。”他看着我道,“你不用怕我还会疯疯癫癫地缠着你,我愿赌服输!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以前我想来找你,但是来不了,现在我有能力来了,却已经没用了。你说这人生是不是特幽默?我父母,酒鬼赌鬼,我妹妹,以前我跟你说过几次吧,比我小七岁,很乖,很懂事,但从小到大都在看病,那年你来跟我说你要出国了,我就想,出国要多少钱?五十万?一百万?而那时我身上连五十块都没有,还欠着人家好几万。”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我还没无能到跟女朋友哭穷。”他拉住经过的服务员,“给我一瓶酒,我今天很开心,我要庆祝,因为这是我跟我爱的人首次一起坐在你们法国吃饭。”他说的是中文,我不得不帮他跟服务员说对不起。
叶蔺不松手,“给我一瓶酒听不懂吗?”
我起身走到他身边,“行了,你别闹了。”
“我没闹啊,我就想要喝酒庆祝,这都不行吗?”
我迫不得已只好跟服务员要了酒,最后看着他一杯杯地喝,等他喝去半瓶红酒后我制止他道:“可以了。”
叶蔺靠在桌面上,“我很难受,安桀,我很难受……我现在有种感觉,你长大了,我却依然停留在十几岁,你走之前的那时候……”他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之后许久没有动静,像睡着了一样。我忍不住伸手去抚摸他的额角。
我们就这样从中午坐到了晚上,他偶尔说几句话,都好像只是在说给曾经年少的我听。
他说:“安桀,我们去操场上走走吧。”
他说:“安桀,老师来了你叫醒我。”
……
我最纯粹的那几年是与他度过的,我没有后悔过。只是他跟我都明白,我们终究是在时间的长河里错失了彼此,即便当初我们都背负着不得已的苦衷。
我在服务员的帮助下将他弄进了出租车里,好在他身上有酒店的房卡,我把人弄到了目的地,离开叶蔺那边已经快凌晨。
回到学校宿舍,在一楼的大厅里,我看到有人站在那里。
法国现在这么受欢迎吗?谁都跑来了!还是深更半夜。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是他的话,我也不奇怪。
“回来了?”他说,语气沉稳。
我直接走过大厅往楼梯口走去,完全地漠视他。
我不想见到他,我甚至连想都不愿去想他。他是我那些不堪记忆的一部分,我每一次的狼狈离开他都见证了。
“你到底要任性到什么时候?”身后传来的声音是平静的。
什么叫作任性,不想再理睬叫作任性,那么他跑来这里的行为又叫作什么?看笑话还是落井下石?
“为什么你每次都只会落荒而逃?”
即使自己再怎么不想去在意,他的这句话还是成功触痛了我,他很了解怎么样让我难受。
我转过身望着他,“席郗辰,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一向不在意他,却常常被他的态度搅得必须要去正视他,“人要懂得适可而止,我已经不再打扰你们,所以麻烦你也别再来打搅我!”
等我合上宿舍的门,我长长呼出一口气。
我简单洗漱了下就上了床,黑暗中听到梁艾文开口道:“聊聊?”她没等我回答就开了灯,翻身坐起,弄出很大的动静,“下午我又看到他了。”
这时我才真正确定,她口中的他是指谁。
“我跟他说了会儿话,哎,他真冷淡。但看他的举手投足,还有穿衣,应该地位不差,他好像还擦了点香水,但我分辨不清是什么牌子的。”她的口气越说越兴奋,“上午我在楼下遇到他,住在这幢宿舍里的华人就我们俩,我就知道这人可能是找你的,因为,你知道,你长得还算可以。我就上去问他,是不是找Anastasia简,还真的是。我就跟他说你一早就出去了,他说没关系,之后就坐在楼下的椅子上等,本来我以为这人一定很爱慕你呢。但傍晚的时候,我再见到他,马丹太太在跟他说,你跟别的男孩子走了,他也没说什么,所以我想你们之间应该没什么。哦,他在法国这边是不是有公司?我听到他打电话说中午开会提到的事宜要如何之类的。Anastasia,你有在听吗?我跟你讲了那么多,你是不是也应该跟我说一点你知道的?”
“我对他不了解。”
“叫什么,事业如何,总知道吧?”
“不清楚。”
“Anastasia,你真没意思!”她说完关了灯,倒头就睡。
我在黑暗中努力清空自己的脑子想要快点入睡,可过了大概半小时依然毫无睡意。我打开床头的台灯打算看点书。我拿过抽屉上放着的法语词典,书已经翻烂了,想起刚来这边的那两年,走在路上、去食堂吃饭都是在恍恍惚惚背单词。
“喂,你开灯我怎么睡觉?”
我看了她一眼,她一直在玩手机,“等你睡的时候我会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