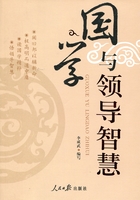1966年,有人抱着试试的态度,根据已经认出的那些玛雅文字,试译了奎瑞瓜山顶上的一块玛雅石碑,没想到,译出来却是一部编年史。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据透露,编年史中记载发生在9000万面前,甚至40000万年前的事情。可是在40000万年,地球上根本没有人类的痕迹,这真的不可思议。难怪那些来到玛雅的欧洲宗教狂人认为玛雅文明是“魔鬼干的活儿”了。
克诺罗索夫、伯林和普罗斯科里娅科夫的研究使玛雅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从那时起,80/100的玛雅象形文字得到了解读,新一代考古学家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潜心进行了新的发掘和探索。世人对玛雅文明的认识也渐渐明了起来,其神秘色彩慢慢隐退。
文化的珍品——纸与书
玛雅和中国一样,也拥有自己的纸和书。但是,它的纸与书与中国纸张和书有很大的不同。玛雅人的纸张是又厚又硬的硬纸板,而中国的纸张是比较薄的,也比较软,便于书写和装订。玛雅的纸是一种很精致的工艺品。据说它是用当地的一种无花果树的树心嫩皮制成的。玛雅人先把树皮捣成纸浆,然后从另一种树上取得汁液相互融合,这种纸浆要经过压平,晒干等程序,才会成为硬纸板。这种硬纸板有点像现在包装纸盒的硬纸。在这种又厚又硬的纸板上要涂抹一层又细又白的石灰,且把石灰面擦拭得平滑而光亮。就这样纸张制成了。那么纸张怎么装订成书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十几页甚至上百页的硬纸板折叠成册,就成了人们现在所说的书了。由于这种硬纸板比较厚重,所以一般装订时页数不能太厚。
在玛雅古典时期,这种纸张和图书就已经很流行了。它的发明时间与中国纸张出现的时候差不多。其他迹象表明,玛雅人在当时使用纸张非常普遍,不仅仅写书、写文件、进行学术研究用它,连写信也用它。但是由于纸张非常昂贵,写书、写信往往成为国王宫廷、神庙祭司、贵族阶级和专门学者的“特权”。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古典期的玛雅图书都完全损毁,再也找不到踪迹。现在我们从考古发掘中只是偶尔可以找到一本书的残页或几页纸板。但是已经模糊得看不清楚。其次。玛雅的热带雨林气候也不便于保存纸张,并且对纸板表面的石灰层腐蚀性很大。
西班牙传教士兰达曾在《尤卡坦记事》中谈过这样一件事情,他曾在尤卡坦的一个玛雅小镇里发现了一个地窖,里面放着30本书,这些书全部是用黑色和红色墨水书写的,涂满着各种符号。纸张的制作材料是无花果和蚕树皮。为了使其表面光滑还特意涂抹了一层石膏粉。为了保护书籍,特意在外面包了一层豹子皮。但不幸的是,这些书籍被征服者认为“魔鬼的谎言与迷信”,没有一丝的留恋,就被搜出来统统烧毁了。尤卡坦的一位西班牙主教甚至在他的著作中公开宣称,经他手烧掉的玛雅图书所写的都是“魔鬼的谎言与迷信”,所以他把这些图书全部烧毁了,他为此而沾沾自喜。这位主教的愚昧,只是当时西班牙殖民者毁坏玛雅文明的一个典型。有些西方学者直到今天还不胜感慨地说:“西班牙烧毁的成百上千的玛雅图书,哪怕其中一两部甚至半部能遗留下来,对于玛雅研究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万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玛雅书籍全部被焚烧,有三部书籍侥幸地逃离了这场劫难。它们很有可能是在焚书之前被当作战利品运往了欧洲。后来这三本书分别被英国的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法国的巴黎图书馆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国立图书馆收藏,它们的名字也随之以收藏地命名,分别命名为“德累斯顿抄本”、“巴黎抄本”、和“马德里抄本”。“德累斯顿抄本”长达3.5米,一共有39页;“巴黎抄本”是这三个抄本中最“袖珍”的,仅长仅1.45米;“马德里抄本”是这三个抄本中最长的,长达6.7米。三个抄本中都有大量的象形文字,这也为学者们破解玛雅文字、研究玛雅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石柱上的秘密
在玛雅人生活过的地方,经常可以看到大小不同、高矮不一的巨型石柱。这些石柱雕刻着精美的图案,不失宏伟庄严,但又神秘莫测。这些石柱的数量非常多,规模也很大。但摆放的位置很特别,这不得不让人费解:玛雅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造这么多根石柱?它们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些玛雅纪年石柱绝大多数建立在一块长方形的巨石上,其上部往往雕刻成椭圆的形状,在一面的正中间,雕刻人物,围绕人物的周围往往是一些铭文。至今为止发现的这类石碑和石柱已经有了数百块。1959年,在玛雅古典时期的中心——蒂卡尔发现了一块最早的纪年柱。这块碑高80厘米,正面刻着一位年轻的王子。
那么,纪年柱的用途有什么呢?通过研究知道,玛雅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每隔一定的年限,大约是二十年,玛雅人就要在他们所居住的城镇里建立一块石碑或者一根石柱,把发生的事情刻在上面,作为记录,这就是闻名世界的玛雅纪年石柱。因为这些纪年柱的材料非常坚固结实,易于保存,所以成为研究玛雅文化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正在在这些石柱的帮助下,玛雅文化才成为美洲古代历史上一个唯一有年代可考的文化。
但是,最初人们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这些石柱和石碑是玛雅人的一种崇拜,即对时间的崇拜。玛雅人有非常复杂的纪年系统。从玛雅人使用的历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些纪年柱和纪年碑上面有很多符号,被人误认为是玛雅人想通过时间来传达对宗教的一种敬仰。
但是后来随着对玛雅文字的破译,人们才发现这些石柱和石碑并不仅仅包含这些含义。
20世纪30年代,一位叫塔蒂安娜·普罗斯科里娅科夫的学者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图书馆抄写玛雅纪年碑的铭文中,忽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一个纪年碑都包含一定的时间跨度,而时间跨度都在60、70年左右。这是怎么回事?为此,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每一个纪年碑的跨度就是一个人的寿命。从这一点可以推出,每一个玛雅纪年碑都包含一位国王的生平,都是在阐述一段历史。这一理论虽然在当时被提出来了,但并没有对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的玛雅学的权威们还沉浸在“时间崇拜”的理论里,他们都认为纪年碑上雕刻的是宗教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
到了60年代,随着对玛雅城邦的考察越来越详细,人们在玛雅的城邦遗址里发现了一些贵族的墓葬。这时,人们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玛雅社会世俗力量的强大。此时人们对玛雅文字的破译也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人们可以读懂一部分玛雅雕刻了。这样,人们终于对玛雅纪年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时间崇拜”论也不攻自破了。
玛雅人的这些纪年碑和纪年柱,让我们了解到很多玛雅城邦详细的发展史。但是这种发现只是沧海中的一粟。有些纪年的建筑,比如著名的科潘“象形文字梯道”,上面的文字顺序已经打乱,要想整理清楚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我们坚信:玛雅历史终有一天会尘埃落定。
铭文中的故事
玛雅古典文明必不可少的是塔庙、广场和纪念柱。
纪年碑的刻制,一如它的金字塔的建造那样,集中了玛雅文明的人力、物力、智慧与技艺。玛雅人不管是出于对城邦发展的关注还是喜欢天文历法,树立纪年碑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经常性的,逢一定年月就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修建。在玛雅城邦,就会看见一些较大的城邦纪年碑,不计其数。它们一般都高达2、3米,重达10余吨。最高大的可高达10余米,重达100余吨。它的雕制,从开采石料,运到现场到雕刻象形,撰写铭文,可以说集中了当时最高水平。只要看到一个个美不胜收的纪年碑竖立在广场中间或者金字塔之前,就会被它独有的魅力所吸引而注目观看。尤其是,纪年碑上的象形文字,更是它的精华中的精华。
玛雅象形文字的发展水平与中国的汉字很相似,只是符号的组合与汉字相比有些复杂,块体不像汉字那样要求方正而是接近圆形或者椭圆形。为了方便书写,排列的非常整齐且被化成方块,方块中各符号又以椭圆为主。但字符的线条与汉字又不一样,笔画不是规整笔直,而是随图像起伏变化。由于这些特点,使得刚开始看玛雅文字的人觉得非常奇怪,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它是很漂亮的艺术品,很多玛雅艺术家为之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玛雅象形文字来自奥尔梅克的文字。奥尔梅克文化确立的象形笔法与方圆结合的块体,以及圆点和直线组成的数字写法,是玛雅象形文字赖以发展的基础。不过,玛雅人在此基础上继承、发展,并超越了自己的前辈。在前古典期的玛雅纪年碑和其他文物上,可以看出象形文字的铭刻和书写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字体逐渐趋向于规范、完整和美丽,字符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到古典初期的时候,文字符号逐渐增加,达到一百多种,此时的纪年碑铭文非常常见,除此之外,庙宇和坟墓的墙壁上也有了这样的铭文。
在蒂卡尔发现了最早的一座纪念碑,即公元292年的。这时的蒂卡尔也开始建立“美洲虎之爪王”的王朝了。这座纪年碑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在其正面还可以看到刻有国王面容和大量的云雷纹、涡卷纹和玉佩羽毛服饰组成的图像的一部分,背面则有一长串标志玛雅历法年代的数字和相应的象形文字,字体也很美观。到玛雅古典期的繁盛阶段,玛雅文字便完全成熟,它的字符总数在800以上,组成的文字则数以千计,最长的铭文也可包括几千个象形文字符号,著名的“象形文字梯道”便有2500多个文字符号。这时的玛雅象形文字不仅有生动鲜明的图形,也有简化的图案,它们已经起着标音示意的作用,在功能方面也和中国的汉字接近了。但与汉字的一字一音、一字一义很不同的是,玛雅文字的每个单体字往往包括好几个符号,读起来有如短语甚至是一个较长的小句,所以“蒂卡尔”一词也可以读作”蒂卡尔王朝”或“蒂卡尔国王的后代”,它的含义必须和上下文相配合才能求得理解。
很遗憾的是,科潘的象形文字梯道,整体被弄得面目全非。现在看到的只是乱石一堆。19世纪末,美国人初次整理科潘遗址时,曾把这个梯道上的部分石块运走而收藏于哈佛大学的博物馆里,一直到现在,对科潘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学者们注意力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象形文字梯道,而且陆续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就。有人甚至希望借助现代最先进的计算机来协助梯道全部铭文的复原排列、修补或最后的释读工作。人们期待有一天玛雅象形文字最后水落石出。
结合玛雅已经有了纸张和抄写成书的事实,以及玉器、陶器和日常用品中都普遍有文字书写的情况,可知它已经成为玛雅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也正是因为它的复杂与广泛应用使其成为玛雅文化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这也是玛雅文明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