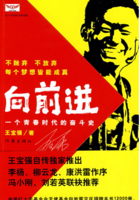莫言的意义当然远远不止于军旅文学的范围,他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坛的。他的集子《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等在法国、西德等西方国家的译介和在港台地区的出版,以及电影《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金熊”大奖等,都说明这位作家已经开始了与世界的对话。
1985年,当莫言以反映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爆炸》等批量作品震动中国文坛时,也给军队文坛造成了不小的骚乱。当大家纷纷对他说长论短却又还没弄清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猜测他可能要给军旅文学带来这个或那个时,他又突然闯入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五老峰”,劈荆斩棘,令人瞠目地种下了一片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开辟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第三条战线”,领导了历史战争题材创作的新潮流。
是有点儿怪,一个抗日战争结束10年后出生的,肯定只在小说《苦菜花》、《烈火金刚》中嗅到过一点硝烟味儿,只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中听到过假日本喊几句“八格亚鲁”的青年人,居然洋洋洒洒神神道道地写出了一大堆关于土匪打鬼子的故事,而且写得是那样的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有死有生、有恨有爱,让年青人看了不得不信以为真,让老年人看了点头说本来如此。当然,这部分地要归结于莫言的文学天才:奇异超人的艺术感觉、颠三倒四的叙述结构、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以及披头散发的语言文体,等等。但在我看来,《红高粱》的成功,还得益于两条。一是莫言对抗日战争独到的认识—“我认为抗日战争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战争。……不仅仅是人力和物力的较量,也不仅仅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而是两种文化的交锋,两种精神力量的抗衡。这样的战争就不仅仅是物质的毁灭,而是精神的毁灭与复苏”。二是莫言对战争文学的深刻理解—“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它不应该停留在对英雄主义和伟大牺牲精神的表面化的歌颂上,还应该考虑战争中人的地位,战争把人变成了什么?……战争文学不去写人,连史料都不如。战争文学应该写出人类感情怎么偏离轨道并力图矫正,它应该成为一种训诫,一种警喻”(莫言:《战争文学随想》,《电影文学》1987年10月)。二者合一,才保证了莫言站在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三个层面上综合地把握战争,并始终把人置于中心加以观照,通过野性的呼喊召唤民族精神的复归,为今天民族品格的重造提供一种比照。也只有这样,莫言的文学天才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如鱼得水地赤足行走在故乡的黑土地上和墨水河边,剪辑那一组组古老神秘的风土地貌与民俗社情的镜头,构就成他“心中的”奇诡灿烂的战争画卷。
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观念和抬升战争文学中人的地位,表明了莫言、黎汝清新老两代作家无独有偶的在战争文学构想方面的某些逼近与认同。然而,莫言的战争和黎汝清的战争又迥然有异。黎汝清的战争以史实为依据,在史实的框架里展开想象。莫言的战争是想象的(或曰“心中的”)战争,在想象的构建中填充现实(包括他的人生经验及文化积累,如民间传说、风土人情等)。他们各自发扬优长,又因了文学观念的更新,两条道路都通向了成功。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的观念与实践,不仅仅对于历史战争题材创作,而且对整个军旅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悠远的启示价值。
关于莫言,我有一种预感,就是在今后的文学“马拉松”中,将阻碍莫言跑得更远的可能是他先定的农民局限性—我以前跟他谈时称作“中农意识”—他晚些时候的《欢乐》、《红蝗》等作品流露出来的某些农民式的狭仄意气和激愤情绪,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忧虑。不过,莫言是个智慧的人,清醒的人,他不会对此没有警觉的,果然这样就好了,他就会不断地搞出新道道,就像在“五老峰”上种“高粱”一样,不定什么时候,他又会让你大吃一惊。
对此我深信不疑。
(原载《长河》1988年1月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