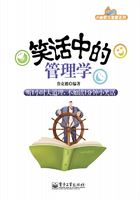单小双说,在城市,她唯一感到有意义的事儿是去那些绿地上尿尿。每当面对一丛花或一蓬草蹲下身子,肌肤与花叶亲密接触,一边嗅着植物的芬芳,一边滋出涓涓细流,她都会在尿与泥土作用出的一种氤氲而迷蒙的气息里闭上眼,陶醉,忘情,投入,俨然到了草木环绕的乡下,到了城市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才叫尿以致用,她跟我说,不仅节约了半盆乃至一盆冲尿的水,还变废为宝,减少了污染,直接把尿尿到了该尿的地方。日久天长,单小双满怀柔情地回望她润泽过的那些花啊草的,果真比别处的花草长势喜人,明显一派葱郁妖娆。目光及此,单小双难得一笑的脸上会浮出调皮而会心的笑意,甚至会滋生些许成就感,仿佛给城市做了多大的贡献。
你看到了吧,单小双比比画画又指指点点地说,在这儿,在那儿,还有那儿和那儿,我都什么过。
单小双这么给我说的时候,是在她的车上。我觉得她明显夸张了,一只耳朵里听一只耳朵里冒,并不全信。正是夕阳西下时分,火一样的霞光洒满车窗,洒在她红得发紫的头发上。我骨子里是个审美细胞匮乏的人,不以跟不上时尚的节奏为耻,动辄还爱吹毛求疵。对于满大街招摇来去的黄头发红头发绿头发紫头发,我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和抵触情绪,甚至有些许绝望。我们生活的这个叫濮阳的城市,经济还不够发达,但是车已经够多,动不动就堵,尤以早晚上下班时为最。单小双一边随波逐流地开着车,一边示意我向外边看。顺着她的手指望去,我看到连片的草坪和行道树,但看不出哪一片更好。它们站立在街道两侧,每每被我路过,又每每被我忽略。我不知这些司空见惯的植被会和单小双有关,也不知我哪一次路过的时候,她正蹲在其间卖力地尿尿。想到这儿我笑了,还没进一步想她的臀上腿间有没有草籽花瓣儿,脑后传来一个声音说,你都想哪去了?
也没想哪去。我叫她唬一跳,心想总不能这么多年过去,她还了然我的一举一动吧,忙从窗外收回来目光,胡乱搪塞说,我只是想到接受美学什么的,想到一个人要换一种心情打量没换心情前的事物,事物会呈现另一副模样。
行啊你,单小双也不回头,只从后视镜里乜斜我一眼说,好些年没见长学问了,还美学。
在此之前,我自觉不自觉地设想过我和单小双的很多种重逢,但没有一种符合眼下的情景。刚才下班时我发现自行车没了,在车棚里来回找了几遍也没找到。近期有一伙蟊贼盯上了我们报社的车棚,我一连丢了三辆自行车不说,还差点把同事江水莲的电动车也给丢了,后来才知道是她骑着它采访去了。打电话给江水莲,这家伙嘻嘻哈哈地说,今天的采访对象真是太讨厌了,非要请她吃饭。她本来不想吃的,但人家把饭局设在了濮云路上的韩国烧烤店里,想想烤肉也不太难吃,只好凑合着赏他们一个脸算了。我说你又送人情又解馋的,不是把我晾起来了,我还怎么回家?她还嘻嘻哈哈地说,我正要给你电话呢,有口福同享,还回什么家啊。这儿正好有你几个比粉丝还宽的粉条儿,人家都想见见你,你打个的过来吧,要不我叫他们单位派车去接你。这是2010年9月,金融危机还没彻底过去,健忘的人们又大吃大喝上了。我不大习惯凑热闹,哼了声挂断电话,悻悻地走向回家的路。
家在城市西南头,转好几路公交车也转不到家门口去。再说眼下秋老虎猖獗,公交车上又吵又挤,与其颠来倒去地坐那不顺路的车,还不如在街上溜达着好。也是因为家离单位远,我平时恨不得把自行车当成电动车骑,当成摩托车骑,来来回回都风驰电掣的,见缝就钻,见车就超,决不允许谁的自行车骑得比我还快,从不曾有事没事地在街上溜达过。这次步行,始知溜达也是需要心情的。我没有心情,便走得嗓子冒烟,头上冒汗。不时有出租车司机在我面前减速,也不时有三轮车夫冲我笑一笑,我一概不理,还给自己打气说,我自己的路自己走,再长的路我也能走到头。这时我还不知道我正朝着一桩艳遇走去,知道了也许会迫不及待地加快步子,当然,你也知道的,欲速而不达,真要快了就可能与其擦肩而过了。
是的,我与单小双的见面还得推迟一会儿,至少还得再拐一个弯儿,这些步骤,一个都不能少。从开州路拐上昆吾路,我仍像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一样引人注目,一个皮笑肉不笑的三轮车夫还用上了盯梢的工夫,耐心地跟着我亦步亦趋。我恼怒了,一拧身拐上了濮月路。濮月路背街,车少人稀,看看身后,果然没谁再尾随着我了。一路上,尽管我抗拒了五个出租车司机和三个三轮车夫的友好,但却对一个兜售冷饮的女孩动了恻隐之心。那时她迎立在路边,笑眯眯地招呼我说,哥,看把你热得,吃块雪糕吧。我已过了在大街上举着一根冰棍儿吮来舔去的年纪,但依然对青春少女有好感,就问她有什么水。她掀开雾气腾腾的冰柜向我推荐着,说这个去火,那个降血脂,还有那个和那个,既解渴又清心明目。我不奢望一瓶水有恁大的功效,随便扒拉出一瓶冰红茶说,就这个吧。女孩不过20岁,却人小鬼大,不仅像老到的卖瓜王婆一样擅长自夸,还通晓口蜜腹剑术,见我拿的是一张5元的纸币,就又甜甜地笑了一下说,哥,你看,一瓶三块钱,两瓶就可以给你个优惠价,五块钱好了,我这会正好也没零钱找你哩。我之所以接受她得寸进尺的建议,也不是贪图什么折扣,说到底还是不忍拂了人家一个姑娘的美意。
两瓶冰镇的凉水下肚,热劲是有所缓解了,接下来就有点尿急。近来动不动尿急,动不动就往厕所跑,也不一定尿多少,但总是非常迫切地想尿。要是在单位还好,在家的话,势必遭到妻子的白眼和唠叨,说在单位喝的水,凭什么跑到家来污染空气?污染空气一说固然冠冕堂皇,但她老人家在意的,还是那半盆乃至一盆冲尿的水。妻子的理财态度是,不能开源的话,就得千方百计地节流。为此她在卫生间放了一大一小两个桶,外带一个改造成敞口的油葫芦,专盛洗衣洗菜的脏水,美其名曰在给子孙后代节约水资源哩。我如果在脏水也用完的时候如厕,她就会叫我等等,等她淘了米洗菜,洗了菜再涮拖布拖地。一系列流程下来,我早已捧上小腹,感到堤坝岌岌可危,有汗从两边额角渗出来,或者是尿也未可知。这也罢了,可气的是我妻子对我的努力合作并不承情,反会不冷不热地说,你的防线太差了,不攻自破。说,是不是又有啥事儿瞒着我?
妻子近来老这样,动不动就拿话敲打我。她怀疑我在外面藏着私房钱,甚至有若干个相好。我常想,天下应该没有比男人更蠢的家伙了,从自己的肌体上摘取一根肋骨造出女人来,造出多少孽缘祸端来!骨肉分离之疼痛不必说了,还要养她吃养她喝,终于养虎为患,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横挑鼻子竖挑眼中,你早已一无是处。请神容易送神难,你再想叫她变回肋骨试试,她不吃了你才怪。在马桶前捧着一泡尿磨嘴皮子是一桩痛苦的事,也是一桩有失体面有损风度的事,一看见她端着一盆脏水泼你的样子,你就尿也不是,不尿也不是了。所以通常情况下,能在外边尿的尿,我通常不带到家里去。
尿意是突如其来的,来在我刚刚路过一个公共厕所的时候,尽管倒过去两三百米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我不想走回头路,一点回头路也不想走。我说过这条路车少人稀,不光两旁楼高,树荫也多得暗无天日,看看路边墙根那儿塔松林立,绿草掩映的,环顾左右了一下,闪身拐了进去。我一边尿一边本能地觑着外边,即便装得再若无其事,也还是害怕有人过来看见了,却不知这里藏着人,不知自己的工作已影响到别人的工作。那人惊叫了一声,我也吓一跳,一叫一跳间,人家就提溜上裙子了。待单小双看清楚是我,我看清楚是单小双,我们都觉得这次尿出来的奇遇,可真是奇得太离谱,也太缺乏诗意了。
然后我们没头没脑地乱笑了一通。隔着许多年的光阴,也实在笑不出什么深意或名堂。单小双先从坤包里摸出纸巾,给我和她各一张擦了手,接着摸出一串钥匙来。我看见路边不远处的一辆红色宝马响了一声,方向灯也跟着明明灭灭地闪烁,又忍不住乐了。她小时候数学不好,算不清账,没想到到现在还是,开着高级轿车找隐蔽处撒一泡尿,耗去的油是多少?当然,人要是开上了宝马,大约已犯不着计较。单小双问我去哪里,她可以用车送送我。我原本想照实说回家的,一上到她冷气充足的车上,我就哪里也不想去了。单小双笑了,看了我一会儿说,好像变化也不大。这么多年过去了,咋还这么黏糊?
也不是黏糊,我双手搓了一下脸,装沧桑样说,而是一下子掉到了美女香车的温柔乡里,跟梦一样,你叫我适应适应。
单小双说别酸了,美女早迟暮了。
我这才留意了一下单小双的脸,熟悉中流露出那么多陌生。我看不出她敷的是什么牌子的化妆品,但要命的是,无论哪个国家进口的脂粉眼影口红,都无法抵挡时光的侵袭,都经不起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打量。岁月无敌,即便是城市里,单小双见老了,单是眼角的鱼尾纹,就比我们分手乃至认识的年数还要多了。从她身上,我反观自己,怕是也好不到哪去。沧桑在那里明摆着,根本不用装。二十年了,我说,二十年的时间好漫长。
越过二十年的隔膜和尘埃,单小双显然也清楚自己经不起如此近距离的打量了,自顾自别过脸去,一边遮掩着戴上一副茶镜,一边发动了车。她又问我去哪,要不要找个地方坐坐。我想久别重逢,又是这么巧碰上的,是该找个地方叙叙旧。只是我拿不准这一叙,会叙出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我确信,跟不跟单小双叙旧,我需要像哈姆雷特那样,耐下心来踌一踌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