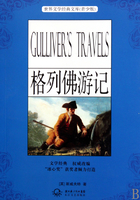然而,也许是心里还有些不踏实,或者乡下的竹床和凉席太硬,空气中也弥漫着太浓重的猪圈或羊圈里的酸臊气,再不然,就是乡下的夜晚实在太安静,以至于从墙角传出的三三两两的昆虫的鸣叫,也变得格外刺耳,反倒使得他更加难以成眠了……当然,除了昆虫的鸣叫外,蚊帐顶部那个“嘶嘶”作响的小电风扇,也像一条将身子盘成一团的小蛇,正不住地朝他吐着芯子,让他惊恐不安。
天气本来就闷热,他胸脯、背脊很快又汗津津的,忍不住摸过脱放在枕畔的背心在身上胡乱擦拭。
“怎么,你睡不着?”邬红梅问。“唔,有点热。”他说。
邬红梅想了想,起了身,到外间找到一块洗脸毛巾,在洗脸盆里用热水搓了搓,拧干,进来帮他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擦拭了一遍,然后又帮他捏脚……他这才渐渐由清醒而至于迷糊,并将蚊帐顶部的嘶嘶声当成了催眠曲,终于进入了梦乡。
然而,睡下不过一两个小时,他却又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那梦中,他的身份已不是堂堂的教育局局长,而是一个刚刚长大成人的高中生。他似乎正在教室里上课,又似乎在操场上跑步,但忽然发现身旁围满了人,都在指指画画地议论着他什么。他低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众目睽睽下,他竟然一丝不挂……他下意识地就用双手去捂自己的敏感部位,却听到四下里响起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声——“看,快看,那家伙在耍流氓……”于是,很快便有人领头大声呼喊起来,“抓住他,抓住这个臭流氓!”他在惶恐之中拔腿就逃,腿却像有千斤重似的怎么也迈不开步子,终于被人抓住,胳膊被反扭到身后,头则被一只大手强按着垂到腹部,差不多就要碰到那一堆晃晃荡荡的物件了。
“说,快说,你为什么要耍流氓?!”有人大声喝问。“没有,我没有。”他说。“还敢抵赖!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从小就无法无天,是个典型的流氓坯子!快说,你强奸了多少女孩子?”
“不,不是……”“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们的不是?”又有一个义正词严的声音在大声申斥。“我……”他还想解释,忽然发现嘴虽然不住地张着,嗓子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了。
“少跟他废话!他不是那玩意不安分吗?割了它,阉了它,看他以后还怎样耍流氓?!”
于是,早有几个人握着杀猪用的刀挤到他跟前,另一些人则闹哄哄地将他抬起来,七手八脚地强按到一张课桌上,然后,就见一把闪着寒光的刀在他面前一晃。
“不,不要——”他大叫一声,腾地坐起在铺上,双手下意识地紧紧捂住下体。
“怎么啦?你又怎么啦?”邬红梅也被惊醒了,知道他做了噩梦,于是也揉揉眼,坐起身。
“没什么,做了个很不好的梦。”他心神恍惚地说。她就没再追问,一边继续躺下,一边喃喃自语地道:“后半夜的梦应该是反的……”
然而,不管这梦是正还是反,龚合国自此却是再也无法入眠了。他也忽然想起不知从哪儿曾听到过的一句话,叫作“梦由心生”。
“奇怪,怎么会做这样的梦?我从小就很本分,还经常被评为三好学生,怎么会是个流氓呢?”
但他继续思考下去,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很显然,严格地追溯下来,即便还是在少年时代,他的确已经很有过一些可以称得上是“流氓”的劣迹了。
最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他曾跟着村里一帮男孩子去村东头偷老木匠家枣树上的枣子。那枣树又高又大,每年都结满了一树红红绿绿的大枣,让人见了不得不流口水。但苦于老木匠的老婆麻婶一整天都坐在门前一边做针线活,一边不住地拿眼瞟那枣树,他们很难得手。于是,他就想出一条“调虎离山”之诡计:麻婶家养了一头大肥猪,因为天热,这猪平时总喜欢躺在出粪口纳凉,于是,他便着人拿了一根树棍专门守在出粪口负责捅那肥猪。待那肥猪哼哼唧唧地叫起来,麻婶就会不安地跑进屋里去张望,看那猪是不是生病或“遭瘟”了——一头猪可是一个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于是,趁此机会,其他人便从藏身的墙后一跃而起,飞也似的扑向那枣树,短棒长竿照着枣子多的地方一顿乱砸……“这难道还不算是‘小流氓’的行为吗?不过……”他悠悠地又记忆起自己八九岁时,的确曾经跟着一批比他大不了一两岁的大孩子,在一个麻田里“强奸”过一个名叫“小莲”的女生。小莲的父母亲是地主和地主婆,但没想到,他们生出的女儿小莲白白嫩嫩的,就像城里人一样,比起许多贫下中农家的孩子可长得要秀气和漂亮得多了,而且学习成绩也好。所以,这让村里的许多男孩子既羡慕又嫉恨。
有一次,不知是谁出的主意,他们竟然设法将她诱骗到了村东头河边的那片麻田里,在麻田深处将她“轮奸”了。只不过,说是“轮奸”,其实也就是勒令她趴在地上,让每个男孩子轮番在她身上骑了骑,或者坐了坐罢了。然而,这是一个恐怖的预兆——那以后,大概是从上初中时开始,她竟真的不断地被人强奸了。先是被她的老师,继后是民兵营长、大队会计,后来还有插队知青……因为她出身不好,自然是求告无门的。于是,经常有人见到她在河边以泪洗面……终于有一天,在遭受了又一次凌辱后,大概以为家中洗脚盆里的水已经无法洗清她满身所沾染的污秽和耻辱了,她绝望地跳到了清澈的河水里……那年,她才16岁。
啊,小莲!想到这个熟悉而遥远的名字,龚合国心里不由得一紧——因为无论如何,小莲的被强奸,毕竟还是从他们这帮“小流氓”开始的,尽管他们那时还懵懂无知。
“可是,我绝不是……”他忍不住在心里说。
不过,当他的“梦中情人”,那个百货大楼的漂亮营业员的影子又飘浮在他面前时,他却感到自己越来越没有底气了。因为要说糟蹋,他可不仅仅是意淫,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在梦中奸淫过她许多次了……当然,现实生活里,他后来也“玩”了权莉,“潜规则”过……所以,他扪心自问,并在黑漆漆的虚空中仔细审视自己经常穿的那身黑衣、黑裤、黑皮鞋、黑眼镜,渐渐地竟觉得自己确实像个流氓了,甚至还越来越具备黄金荣、杜月笙的神韵……“可是,能做到他们那种水平的流氓,倒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了一趟……”他在床上翻了个身后又悠悠地想,继而则意识到:“……流氓其实也是有层次的,作奸犯科的都还是些低层次的流氓,高层次的流氓却常与英雄和伟人齐名。比如,刘邦为了自己逃命,不是还将亲生的儿子推下车去吗?曹操为了不让天下人负我,不也经常言而无信、滥杀无辜吗?……”
这样想,他渐渐摆脱了噩梦中“耍流氓”的阴影,反倒对另一种高层次的“流氓”无限憧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