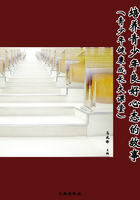许是屈原的缘故,中国诗人总喜欢逐清流而去,在江湖河海的怀抱中永远沉睡,诗人似乎对水情有独钟,水仿佛是诗人最终的安身立命之处,水就是诗人流逝的生命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水才多了一份悲凉的情愫。在那流逝的悲凉的世界里,心中常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的文化巨擘王国维(1877-1927)在学术研究如日中天之时,却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遽然在北京颐和园自沉昆明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而这一天离端午节只差两天;在那流逝的悲凉的世界里,载誉中外,举世瞩目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老舍(1899-1966)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一个黑色的日子里,怀着不尽的痛苦、困惑和愤怒,在首都北郊一处冷僻的、鲜为游客所注意的太平湖公园里投向了沉默的湖水,用屈原的自殉方式,向这个荒诞的人间作了警世式的抗议和控诉;而在同一天,着名文艺评论家陈笑雨(1917-1966)也作了这样悲壮而凄惨的选择,在永定河里沉没;着名作家李广田(1906-1968)则以冰凉的池水作为永远安息的栖身处,“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周瘦鹃(1895-1968)也在闷热得透不气来的一个深夜,不堪忍受政治***的压力、凌辱和摧残,与清凉的井水溶为一体;在那流逝的悲凉的世界里,当代北大诗人戈麦心灵过度的敏感和脆弱,在个体生存价值危机中毅然选择了个体生命的毁灭,面对真理而只能无言的绝望,在毁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诗作后,毅然于圆明园附近投水而去,使燃烧的诗意彻底熄灭;20世纪末夏天的一个清晨,海南三亚天涯海角,人们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发现了一具漂浮的尸体,惊讶的人们把他打捞上岸,确认他是重庆人胡佳文,曾经在重庆诗坛上闪光过的新星,出版有诗集《红苹果》,因诗歌而婚姻破裂,又因婚姻破裂而诗意全无,于是在一个深夜,他一个人在三亚海边听着涛声,望着无垠的大海,他没有拒绝那充满诱惑的召唤,一直向前走再也没有回头,任凭波涛汹涌的大海把他揽入怀中诗人啊,为什么如此眷恋于水?与水有如此的不解之缘?难道屈原的魂灵注入了诗人的体内?
翻开中国诗人自杀的名册,一个个你熟悉的或陌生的名字都让你感到触目惊心: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陈梦家,《红岩》作者罗广斌,散文家杨朔,翻译家傅雷,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杂文家邓拓,着名诗人闻捷,戏剧家田汉,着名小说家赵树理、孔厥、陈翔鹤、彭柏山,文艺理论家以群,美学家吕荧,文学评论家邵荃麟、侯金镜、胡先、陶然他们是在“红色恐怖”的“文革”岁月中加入中国诗人自杀行列的,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份灵魂撕裂的无言的抗争和控诉。这是一个时代诗人的集体的悲剧,因为在一个完全扼杀了诗意的时代,在一个根本不需要诗人的时代,诗被杀了,诗人的诗魂也就被杀了。而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到了20世纪末,中国诗人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仿佛又一次砰然发动,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苦难的脆弱的生命,以英雄式的沉默加入了黑色的死亡游戏:海子、陈泮(诗人江河的妻子,笔名蝌蚪)、方向、顾城、昌耀、徐迟、三毛;还有年轻的文学研究者胡河清、文艺批评家吴方、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宋祖良等。他们使死亡的话语成为最令人揪心的话语和最惊心动魄的诗篇,超越了人们用哀怜和回忆所勾勒出的意义轮廓。
然而,当历史无言地将中国诗人的悲剧浮现在我们眼前时,我却在死亡序列的另一头看到了域外诗人更为惨烈的自杀悲剧,我不想惊扰那些在历史深处沉睡久远的灵魂,我把沉痛的目光投向20世纪那些不幸的和勇敢的缪斯的信徒们,在那一幕幕残忍的自戕生命的悲剧里,我仿佛看到了杰克·伦敦、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哈特·克莱恩、海明威、弗吉尼娅·伍尔夫、斯特凡·茨威格、奥拉西奥·基罗加、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帕奥洛·亚什维里等,一个个充满忧郁和悲凉的“临终的眼”,我深深地感到不安的是我为什么要打扰这些已经安息的灵魂?如果越过死亡,回到死者生前放歌的岁月,我能将亡灵点燃言说的火焰燃烧下去吗?我能找到通向诗魂的入口处吗?
我首先想起那个与中国诗人同样喜欢与水为伴的美国诗人哈特·克莱恩,那个写出了被批评家誉为“20世纪美国诗歌的里程碑”的《桥》的海中孤魂。哈特·克莱恩生于1899年7月21日一个生活舒适却丝毫没有艺术细胞的商人家庭,父母的婚姻破裂使他承受着变态的母爱,以致弄得脾气海明威暴躁,过分敏感,并执着于同性恋。1908年他萌生了做一个诗人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只身来到纽约,很快打进了纽约文艺界。他漫游在现代主义和惠特曼的传统两个流派之间,从中吸收营养进行自己的诗歌创作。在艾略特《荒原》的影响下,他创作了《桥》,将历史、传记、地理统统溶进诗中,试图创造一个“积极的”美国神话,然而当时美国文坛无法理解和和无法接受这首史诗杰作,于是他的精力、才智、生命统统消耗在酒精里,他感到江郎才尽,只有和自己所爱的人一同走进一个爱的新的天地,他的美国神话才不会消失。但他所倾心相爱的人对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的价值观和深邃的洞察力并不理解,激烈的争吵粉碎了他的最后一线希望,于是他执意要把自己锁进漂游的花朵里。1932年4月27日那个黑色的日子,在墨西哥开往纽约的“阿里扎巴号”的轮船上,绝望而去意已定的哈特·克莱恩冲向甲板,纵身跃进了加勒比海,成了一个在大海中永远漂游的孤魂。哈特·克莱恩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美国的悲剧,在那样一个充满奇迹而又充满困厄的时代,一个充满艺术而又充满讽刺的时代,美国作家几乎都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哈特·克莱恩虽然并没有自杀的本性,但他的死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不幸的是哈特·克莱恩的悲剧在美国自白派诗人那里又一次悲壮的重演。当我把目光投向自白派诗人的黑色墓碑时,仿佛又回到了50年代到60年代自白派诗人风靡美国文坛的那个时代,在那样一个精神生活几乎崩溃的时代自白派诗人以静静的和不约而同的方式对抗社会习俗,毫无顾忌地揭示自己的性欲、死念、羞辱、绝望和精神崩溃等为常人避讳的隐私,常常恨不得在毁掉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的同时也毁掉自己,他们敢于同传统势力和不公正的社会抗衡的精神使他们常常以写自杀而着称。自白派诗歌的创始人罗伯特·洛威尔以“我就是一座地狱”
的名言成为自白派诗人顶礼膜拜的信条,而洛威尔本人差一点便自杀,其后的女诗人西尔维娅·尔维娅·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和约翰·伯里曼则都在成名后自杀身亡,尤其使人感到迷惑的是刚过而立之年的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夭折了。这个醉心于在自我和客观之间的关系中发掘混乱,几乎把自白诗那种悲剧式的忘我剖析推到了极端的女诗人,于1932年10月27日出生在马萨诸塞洲的波士顿市一个来自德国移民的家庭,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普拉斯从小就显露了写作的天才,17岁就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在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与英国青年诗人特德·修斯一见钟情,很快结为夫妇,随即回国,参加了自白派诗人运动。但普拉斯的精神生活却像江海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定,夫妻关系逐步恶化,诗人、贤妻、良母三重身份的缠绕使她几乎难以应付,流产、阑尾炎、怀孕,接二连三的住院,使她感到现代生活中的人不过是机器而已,人被阉割了完整的人格,面临着虚无又无可解决,只能在死亡中寻求意义。19岁时普拉斯曾第一次尝试过自杀,她服了50粒安眠药后藏身于地窖最不显眼的角落,经过长时间之后才被发现,并奇迹般地被救活,这次故意的自戕反映在她的小说《钟形罩瓶》(1963)里。10年后她又尝试了第二次自杀,她故意飞快地把汽车开出车道,造成撞车事故,却又一次神奇地活下来。然而1963年2月11日,普拉斯在精神极度错乱中吸煤气自杀,这一次她没有能够幸免,终于达到了“自我毁灭”
的最高形式,将其不朽的诗句“死亡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我要让她分外精彩”付诸于其残酷的实践。
文学声誉在英美等国超过劳伦斯的弗吉尼娅·伍尔夫,被誉为“当今世界上唯一具有超凡智慧的才女”,在58岁的时候自绝于人世令英国文坛为之震惊!她选择的归属竟也是清流!我无法描述1941年3月28日那个阳光灿烂却又充满凄凉的日子:已经好些天感到与远方的缪斯的召唤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弗吉尼娅·伍尔夫,给亲人留下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她姐姐的,一封是给她丈夫的,因为在这喧嚣而寂聊的人世,只有姐姐和丈夫是她深深爱着的人。她一生经历过许多黑暗的岁月,父母的早逝和其它亲人的离去,精神病的折磨,自杀未遂,不能继续创作,和丈夫虽然忠贞相爱,体贴入微,却缺乏灵魂的撞击,他们无法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她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和恐惧,战争又毁了她在伦敦的家,只好迁居到乡下的别墅,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人世知音难觅,她的精神崩溃过多次。她并不害怕死,问题是陷入生死不能的境地时,她只好寻求一直诱惑着她的让她感到愉悦和宁静的流水,童年时代她就听惯了窗外拍岸的淘声,水成为她最亲密的朋友,水,大海,波涛成为她和她笔下人物生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她愿意化为清流的一份子,那是她最幸福的解脱。她从容地拿起心爱的手杖,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寓所,来到乌斯河边,凝视着迷人的流水,在波光粼影里她仿佛听到了一种甜美而动听的召唤,这召唤令她感动得泪流满面,让她的灵魂颤抖。她心中充满着回归水的渴望,于是她把手杖轻轻丢在岸边,然后将石块塞满衣兜,毫不犹豫跳进冰冷的河中,汇入了永恒的流水。
弗吉尼娅·伍尔夫的死让英国文坛震惊了一下,而在她之后的川端康成的自杀身亡不仅令日本列岛,更让世界文坛哗然和震惊。
川端康成从一出生就没有享受过人间温情,接二连三失去至亲的悲哀一再打击着他的压抑的童心,并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因此他除了寂寥和孤独之外就是苦闷。直到20岁时一次伊豆温泉之旅,才改变了他的人生,一个美妙的歌女犹如一朵完美之花照亮了川端康成20岁的心灵,也照亮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
《伊豆舞女》以其情节和情景的甘美以及青春形象的清纯风靡世界文坛,为日本民族和世界文坛塑造了一个永恒的美的形象。然而这样一个如此珍爱花蕾一般未被生活尘埃污染的少女的人,却没有勇气生下一个如花的女儿,因为他锐利的目光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了生活对于美的摧残,他不敢让儿女们出生,他虔诚地维护着他心中的女神。他不停地搬家,因为他要择美而居,择清净而居,世事于他如浮云。58岁时,孤独到极点的川端康成开始了一次孤身旅行,他到国外是为了寻找美,发现美,享受美。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人们精神空虚,思想沉沦,道德水准下降,物欲横流。川端康成走遍了世界,却发现自己更孤独了,他发现的美只是在他心中,没有人愿意也不可能和他分享,他只能自嘲是一个“无赖闲人”,一个多余的人。所以突然有一天他像彩虹出现般地消失了,令人惆怅不已。世界文坛有幸,出现了这位完美的大师;大师不幸,因为他终被人间烟火窒息,包括他的自杀方式:口含煤气管窒息而亡。虽说日本似乎有一种自杀的传统,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不到一百年之间就有七八个知名作家相继自杀:明治时代的厌世诗人北村透谷自缢而死,白桦派文学的重镇有岛武郎与恋人双双情死,还有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太宰治、田中光英、三岛由纪夫都自戕而亡。然而谁的悲剧都没有川端康成这样让人扼腕,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散步去。”川端累了,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就说“累了”,现在他是去天国散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