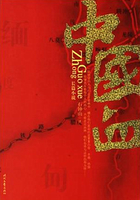长期的劳累让萧红的身体和精神都快垮掉了。朋友黄源提议萧红去日本住一段时间,换个清净的环境疗养一番,还可以趁机学学日语。他妻子许粤华此时就在日本,二人也好有照应。
萧红和萧军都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一来是身体所需,二来两人的情感进入了危机,或许分开一段时间于己于他都有益无害。于是,萧红踏上了去日本的航船,而萧军则搬回了青岛。
早在哈尔滨的时候,萧红就与胞弟张秀珂取得联系。时常通信联络,给他寄去自己的作品,而当张秀珂来到哈尔滨的时候,萧红已经逃到青岛了。萧红去日本的时候,张秀珂正在日本留学。萧红本来想借机看看睽违已久的弟弟,谁知张秀珂却说自己早已回国。屡次的擦肩而过,令萧红十分失望。很久之后萧红才知道,原来当时时局严苛,张秀珂早就被日本当局盯上,加上萧红又是中国著名的左翼作家,若是见面会给两人的处境带来极大的危险。
萧红起初和许粤华住在一起,没过多久,许粤华回国,她便只好独居。刚刚到日本,一切都觉得无所适从。在市井里习惯了嘈杂的萧红觉得日本安静得可怕。远在大洋彼岸的萧军依旧是她唯一的寄托,她给他写信倾诉在日本的一切,嘱咐他要买软枕头以防损坏脑神经,要照顾好身体。萧军则寄给她自己安排周密的作息表,像革命伙伴一样相互鼓励,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远。而爱情,在这时已经悄悄地变了质。
就在许粤华回到中国之后,萧军与她坠入爱河。远在他乡的萧红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她并没有之前那样的反应强烈。在日本的时日已经让她渐渐清楚,她与萧军的爱情早已不可挽回,如今的关系也只是勉力支撑,随时都有可能溃散。她在组诗《沙粒》中写:
11今后将不再流泪了,不是我的心中没有悲哀,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失了我了。 26当悲哀,反而忘记了悲哀,那才是最悲哀的时候。 34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在她离开上海三个月后,鲁迅逝世,她在日本悲痛却不能言。次年,她回到上海,参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出版工作。1937年 8月,上海沦陷,成为“孤岛”。
在萧红回国之前,张秀珂就已经回国,逃离了呼兰县的家庭,转而投奔萧军。据他说,此时的二萧常常吵架。每每被张秀珂撞上,都以为是萧红的过错,渐渐地他就站到了萧军一方,与姐姐生疏起来。直到十年后回忆起来,他才明白当时的事情萧军也要负责,并不全是萧红的过错。
萧红脸上甚至经常挂彩,旁人问及,萧红便说是自己不小心撞的。而萧军则“一人做事一人当”说是自己打的。此时,萧军和萧红的关系继续恶化,黄源和许粤华也已经离婚。一切仿佛已成定局,只是事中人还不愿意接受。
失落的原乡
端木蕻良第一次见到萧红是在《七月》的筹划会上。当时他刚刚从青岛来到上海,追随茅盾先生左右。
端木的性格比较内向,寡言少语。因为是辽宁人,因而很快地和同样来自东北的萧红、萧军谈到一起。这两位年轻作家的名声他早有耳闻,如今见到本人还是十分惊喜的。尤其是萧红豪放的作风令他十分钦羡,这样的率直无拘的女子在当时那群文人中间必定会成为一道醒目的风景线。
之后,上海的形势越发危急,萧红与萧军去武汉。他们住在诗人蒋锡金家中。萧红担当起主妇的工作,照顾萧军和蒋锡金的饮食,为他们洗衣服。也是在此时,萧红开始提笔写《呼兰河传》。大片的抒情,看似凌乱无章的叙事明明是散文的写法,都令蒋锡金十分不解,这是小说吗?然而其文笔和情意又令蒋锡金十分欣赏。
不久,二萧写信给端木,让他也赶赴武汉,与大家一起继续办《七月》杂志。端木来到武汉之后,住到了蒋锡金的房间中,于是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再后来,女漫画家梁白波也搬来住了一段时间。五个年轻人一时间又在武汉搭起了文艺阵地。
虽然萧军亲自写信让端木来武汉,他的到来还是给萧军带来了危机感。萧红和萧军的关系本身就一直都处于边缘地带。而此时,萧红对这个比她年轻的弟弟十分照顾,常常与他很是亲近。端木非常欣赏萧红的文章,甚至说她的文章比萧军的更好。这无疑给萧红很大的鼓舞。在文学道路上,萧军一直与她有很深的分歧,萧军将他的大男子主义带到了文艺欣赏上,曾经屡次在人前说萧红的文章不好,,说过“结构不严谨”“秀丽、但是不伟大”之类的话语。他对此习以为常,而把文章作为命根子的萧红却一直隐隐地自吞苦泪。
那时候,端木常常回到房间,发现几张写了字的纸,便明白是萧红来练过字了。“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萧红反反复复地写这首古诗,还特地将最末一句多写了几遍。她对端木的情感一直令人猜测,到底是因为与萧军走不下去了,随手抓来的一根救命稻草?还是久逢甘霖,终于遇到倾心的人呢?
这首诗是端木后来的妻子钟耀群记录在《端木与萧红》一书中的故事,若是这故事成立,那么想必萧红对于端木的情感也是早就萌芽了。
1938年,萧红萧军一行人赶赴临汾,去正在组建的民族革命大学教书。在此,萧红遇到了丁玲,并且一见如故。
萧红和端木的亲近,渐渐让萧军起了疑心。他与萧红大吵,在人前说端木软弱无能,还要与端木决斗。与萧红打架之后,他便一脚踹开端木的房门,质问他萧红的去处。他的大男子主义简直是野人一般,而端木则站在他的对立面,像个女孩子一般腼腆,又对女人十分地尊重。
后来,萧军在临汾与萧红分别,去前线追求他的梦想。萧红没有同去,一来是因为感情早已走到了尽头,她没有办法再继续伪装下去。二来,萧红的政治立场从来都是坚定的,她是一个左翼作家,也仅此而已。她不会让政治来围困她的自由,如她所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全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上世纪 30年代在上海,众星捧月围着鲁迅的青年里,萧红无疑是最得其真传的,因而也是鲁迅最喜欢的一位。
在重庆期间,她还拒绝了去当大学教授的机会,认为教学会使得她的文章刻板、有学究气。她自诩为《红楼梦》中的痴丫头香菱,梦中都在写作。这样一个人,自然不会成为政治的俘虏,自由才是她的追求。
萧红回到武汉之后,与端木结婚,腹中怀着萧军的孩子。他们的结合在朋友眼中十分的不堪,几乎没人承认他们是结婚,有些朋友甚至与他们断绝联系。萧红百年之后,亦无人替端木说话。在那些文人朋友的笔下,这是一个自私、懦弱、没有担当的男人。
1939年,武汉也渐渐受到了日军的侵袭,二人决定去重庆。端木与友人先走,留下大肚子的萧红踽踽独行。她不无悲戚地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这句苍凉的独白好像是她这些年的写照:战火从东北烧到南方,又从南方烧到内地,她也就一直被这火驱着赶着,一路流离。
在重庆,不停地颠簸使得她腹中的孩子流产。这一次,她有能力养育,却没有机会生下来。
1940年,内地战事吃紧。端木和萧红刚好为香港的一些报刊写文章,便想着去那边躲躲。于是与端木一同前往香港。来到香港之后,二人住在狭窄的小屋里,一张桌子,相对而坐,终日辛勤写作。
萧红的身体渐渐垮了,她被劝住进了跑马地养和医院。在此之前,东北作家群中的一个年轻人也来到了香港,他叫骆宾基,是陪伴在萧红身边最后的人。
萧红入院后,香港的战况也逐渐危急,为了帮助萧红和端木二人,骆宾基放弃了回到内地,而是留在了香港,照顾左右。
萧红住院的这段往事日后成为了一段谜案,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斥责端木的离去,将萧红一人抛在医院里,而端木却以外出求救为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不管其中实情如何,想必在萧红最后的岁月里,对端木都是失望的。她曾经对骆宾基说:“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对萧军的眷念,不过是来自于对端木的失望。在她的遗嘱中,《生死场》的版权给了萧军,《呼兰河传》给了骆宾基,《马伯乐》给了张秀珂,唯独端木未曾分到半杯羹。
从内地到西北再到香港小岛,这一路,她一直在颠簸,却一直在回忆。与萧军的感情,鲁迅的逝世,无一不是她的痛苦所在。这个逃离家门的女子也开始怀念起了家乡,怀念起后花园里宠爱她的祖父,怀念那条从记忆中滔滔而逝的呼兰河。她提笔写《呼兰河传》,寥寥十万言,却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当现实已经一片冰冷,她只得从回忆中寻找慰藉,汲取温暖。这部散文诗一般的田园牧歌是萧红给文学最大的献礼,她被称作“30年代的文学洛神”。若是她听到了,必定又是一笑:我哪儿是什么洛神,不过是呼兰县里飞出的精卫鸟。她从记忆的庄园中取出一砖一瓦,细细地摆放、建筑,企图在这大海之南,再造一座后花园。
卧听海涛闲话
1944年,斯人已去。那些闲言碎语和人事纠纷在内地继续各执一词地争辩、吵闹。在香港浅水湾的萧红墓,故人戴望舒写下了一首《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很多朋友眼中,萧红给人的感觉是“不具寿相”。然而,她又是一直如此地饱含生命力地活着。她的一生经历过很多次死亡。少女时代,在逃到北平的时候,她在小屋中煤气中毒,醒来之后她叹道:“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
在福昌号屯的软禁岁月里,在东兴顺旅馆被当作“人质”关押的岁月里……她自杀的理由是如此充足,可她没有想过死。
她一直相信活下来就会有自由,而死亡,是绝不甘心的。天才如她,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更多的文章要写。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她被庸医误治,喉管开刀,因而不得言语。她拿着笔,勉力支撑,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的悲剧是女性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母性和童心构成了她的全部个性。她对于万物有着极大的悲悯和领悟,地母一般宽容博爱,因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去爱 ,她永远像一个母亲那样去毫无保留地爱着男人,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宽容他们。可是她的肉身又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容易对人产生依赖。她把生命中的每一个男人都当作救命稻草,对王恩甲的信赖,对萧军的依恋,都是她致命的弱点。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仰视她的“弟弟”端木蕻良,他却是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所以,在爱情的道路上,她必定会失望。
她在小说中反复地探讨生、死、生育、失去……这些看似宏大的话题其实是她从少女时代就开始目睹和经历的东西,是她最深刻也最直接的生命体验。她所生活的时代给予女性的舞台本身就很小,而她的思想和才情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舞台的容载量。正如她与好友聂绀弩在聊天的时候所说的: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弱,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下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性情。我知道,可是我还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
萧红的一生如昙花乍现,在红尘中晃了个身儿,便又匆匆离去。仿佛从一开始,她便预见自己的生命太短,因而迫切地要逃离,要抓住……而最终,那些急匆匆要留下的人啊情啊都化作指间沙,缓缓地流走。在那段荒芜的岁月里,只余下遥远的记忆与她互相取暖,一点一点地丧失了生命的温度。
参考书目:
季红真 .萧红全传 .现代出版社,2012.钟耀群 .端木与萧红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王观泉 .怀念萧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骆宾基 .萧红小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悄吟 .商市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萧红 .呼兰河传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