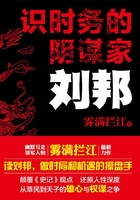萧红的一生如昙花乍现,在红尘中晃了个身儿,便又匆匆离去。仿佛从一开始,她便预见自己的生命太短,因而迫切地要逃离,要抓住……而最终,那些急匆匆要留下的人啊情啊都化作指间沙,缓缓地流走。在那段荒芜的岁月里,只余下遥远的记忆与她互相取暖,一点一点地丧失了生命的温度。
关联人物:萧军、王恩甲、鲁迅、端木蕻良、骆宾基等等。
娜拉出走
她的故事仿佛开始于那场大水,大水冲溃了她的围城,又给她圈上新的枷锁。
1932年 8月 7日夜里,松花江决堤,连续两个月的强降雨使得整个黑龙江流域被淹没。当时,萧红住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挺着大肚子,绝望地捱过一日又一日。
去年深秋,她和未婚夫王恩甲开始在这里同居,欠了旅馆很多钱。王恩甲借口说要回家拿钱,却一去不复返。当时萧红已经临近产期,未婚夫这一走,所有的债务都压到了她身上,几乎濒临绝境。旅馆老板说如果她无法付清欠款,便将她卖到妓院。
被逼到绝处的萧红,给当时哈尔滨的几家报纸刊物写信求助。几家均没有理睬她,以为是投稿者为了引起注意故意捏造的谎言,之后她又给《国际协报》的编辑裴馨园写求助信,历数她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如何逃出家门,如何被未婚夫抛弃。裴馨园看了她的求助信很受震撼,可是编辑们又没有足够的钱财将她救出来,只好用些小钱来接济她的生活,并给她带去一些读物。
萧军,原名刘鸿霖,是辽宁乡下一个细木工的儿子,1925年考入张学良办的陆军讲武堂,之后渐渐开始文学创作。他于 1932年初来到哈尔滨,当时是《国际协报》的撰稿人,发表了些文章,日子却也一穷二白,靠着每月 20元的稿费生活。之后,他受裴馨园之托,带着信件和书籍走进了东兴顺旅馆。经茶房的指点,他走到了甬道尽头的小房子跟前。萧红就在里面。
她挺着大肚子,脸色苍白,发丝凌乱,因生活的苦难而生出和年龄不相符的白发。在那个发霉的小屋里,她大概更像一个可怜的女囚徒,等着死期步步逼近,而非正当华年的女子。
如果不是桌上的字画,萧军可能就此别过,例行公事一般地结束慰问了。她叫住了他,开始央求他与自己聊天。他们一起谈论文艺作品,谈论当时的作家,萧军则坦言自己的爱情观是:
“爱就爱,不爱就丢开!”萧军问她,桌上的字画和诗歌是否是她的作品,她害羞地点头。就在这聊天的瞬间,萧军感到讶异,这个看似羸弱的女子居然有着如此美丽的思想和坚韧的生命力。两个年轻的灵魂像是寻到了丢失已久的另一半,紧紧地契合在一起。萧红向他讲述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她叫张乃莹,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之家,父亲张廷举是呼兰县的教育局长,接受过新式教育,却用旧式的思维来限制女儿的自由。萧红读到中学之后,他便不允许她升学了,怕女儿到了大城市会学坏。
在很小的时候,张廷举便给萧红安排了一门亲事,是骑兵团长王廷兰的儿子王恩甲,双方家长还给二人订了婚。后来,两家商量,同意让萧红继续念书。她这才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
在哈尔滨读书的日子,萧红第一次见识到大城市,她爱上了绘画,立志要做一个画家。而她的那些女同学中,常常有人遭遇不幸,从别人三三两两的事迹中,萧红隐约预见到:未来的不幸都是来自婚姻。有同学被官员强抢去做小妾,有同学被家中安排嫁了人,从此便成了三从四德的小妇人。
这些都是萧红无法容忍的,她喜欢有思想的知识青年,痛恨纨绔子弟和包办婚姻。然而,她的未婚夫王恩甲便是一个纨绔子弟,吸鸦片,恶俗,不务正业……萧红对于即将来临的婚姻感到恐惧,这时候,她的一个远方表哥陆振舜出现了。他和萧红一样,是新式青年,虽然已经结了婚,却还坚持自己的想法,痛恨包办婚姻和家庭的羁绊。两个人在一起谈论未来,宛如知己。陆振舜去了北平,追求自己的求学理想,随后又让自己在哈尔滨的同学带信给萧红。萧红不久之后就追随他去了北平。
“张乃莹与表哥私奔”这事儿在呼兰县闹得沸沸扬扬,张廷举在呼兰县有些地位,因而这事儿更让他脸面丢尽。
萧红与陆振舜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家人的反对,很快丧失经济来源,他们就像鲁迅《伤逝》中描写的子君和涓生,最终还是向家庭投降。如鲁迅先生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后无路可走。”
萧红回到了呼兰老家,被家人软禁在福昌号屯。家族中每一个人都对她冷嘲热讽,出走的失败令她在这个家里更无地位可言。每一双眼睛都如尖刺一般,把她钉在这个封建庄园里,不得离开半步。“九一八”事变为萧红的逃走提供了契机,她搭上送白菜的马车,从福昌号屯逃出,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再一次来到哈尔滨,萧红四处求救无门。此时,未婚夫王恩甲出现在她眼前。虽说王恩甲是个沾染恶习的纨绔子弟,可他对萧红却是一片真心。二人恋人一般同居在东兴顺旅馆,萧红腹中怀着他的孩子。
可是之前的私奔事件却让萧红在王家人心中信誉破产。当时王廷兰已经去世,当家的是王恩甲的哥哥,他根本不承认萧红腹中的孩子是王恩甲的。于是拒绝从经济上救济她,并且劝王恩甲与萧红解除婚约。就这样,王恩甲很快就不见了,留下萧红一个人在东兴顺旅馆苦苦地等待他回来……萧红的凄惨遭遇让原本就大男子主义的萧军十分感慨,默默发誓一定要拯救她。即便如此,他也无法将萧红从水深火热中救出。他的贫穷让他无所畏惧,同时也让他失去了保护爱人的本领。他唯有用强壮的体魄去威慑他人,用最原始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的爱人。在离开旅馆的时候,他蛮横地警告旅馆的店员一定要好生照顾萧红,不许再威胁或是欺侮她。
那天她写下《春曲》:
我爱诗人又怕害了诗人,因为诗人的心,是那么美丽,水一般地,花一般地,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但又怕别人摧毁,那么我何妨爱他。
从此之后,萧军便常常来看她,俩人渐渐进入热恋期。经萧军的介绍,一些左翼文学青年也看到了萧红的诗,欣赏她的文采,时常来看望她。众人都对萧红的境况感到同情,却没有办法帮助她脱离苦海。
于是,上天开了个口子,让漫天大雨堕入黑龙江流域。也是这个口子,给萧红打开了逃出生天的契机。1932年 8月 7日夜里,松花江决堤,大水开始漫入旅馆内。一楼被淹没,客人们纷纷逃到二楼。到了 8月 9日,旅馆的老板也逃走了,根本无暇顾及欠债的萧红。大水还在继续漫涨,萧军和舒群坐在租来的木划子上接她。
在那个夜里,如临大敌的哈尔滨城内每个人都经历着兵荒马乱,或许只有她一人心中是宽慰的。一场大水冲走了所有前债,给她的生活打开了新的入口。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逃离之后,她总算是获得了自由。这个中国的娜拉终于出走成功。
爱君笔底有烟霞
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
这是晚清才子张船山的妻子林佩环写的诗,表明自己一片芳心托付给张船山这样的才子,即便是受苦倒贴也在所不辞。这诗用到彼时的萧红与萧军身上恰到好处。
比起还有金钗可当、有酒菜可食的林氏与张船山,萧红与萧军可以说是真的一穷二白。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记录着这段时光的点点滴滴,每一篇都写满饥饿和寒冷。
萧红逃出东兴顺旅馆之后寄住在裴馨园家中,不久,萧军也住了进来。因为寄人篱下,难免觉得不习惯,萧红又十分寡言,这一点令裴馨园的家人觉得她十分难以相处。于是萧红干脆每天上街压马路,一边等萧军回来。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与萧军在大街上手拉手,恩恩爱爱地招摇过市,令裴馨园一家十分难堪。
当时人们的思想很保守,再加上萧红之前的遭遇,她在家中就一直被误认为是私生活放荡的女子,裴馨园自然也觉得难以接受,于是在路上碰到二人也是冷眼,甚至不应他们的招呼。萧军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以为是经济关系导致他遭到裴馨园的冷遇。
不久,萧红的预产期到了,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萧军到处借钱却毫无收获,于是裴馨园给了他一块钱,这钱只够他雇马车的。萧红住进了哈尔滨市立医院,生下来一个女婴,本身就十分孱弱的她因此又大病一场。
因为无力支付住院费,医生们对她十分冷漠,也不给她医治。萧红受不了医院中的种种冷眼,对萧军说要出院。萧军安抚她,安心养病,自己又跑去找医生理论,医生只是以庶务作借口,说不支付住院费就不给她看病。萧军一怒之下在医院中大闹一场,拼了命地要医生给萧红医治。医生欺软怕硬,看到他这个架势便都乖乖地就范了。
之后,为了躲避庶务追款,萧军从窗户中跳进病房来看望萧红。萧红生下了女婴,却从不敢看她,害怕自己一旦看到了孩子便母性大发,不再舍得离开她。可是此时的萧红萧军连自己都无法吃饱穿暖,又如何养活一个初生婴儿呢?于是,这个孩子不久便被送走。这是萧红第一次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这个在爱情途中总是颠沛流离的女人拥有最纯真的母性,却一再失去发挥它的机会。
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萧红终于得以出院。他们离开了裴家之后,便暂住在欧罗巴旅馆。五角钱一天的铺盖他们不租,六角钱的夜饭他们也不包,多花一分钱,他们都是付不起的。萧军在报上登了免费的求职广告,说自己可以做家庭教师,教国文、武术。于是不断地有人登门,有人问能不能教《庄子》,有人说,想学武术强身健体,也有人看到他们穷酸的境况便扭头就走。
就这样,两人凭借着萧军的零碎收入勉强度日。萧红这个原本家境优越的小姐此时又一次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她成为别人的妻子,却依旧是小姐的心态,不会持家,更无家财可以供她精打细算的。这时候,维持生活凭的是耐力。他们日日在牙尖上省食,萧军出门工作,喝一口茶便走,虽然等一下要教武术。萧红躲在小房间中,听着屋外的市声,嗅着别人的食物香气,艰难地捱着。她看到街上乞讨的乞丐,想到了自己其实与他们无异。“列巴”圈挂在别人的门上,她甚至想到了偷,经历了几次心理斗争之后,还是忍住了。
那些日子,她一直活在等待中,等待楼下传来萧军“噔噔噔”的脚步声,为她带来食物和恋人的温暖。
她在《饿》中写道:“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
——《黑“列巴”和白盐》
“列巴”就是俄式面包,在东北很常见。当年萧红与萧军经济好的时候,就以此度日。新婚宴尔,二人说笑着要度蜜月。于是萧军学着电影中的人物,将黑列巴上涂上白盐,送入萧红口中,让她先咬一口,然后自己再去吃。白盐毕竟不是奶油,一口下去就受不了,只好大口大口地喝水,然后嚷嚷道:“不行不行,再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
这就是萧红和萧军的爱情,穷、苦、饿、冷,却一直保持乐观。他们就像两个永远饱含生命力的孩子,在人生的长途中结伴而行,与苦难力搏。
不久,萧军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家庭教师的职业,给一位姓汪的庶务科长家的儿子教武术,酬劳是可以住到他们家。于是二人拎着个箱子跳上马车,箱子里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穷人的潇洒就是身无长物,因而可以两袖清风。他们搬到了商市街 25号的耳房里,在那里搭建起家园。
这就是“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穷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
——《他的上唇挂霜了》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家。什么都没有,对于萧红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唯一赖以生存的爱也开始濒临危机。
他们搬到汪家的时候,汪家的兄弟姊妹来拜访老师。其中有个小姐叫汪林,生得漂亮,又是富人家女儿,自然衣着打扮都要鲜亮。她自称是萧红当年的同学,每天都能在学校看到萧红。萧红当下觉得自惭形秽,她也不过二十出头,却已然容颜苍老,衰败得如同三十多岁。太多苦难让她过早地丧失青春,她自嘲地写道:“追逐实际吧!青春唯有自私的人才系念她。”
也就是从那时起,汪林开始成为她心间的一根刺。
《夏夜》中写,夏天很热的夜里,萧红因为瞌睡早早地入睡。郎华(萧军)与汪林在院中长谈。萧红不知道那些个夜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萧军多晚才回到房中。直到萧军主动对她说起汪林:“她对我要好,真是……少女们。”
萧红心中觉得奇怪,贫穷已婚的家庭教师和美丽富有的小姐,她知道二人是没有未来的,而她也无法离开萧军。于是她向萧军分析他们无法在一起的各种原因,萧军最终打消了念头。其实,在那些个夜里,汪林已经向萧军提起了结婚。
汪林始终是初解爱情的少女,来得快,去得也快。之后,萧军和萧红便邀她一起去游玩,还带上另一个未婚的编辑,有意撮合他们俩。汪林很快便把心思从萧军身上转移,与编辑要好。
可就是在这时,萧红遇到了更大的情敌。一位从上海来的中学生陈涓来家中拜访她,其实她与陈涓素昧平生,自然知道她是借机来探望萧军的。因此萧红态度十分冷淡,几乎针锋相对。陈涓明白其中意思,便不再常来,最终黯然离去,回到南方。
萧军虽然穷,当时却在哈尔滨文坛小露锋芒,军人出身的他还孔武有力,五官也算得上英俊,十分有男子气概。因此,很多女子都对他心生爱慕。而萧军早早地就阐明了自己的爱情观“爱就爱,不爱就丢开”,他的爱情从来都是迅风疾雨,并且极其自私,毫无责任感。大男子主义让他很少考虑到萧红的感受,爱的时候,把她当作孩子一样宠着,不爱的时候,则二话不说地背叛,与他人交好。萧红则相反,她经历过好几次的爱情,然而每一次她都处于一个无力的弱者地位,她会全心全意地去爱,在爱情无以为继的时候,她则选择伤痕累累地离开,来成全对方的背叛。这种离开近似于被丢弃,所有爱情的苦果都被加诸彼身。
这种潜在性格差异,让萧红无力掌控萧军的背叛,而萧军则从来不会顾及萧红的感受。这也是二人最终几度面临情感危机的根源。
小小红军
萧红在绘画上小有天赋,在学校时候就十分爱画画。为了赚钱补贴家用,她作为副手与邻居金剑啸一起给电影院画广告。而大男子主义的萧军虽然穷得叮当响,却不同意自己的女人出去工作。但最终还是拗不过倔强的萧红,只好跟着她一同去画画,给她打下手。最后,人家没有认可他们的广告,三个人却这样熟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