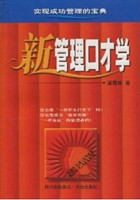文/萧潇
那是十九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刚满九岁,同母亲住在川南那座叫茶子山的山脚下。那时我经常怀疑自己没有父亲,因为,父亲远在省外一家兵工厂上班,一年最多回家两次,住的时间也极短。他留给我的印象,平淡得像那个隔十天半月便来我们村子吆喝一阵的补锅匠,他的模样在我脑海里如荡漾在水中的山峰一样模糊不清。
母亲长着一副高大结实的身板,和一双像男人一样结着厚茧的手,这双手只有在托着我的脑袋瓜子送我上学或搔着我的后背抚我入睡的时候,才能让我感觉到母性的温柔与细腻,除此之外,连我也很难认同母亲是个纯粹的女人。特别是她挥刀砍柴的动作,犹如一个左冲右突威猛无比的勇将,闪着灼人寒光的砍刀在她的手中呼呼作响,手臂粗的树枝溃军般在刀光下哗哗倒地。那时的我虽然幼小,却也极不欣赏母亲这种毫无女人味的挥刀动作。
然而在那个有雪的冬夜,在那个与狼对峙的冬夜,我对母亲的所有看法,都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后全部改写。
学校在离我家六里外的一个山坳里,我上学必须经过一个叫乌托岭的地方,乌托岭方圆两里没有人烟,岭上生长着并不高大的树木和一簇簇常青的灌木丛。每天上学,母亲总是把我送过乌托岭,放学时母亲再来这里接我。接送我的时候,母亲身上总带着那把砍柴用的砍刀,这并非是怕遇到劫匪,而是因为乌托岭上有狼。
1980年冬的那个周末,下午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在学校玩耍忘掉了时间,母亲找到学校来。当我随母亲走到乌托岭的时候,月亮已经在我们的头顶升起。
这是冬季里少有的一个月夜,银色的月光倾泻在丛林和乱石间,四周积雪般一片明晃晃的白。树木昏暗斑驳的影子静静地投射在山岭上,不知名的鸟儿在林子深处呜叫,叫声凄厉绵长,久久地回荡在空旷的山林里,给原本应该美好的月夜平添了几分恐怖的气息。
我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生怕在这个前不挨村后不挨店的鬼地方遇到人们常说的狼。
然而,狼却在这时候真的出现了。
在乌托岭上的那片开阔地,在如水的月光下,四簇莹莹的绿光,突然从一块大石头后跃了出来。我和母亲几乎是同时发现了那四簇令人恐惧的绿光——那是狼!母亲立即伸手捂住我的嘴,怕我叫出声来。
我们站在原地,紧盯着两匹狼一前一后慢慢地向我们靠近,确切地说是一匹母狼和一只尚幼的狼崽。在月光的照射下,能明显地看出那是两匹饥饿的狼,母狼像一只硕大的狗,狼崽紧紧地跟随在母狼的身后。
母亲一把将我揽进怀里,我们都屏住了呼吸,眼看着一大一小两匹狼,大摇大摆地在离我们六米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仿佛冒着绿火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我们。
母狼竖起了身上的毛,摆出腾跃的姿势,准备随时扑向我们,用那锋利的牙齿一口咬断我们的喉咙。狼崽慢慢地从母狼身后走了上来,和母狼站成一排,做出与它母亲相同的姿势,毫无疑问,它们是要把我们当成训练捕食的目标!
惨淡的月光,没有风,连那不知名的小鸟也停止了呜叫,一切仿佛都在这个时候静止下来,连空气也凝固了,让人窒息得难受。
我的身体不由得颤抖起来,母亲用左手紧紧揽着我的肩,我侧着头,用畏惧的双眼盯着那两匹将要向我们进攻的狼。隔着厚厚的棉袄,我仍能感觉到母亲手心的汗渍正在浸入我的肩膀。我的右耳紧贴着母亲的胸口,能清晰地听见她胸口不断擂动着的狂烈而急速的“鼓点”声。
而此时母亲的表情却是出奇的稳重与镇定,她轻轻地将我的头朝外挪了挪,伸出右手慢慢地从腋窝下抽出那把尺余长的砍刀。砍刀因常年的磨砺而闪烁着慑人的青光。
寒冷的月光随着刀的移动而不停地在树林里跳跃,杀气顿时充满了整个乌托岭。两匹狼迅速地朝后面退了几步,然后前腿趴下,身体弯成一个弓状。我紧张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我听母亲说过,那是狼在进攻前的最后一个姿势。
母亲将刀高举在空中,一旦狼扑上来,她会像砍柴一样毫不犹豫地横空劈下!
那是怎样的时刻啊!双方都在静默中进行着战前较量。我仿佛听见刀砍入狼身体的那声闷响;仿佛看见母亲手起刀落时,狼血四处喷散;仿佛已经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在乌托岭弥漫开来。
母亲高举的右手在微微地颤抖着,颤抖的手使得刀不停地摇晃,刺目的寒光一道道飞射而出,这一道道刺目的寒光居然成了一种对狼的挑衅,一种战斗的召唤。
母狼终于长嗥一声,蓦地腾空而起,身子在空中划着一道长长的弧线向我们直扑过来。在这紧急关头,母亲本能地将我朝后一推,同时一刀斜砍下去。没想到狡猾的母狼却是虚晃一招,它安全地落在离母亲两米远的地方,刀没能砍中它。它在落地的一瞬间快速地朝后退了几米,又做出再次进攻的姿势。
就在母亲重新举起刀准备抵御母狼再次进攻的间隙,狼崽突然飞腾而出扑向母亲,母亲打了个趔趄,跌坐在地,狼崽正好扑倒在母亲的身上。就在狼崽张嘴咬向母亲脖子的一刹那,也许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慌乱中母亲的左手掐住了狼崽的脖子——死死地掐住了狼崽的脖子。狼崽动弹不得,两只后爪不停地狂抓乱舞,母亲棉袄里的棉花被一团团地抓了出来。
母亲一边同狼崽搏斗着,一边在旁边的地上摸索她的砍刀。就在母亲的右手再次抓住砍刀的时候,母狼朝躲在一旁的我猛扑过来,我害怕得大叫一声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感觉到母狼有力的前爪已按在了我的胸口和肩上,母狼嘴里喷出的热热的腥味已经钻进了我的颈窝。
也就在这一刻,母亲忽然悲怆地大吼一声,一刀砍在狼崽的后颈上,刀割进皮肉的刺痛让狼崽也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
奇迹就在这时发生了。
我突然感到母狼喷着腥味的嘴猛地离开了我的颈窝。我睁开双眼,看到仍压着我双肩的母狼正侧着头用喷着绿火的眼睛紧盯着母亲和小狼崽;母亲和狼崽也用一种绝望的眼神看着我和母狼。母亲手中的砍刀仍紧贴着狼崽的后颈,她没有再用力割入,一条像墨线一样细细的东西从刀柄上缓缓地滴下来——那是狼崽的血!
母亲用愤怒而又近乎绝望的眼神直逼着母狼,那种神情似乎在警告母狼:你一旦出口伤害我的孩子,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割下你孩子的头!
两个母亲的较量在无助的旷野中开始久久地持续起来。无论谁先动口或动手,迎来的都将是失去爱子的惨痛代价。
起风了,凛冽的寒风将四周的树木吹得沙沙地响,月亮也躲进云层里,空气凝重得使人害怕!
对峙到底持续了多久,我不知道。感觉好像过了一个世纪后,母狼扭过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轻轻地放开我,先前还高耸着的狼毛也慢慢地软了下去,那闪着绿光的眼眸居然闪过一丝我只有从母亲眼中才能读到的情感!
母亲的刀也慢慢地从狼崽脖子上滑了下来,她将狼崽使劲往远处一抛,母狼马上撒腿奔了过去,对着狼崽又闻又舔。母亲也急忙向我跑来,一把将我揽入怀中,她仍将砍刀紧紧地握在手里。
母狼没有再次进攻,它和狼崽站在原地久久地看着我们,然后朝天发出一声长嗥,带着狼崽很快消失在幽暗的丛林中。
母亲将我背在背上,一只手托着我的屁股,一只手提着砍刀飞快地朝家跑去。刚迈进门槛,她便两腿一软,摔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手中的砍刀“咣当”一声摔出去好远,而她那像男人般布满老茧的大手仍死死地搂着还趴在她背上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