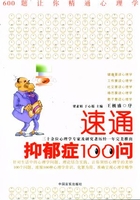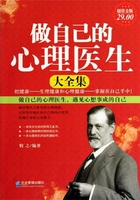首先必须要说的是,要求蒙昧人将他们禁忌的真正原因,即塔布的起源,告诉我们,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佐证了我们的假设,他们回答不了,因为真正的原因必定是“潜意识的”。但是,根据强迫性禁忌的模式(model),我们则可重新构造塔布的历史。我们必须假定,塔布是远古时代的禁忌。它们一度是从外部施于一代原始人。这也就是说,它们肯定是由上一代人强行施加的。这些禁忌一定是与人们倾心的活动相关联的。然后,也许仅仅作为由家长和社会权威所传递的一种传统而代代相传。不过很有可能,在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那里,这些禁忌“被组织好了”,成为一种遗传的心理禀赋(psychical endowment)。谁又能确定这类“先天观念”是否存在,或者确定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他们到底是独自还是通过教育来实现塔布的永久固着的呢?不管怎么说,塔布的继续存在必然会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原本的要做禁忌之事的欲望在有关的部落中,也必然是继续存在着。他们对这些塔布因而抱有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其潜意识中,他们只有触犯的欲望,但是又害怕这么做。他们正因为想做而感到害怕。恐惧强于欲望。然而,正如神经症患者一样,这一欲望对于部落的每位成员来说,都是潜意识的。
最古老以及最重要的塔布禁忌是图腾崇拜中的两个基本定律:不许宰杀图腾动物。避免与图腾氏族中的异性成员性交。
这些一定是人类最早最强烈的欲望。如果我们对图腾体系的起源和意义仍然一无所知,我们就别指望能完全理解它,或以我们的假设来验证这两个例子。可是,这两个塔布的措词和它们同时出现这一事实,将使任何对精神分析学的个体研究有所了解的人,想起一个十分肯定的东西,这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儿童愿望的中心要点和神经症的核心。
塔布的形式是多样的。因此,人们试图对它们加以分类(上文中已提及过)。但是,按照我们的命题,我们可以将它们减少到一个单位,即塔布的基础是一种受禁忌的行动,做出这一行动的强烈倾向存在于潜意识中。
我们已听说,尽管还不甚理解,任何人做了犯忌的事,即任何触犯塔布的人,本人会成为塔布。那么,这一现象又如何与下面这一事实联系起来呢?塔布不仅依附于犯忌者,也依附于处在某种特别状态中的人,依附于这些状态本身,还依附于不具人格的物体。这一危险属性到底是什么,竟能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条件下毫无二致?只有一样东西能胜任,这就是,能激起人们的矛盾情感并诱惑他们违犯禁忌的特性。
任何触犯塔布的人都会自身成为塔布,这是因为他拥有诱惑他人仿效自己的危险特性:为什么他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因此,他的一言一行都在鼓励他人仿效,他是真正的传染源。鉴于此因,他本人必须被隔离起来。
但是,一个从未违犯禁忌的人,也有可能永久地或临时地成为塔布。这是因为他所处的状态具有那种激发他人受禁的欲望和唤起他人的矛盾情感的特性。大多数特殊地位和特殊状态都具有这种性质和这种危险力量。君王或首领由于他们的特权而受到他人羡慕:人人都想当君王。死去的人、新生的孩子、月经期间或生产中的女人,因其特别的无助而激发起这样的欲望;刚刚成熟的人,因其有可能得到新的快乐而激起这样的欲望。由于这一原因,所有这些人和这些情景状态都成了塔布,因为诱惑必须被制止。
现在,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不同的人所拥有的不同数量的玛那可以彼此相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完全抵消。对于臣民而言,君王的塔布太强烈了,因为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异太大。但是,大臣或可成为他们之间的中间人而不产生任何伤害。如果我们不用塔布语言而用心理学的一般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的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如果惧怕那种与君王接触而面临的强大诱惑,也许能够容忍与他无须多么羡慕的官吏打交道,因为他的地位似乎并非高不可攀。而一位大臣只需想想自己手中的权力,也可缓解自己对君王的羡慕。因此,两个人所拥有的诱惑性魔力在数量上的差异越小,就越不会被更强的一方吓倒。
同时,我们还搞清了,为什么触犯某些塔布禁忌会构成社会危险,并招致来自社团内全体成员的惩罚并对之做出偿还。即使他们并没有全都受到伤害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用有意识的冲动来置换潜意识的欲望,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危险是真正的危险。它完全在于模仿,模仿可迅速导致社团的解体。如果其他成员不对触犯行为进行报复的话,那么他们必然会意识到自己也想以违犯者的同一方式来行动了。
我们绝不会感到吃惊的是,触摸在塔布限制中发挥着它在“触摸恐怖症”中相似的作用,虽然禁忌的神秘意义在塔布中并不像在神经症中那样,具有专门的性质。触摸是通向获得对一个人或物的控制,或者企图利用一人或一物的第一步。
我们已将塔布内在的传染力量解释成,对某种可能形成诱惑或鼓励模仿的属性的占有。这似乎与事实不甚相符,因为塔布的传染性(contagious)主要表现在它对其他物体的可传导性上,正是这种传导性使得后者也成了塔布携带者。
塔布的可传导性是对我们已讨论过的一种倾向的反映,即神经症中潜意识的本能不断沿着联想途径继续向新的物体移动。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集中到如下事实上。这就是,玛那的危险魔力与两种更加现实的力量是相对应的,即与提醒人注意自己的违禁愿望,和引诱人为满足愿望而触犯禁忌这一显然更加重要的力量相对应。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在原始心理中,违禁行为的记忆的觉醒自然与将这种行为付诸实施的冲动的唤起相联系着,那么,这两种功能就可以简约为一种。回忆和诱惑因此又走到了一起。同时还必须承认,一人违犯禁忌可诱使另一人重蹈覆辙;和塔布从一个人传导到物体上以及从一物体传导到另一物体一样,对禁忌的不顺从也会以相同方式,像瘟疫一样四下扩散开去。
如果对禁忌的触犯可用补过或赎罪的方式来加以补偿(这包括放弃某些财产和自由),那么这完全可以证明对禁忌责戒的服从,其本身便意味着对某些欲求之物的自我克制。在一个方面没有自我克制,那么在另一方面就必然会自我克制。这使得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塔布仪式中的涤罪相比较,补过是一种更基本的因素。
现在,我要对通过塔布与神经症中强迫性禁忌的比较而展示的塔布本质的方方面面做一总结。塔布是一种(由某些权威)从外部强行施加的原始禁忌,针对着人类最强烈的欲望。触犯这一禁忌的欲望存留在人类的潜意识中。遵守着塔布的人往往对塔布所忌讳的对象,抱有一种矛盾态度,归因于塔布的那种魔力的一个基本效力是产生诱惑。它像瘟疫一样作用着。这是因为违禁的前车之鉴往往具有传染性,同时也因为潜意识中违禁的欲望常常从一个物体转向另一个物体。通过自我否定对塔布触犯行为进行补过,该事实也表明,补过行为正是以对塔布的服从为基础的。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对塔布和强迫性神经症进行比较到底有多大价值?我们从这一比较中所获得的对塔布的认识又有多大的价值?这种价值显然必须取决于,我们提出的观点是否优于其他学者的观点,是否能使我们对塔布产生更清醒的认识。我们觉得,在上述讨论中虽然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观点的适用性,但是还必须对塔布禁忌及其惯用方法做更详细的解释以加强我们对自己观点的证明。
在我们面前还有另一条途径。我们可以着手探讨一下,前面所提出的从神经症到塔布的某些推论,以及这些推论的结果,在塔布现象中是否能得到直接的证实。但是,必须确定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塔布起源于由某种外部权威在某时所设置的原始禁忌的断论,显然是无法证明的。因此,我们努力要证实的是塔布的心理决定因素。从强迫性神经症中,我们对这些因素已有所了解。我们又是如何从神经症中了解到这些心理因素的呢?是通过对它的症状,尤其是对强迫性动作、防御方式和强迫性命令进行的分析性研究。我们发现它们显示出矛盾冲动所派生出来的所有征兆,既有同时与愿望和相反的愿望都相关的冲动,也有主要是体现其中的一种愿望的冲动。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奉行塔布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冲动(即受制于两种对立倾向),如果我们能够表明其中的某些征兆(像强迫性动作)同时体现了这两种倾向,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塔布和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心理共同点,这也许是它们最重要的特征。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塔布的两个根本禁忌之所以难以分析,是因为它们与图腾崇拜相关联;其他一些禁忌因具有继发的性质而不适于我们的研究目的。这是因为在这些受制于塔布的民族中,塔布已成为立法的基本形式,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目的。与古老的塔布相比,这些目的更接近现实。例如,首领和僧侣的那些塔布,完全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特权。此外,还有许多禁制(observances)我们都可以对之加以研究。从中我选择了附着于(a)敌人,(b)首领和(c)死人的塔布;我将从弗雷泽的巨著《金枝》的第二部分“塔布与灵魂的危险”(1911b)所收集的极好的例子中,选择我们的研究材料。
(一)对待敌人的方式
我们往往认为,那些未开化或半开化的民族对待他们的敌人犯有惨绝人寰的罪恶。因此,当我们发现,即使在这样的社会中,杀死一个人也是受制于塔布习惯做法中的许多禁制时,一定会惊讶不已。这些禁制很容易被分成四个部分。它们要求(1)抚慰被杀的敌人;(2)对杀人者加以限制;(3)杀人者做出赎罪和涤罪的行动,以及(4)某些仪式性禁制。由于局限于这方面资料的不完备,我们无法肯定地断论,这些习惯做法在这些民族中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性。不过,这对我们目前的研究而言,关系不大。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面前所展示的不是一些孤立的奇特做法,而是普遍的习惯做法。
在帝汶(Timor)岛,好战的远征军带着斩获的敌人首级凯旋之后,总要举行抚慰(appeasement)仪式。这些仪式特别值得注意。因为除了仪式以外,远征军首领还要被加上严厉的限制[参见下文第39页]。在远征军归来的时刻,通常都供奉牺牲品来抚慰那些首级遭割取的敌人的灵魂,“人们相信,如果疏忽了祭供,厄运必将降临到胜利者身上。”此外,仪式中还有一组歌舞,哀悼被杀的敌人,祈求他的宽宥。悼词说:“请不要因为你的头颅挂在这里而愤怒。我们如非侥幸,此刻头颅也已暴露在你的村里。我们谨向你祭奠,愿你的灵魂安息,不要骚扰我们。何必与我们为敌?一直友好相处岂不更好?如果这样的话,你也不致流血,头颅被斩。”西里伯斯(Celebes)的帕卢(Paloo)人也是如此。同样,“东非的加拉人(Gallas)打仗归来时,也在踏入自己家门前向被杀敌人的保护神供奉。”
其他一些民族则找到一种方法,将死去的敌人转变成守护神、朋友和恩人。这种方法就像博内奥(Borneo)的某些未开化的民族所炫耀的那样,在于以慈爱来对待这些割下的头颅。当沙捞越(Sarawak)的沿海迪雅克人(Sea Dyaks)在一次获胜的猎头颅远征中带着敌人的首级回来后,几个月内这颗头颅都会得到最悉心的照料。人们将用他们语言中所有的充分显示爱的名称来称呼它,并将最美味的食物,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有时甚至是雪茄,塞入它的口中。人们不断地恳求这颗头颅去恨它从前的朋友,爱它现在的主人,因为它现在已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我们将这些令我们胆战心惊的禁制视为荒唐的话,那我们是大错特错了。
北美洲的一些未开化民族会对那些遭他们杀害并剥去了头皮的敌人进行哀悼,这令研究者们吃惊不已。当一个乔克托人(Choctaw)杀了一个敌人后,他将连续哀悼一个月,其间他要受到许多限制。达科他人(Dacotas)也有类似的做法。据一位目击者说,奥萨格人(Osages)悼念自己死去的人。“而对于敌人,他们也是把他当作朋友来哀悼的。”
在我们继续讨论与敌人有关的其他的塔布习惯做法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条明显的不同意见。弗雷泽和其他人的一些观点都有可能被引用来反对我们,认为这类抚慰仪式的动机最简单不过,与“矛盾症”毫无关联。这些民族被那种迷信于敌人鬼魂的恐惧控制着。这是一种在古代就有的恐惧,英国大戏剧家曾在《麦克白与理查三世》一戏的幻觉中,将这种恐惧展示于舞台之上。从逻辑角度而言,所有这些抚慰仪式,包括马上要讨论的种种限制和赎罪做法,都是这一恐惧的产物。这一观点得到塔布的第四类习惯做法的支持,而这些做法只能被解释为企图驱赶掉萦绕着杀人者的死者的鬼魂。此外,这些未开化的人们公开承认对所杀敌人鬼魂的恐惧,他们自己也承认塔布的那些习惯做法(我们将要讨论)也都是出自这种恐惧。
这一反对意见确实很明确,如果它能解释一切的话,我们倒可不必烦神再做进一步探讨。我想这个问题可以放一放,现在先来提一下与之相左的一个观点,它来自我们在前面关于塔布讨论中所做的假设。从这些禁制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指向一个敌人的冲动并非总是充满敌意的,它们有时是懊悔、对敌人的钦佩和杀了这个人之后的良心谴责的具体体现。我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观念,这就是,早在神赐予任何法典之前,这些未开化的野民已具有一种维持生存的戒律:“不可杀戮”,任何冒犯必遭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