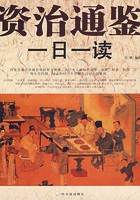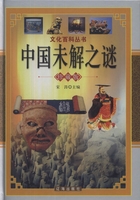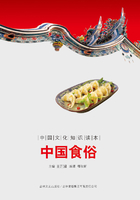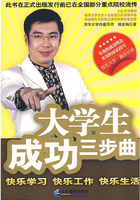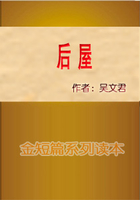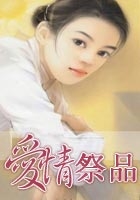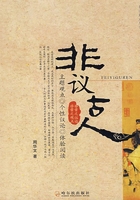知情者出面作证,人们总是希望他所说的都是真话,不掺任何水分。
许多接触过中国人的知情者,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是很少有人能抛却个人情感,如实地叙述,更不用指望他们讲出全部事实。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博学,都不可能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情。所以,本书里的观点,必须坦然面对来自三个不同方面的异议。
首先,有一种观点说,如果谁试图把他所知道的有关中国人的特性如实地转述给其他人,那么他将白费力气。
1857年至1858年期间,伦敦《泰晤士报》的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是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像当时所有到中国去的作家一样,有机会观察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且能够借助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的观察,获得对中国人全面、正确的理解。然而,库克先生在他书信集的前言中,对他描述中国人特性的失败表示了歉意。
在这些书信里,有一个重大的疏忽,就是关于中国人特性的文章,我写得不够精彩。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的诱惑力,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让人施展才华的机会;精巧的假设、深刻的概括、自信的断言,都可以在其中充分展示。所有的批评家,肯定会断然地蔑视我,因为我没能利用这样的机会,总结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事实上,我写过几位中华民族中很出色的人物,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写这些文章的同时,他们曾有过的言行的粗俗,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为了真实起见,我连续烧了好几封长信。而且,我常和最著名的汉学家谈论这种事,发现他们和我一样,很难形成对中国人特性的整体概念。
当然,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才能遇到这种困难;一个八面玲珑的作家,对所写的主题可能一无所知,却可以轻易地写出一篇辞藻华丽的文章,以两个客观事实、头头是道地加以分析论述。某一天,或许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必要的知识,对中国人的矛盾心理,能够做出全面、准确的分析。目前,我避免严格的定性,用中国人具有的特殊品性去描述中国人。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可以看出,中国人是不能被征服的;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又不是易被理解的。要想真正地了解中国人,除了中国人,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与中国已经交往了几百年,那么,我们就应该像认识其他复杂现象的秘密那样,真正认识中国这个国家。
其次,一个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我不具备写这本书的资格。就算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也并不能保证他有能力写书论述中国人的特性,正如一个人在银矿工作了二十二年,并不足以证明他能写一篇关于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
中国幅员辽阔,一个人只是在其中几个省居住,考察过的省份不到它的一半,当然没有资格对整个国家作出概括。需要声明的是,这些文章最初只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写的,并没想过要更广泛地传播。然而,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才应邀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
最后,是一些人提出的,认为阐发的部分观点,尤其是涉及中国人伦理特性的看法,很容易让人误解,作出错误的判断。
然而,人的印象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做到分毫不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种印象就像是相片的底版,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可是每张都可以真实地映现一些图像,是其他底版无法呈现的。相片的底版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剂又不同,其结果当然也不可能相同。
对中国的了解,我远不如那些久居中国的人,但是,他们与我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也理应同样受到尊重,他们认为,在某些部位增加一些明亮的色彩,可以使过于单调的画面更为逼真。考虑到这些正确的意见,我对原文作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然而,由于出版的急迫,原本讨论中国人的特性有三分之一被省略了,只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写了“知足常乐”一章。
要想拒绝赞美中国人所具有并表现出来的优点,我想不到任何理由;同时,又存在着另外一种危险,即屈从于既定的思维框架,给予中国人超过实际道德品行的高度评价——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由此,我们联想到威廉撒克里(1811—1861,英国小说家),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蠢的,坏人却是聪明的。
对于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讽刺家回答说,他有眼无心,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有一幅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中分辨出一个画面——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侧身像,抱臂低头站着的样子。但是,长时间注视之后,往往一无所获,似乎其中有什么差错,而一经人指点,就会感到,在画面中看不出拿破仑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许多事情在中国每一次出现,人们往往视而不见,而一旦看出,就难以忘却。
读者需要注意,正像一个限制性的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一样,不要以为本书的文章概括的是整个中国,也不要以为是外国人观察和体验的全面荟萃。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所得印象的记录,是许多“中国人特性”中的一小部分。它们不是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画,而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见闻,用炭笔勾勒的一些民族特性的素描。图像仅仅是由单线构成,无数单线交织在一起,才形成了完整的白色光幅。它们是来自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的个别经验的汇集,是一种归纳研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论题得到了如此广泛的例证。
梅多斯先生,众多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一位,他认为,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特性有了正确的看法,并想把它告诉他人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笔记交给他,让他细读。这些笔记详细地记录了引人注目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常事件,并且还附有当地人对该事件的看法、说明。
一般性的结论都是从大量的事例中推出的。这些结论可以被怀疑或否定,但是所列举的事例却不能搁置一边,因为它们是绝对真实的。任何关于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要参照这些事例。
试图拿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属于日耳曼民族,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一支,5世纪和6世纪居住在英国)进行比较,那是非常困难的。显然,许多看起来是“中国人特性”的东西,纯然是东方人的特性。至于对与否,读者在看到这样的情况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作出自己的判断。
很多人认为,在当今,我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要想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三条途径: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无疑,这些知识来源是有其价值的,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条途径,比前三者加起来还要有价值,那就是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生活,不过这个来源并不向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就像对于一个区域的地形,在农村比在城市更容易弄清楚一样,在农村更容易了解人们的特性。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十年,关于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可能还不如在农村住上十二个月获得的多。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乡村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而本书就是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写成的。
这些文章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以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观察者的角度,如实报告其所见所闻。由于这个缘故,本书没有作出中国人的特性可以由基督教进行改善的假定,并不猜想中国人是否需要基督教,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去纠正这些缺陷,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问题”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认为,在20世纪,这一问题会变得更为紧迫。任何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对于如何改善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问题,都充满了兴趣。如果我们得到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将会得到对曾被忽视的一系列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话,无论得到怎样的支持,都将不能成立。
埃尔金勋爵对上海商界的答问,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他的话至今仍然是正确、恰当的。他说道:“当阻挡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可以自由进入的时候,西方基督教的文化将发现它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存在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不过,在其他方面,又不得不让我们同情和尊敬。在即将出现的竞争中,在这个有着怀疑态度而又聪敏的民族中,基督教文化要想找到立足之地,所凭借的方式,就是宣传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相比,在公共和个人的道义上,能得到更好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