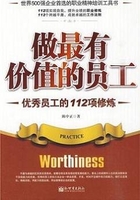中国人很能适应环境,并以此为满足,他们并不太讲究舒适与方便。当然,我们这么说的标准依照的是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我们现在要谈论的,是在所谓舒适与方便问题上,东西方人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
首先从中国人的服装说起。在前面曾谈到中国人轻视外国人时,一方面就是因为西方人的服装样式,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中国人的外观打扮,也会令西方人很难接受。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有这样一种打扮,即把前半部分的头发剃光,让本来应该得到保护的部位暴露于外。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种削发方式,是中国人在刀尖之下被迫采取的,并以此作为忠于皇帝的标志。既是如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削发方式,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舒适,而且或许再也没想过要改变样式。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中国文明有许多不可理解的现象。据说这个民族起先是游牧民族,按理说,他们在毛纺技术方面应该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他们却不懂。虽然有一个特例,即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一些毛纺业,但是这一技术并没有被普及,我们看到的还是漫山遍野的羊群。
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这里的人们是用灯心草一类的植物纤维做衣服的。现在,整个国家完全是用棉花织成布来做衣服。在有些地区,冬天异常的寒冷,人们就不得不穿好多件衣服,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一个小孩要是摔倒了,常常爬都爬不起来,就像掉进了一个桶里。但是,我们从没听人抱怨过,穿这么多衣服很难受等诸如此类的话。我们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不愿意忍受这种束缚的,无论如何都会想方设法摆脱它。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们没有、也不穿任何的内衣。虽然对我们来说,不能没有那种可以经常换洗的棉毛内衣,但是中国人从没想过这种需要。他们为了对抗寒冷,用很多的衣服裹住身体,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么穿衣服不舒服,但是他们也不是特别在意。我们曾经给了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一件内衣,告诉他每天都要穿着,就不会受寒了。但是一两天后,我们发现老人又把它脱掉了,因为他都快“热死了”。
中国人穿的鞋子是用布做的,经常会渗水变得潮湿。如果天气冷的话,脚底板整天都暖和不了。当然,他们还有一种防潮的靴子,是上过油的,但价格相当昂贵,很少有人用得起。雨伞也是如此,在中国人眼里,都是奢侈品。让雨淋湿的人,很少会把衣服换下来,而是很自然地让身体来焐干。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手套很好,但自己却没想过要用。即使在北方,那种不灵便的连指手套,也是难得一见的。
最令外国人烦恼的是,中国服装居然没有口袋。一般情况下,外国人希望衣服上有许多口袋可用,外衣胸前的口袋装记事本,下面的口袋装手绢,衬衣的口袋放铅笔、牙签、怀表之类,其他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皮夹子。外国人把经常用的东西放在身上,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像小梳子、折尺、开塞钻、靴扣、镊子、指南针、小折叠剪刀、弹子球、小镜子和自来水笔等。
中国人就不同了,他们几乎没有用到过这些东西,就算要用,也没有口袋放。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会把手帕塞在怀里,即使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你把重要的文件交给他,可就要担心了,他会把文件塞在绑腿里,虽然上路前他认真地扎紧了,但是,带子在不知不觉中会变松,文件也常常会丢失。如果身上还要带其他的东西,他们一般就把东西放在卷起的长袖里,或帽子的某个地方。
在中国人身上很难找到放小东西的地方。他们会把钱卷成小筒夹在耳朵上;钱包、烟袋、烟杆一类的东西,就系上带子挂在腰带上;钥匙、梳子、古钱系在外衣的纽扣上。人们要异常地小心,稍不注意,这些东西就会丢失。
在照顾孩子方面,知识也严重匮乏。他们不知道婴儿对温度的变化异常敏感。不但不注意给婴儿盖好被子,甚至还经常掀开被子,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孩子。从这些无知的做法中,我们就可以了解、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为什么许多中国婴儿满月之前,就会死于因突然受寒而发作的惊厥。
当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在中国的有些地区,人们用一种沙土袋代替孩子的尿布。这对于西方的母亲来说,想想都会惊恐万分。这些可怜的孩子吊着一个沙袋,就像青蛙“背”着一个铅弹,根本不能动弹。至今,在这种做法流行的地区,如果一个人没有实际经验,还会被人们说成是没脱掉“土裤子”。
中国人很能将就,不仅表现在服装上,在住房上也是如此。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且不去说那些没房子的穷人,来看一看有房子的中国人。他们似乎不愿意在房子的四周种些树用来遮荫,而是喜欢搭个凉棚。即使不搭凉棚,他们也不会去种遮荫的树,而是种些观赏类的灌木。酷暑来临,院子里热得受不了,他们干脆坐到街上去。实在不行,就回到房间里去。大多数的房子没有北门,只有南门,因而空气无法形成对流,屋里不见得有多凉快。如果问起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时,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我们的房子从来就没有北门!”
在中国的北方,人们一般都是睡炕。炕是用砖坯垒起来的,可以在中间烧火加热。外国人很难适应这种炕,如果没有烧火,炕就会很凉;如果火烧的太旺,后半夜的时候会被热得睡不着。不管怎样,炕的热度是不可能一夜都很适宜的。此外,由于材料的原因,这种炕还会生虫,即使每年都更换砖坯,这些不受欢迎的家伙也不会消失,因为整个房间的墙上早已都被它们占据了。
害虫会传播疾病,这是许多中国人都知道的,但是,却没有人去防治这些害虫。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许多人家的墙角上都挂着蜘蛛网,没有人打扫。对于苍蝇和蚊子,中国人更宽容,它们闹得太厉害时,就烧一些有香味的草驱赶它们。
睡觉用的枕头,在东西方的舒适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枕头是用来支撑头部的,是一个装着羽绒的袋子;在中国,枕头是用来支撑颈部的,或者是一张小板凳,或者是一截木头,或者是一块砖头。如果以中国人的方式枕着中国人的枕头,那无疑是在受折磨。同样的,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所使用的枕头上睡十分钟,这是肯定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中国人不懂毛纺技术,不仅如此,他们对家禽的羽绒也不感兴趣。中国人不知道羽绒可以制成被子,任羽绒随风飘走。他们只知道羽绒可以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是把羽毛扎起来做成鸡毛掸。在中国西部,为了保护刚出芽的麦子和豆子不被动物吃掉,家禽的羽毛被随意地、厚厚地散布在地里。
对西方人来说,最好的床要数钢丝床,坚固而且有弹性。但是,中国人的观点显然不同,当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添置了这种床时,竟使得置办这些用品的医生失望了,居然有病人宁可躺在地板上,也不愿意睡在床上,因为他们觉得躺在地板上就像在家里一样舒服。
中国人居住的房子,一到了晚上就会变得异常昏暗。人们一般都不点煤油灯,绝大多数地区还是按照惯例,一直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点灯,这种灯的光非常暗,仅仅能照见东西,但是他们似乎很满足,根本就没想过进一步看清东西这种更高层次的追求。
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家具既笨重又丑陋。中国人坐的长凳没有靠背而且很窄,如果凳子的某条腿不牢固,或者凳子的一端没坐人,那么坐下去的时候,凳子就会翘起来。在亚洲各国,中国是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当然在我们眼里,也是相当难看的。其中有一种椅子很高,靠背很直,好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所流行的式样。还有一种比较常见,椅子很大,足以坐一个大胖子,但是看起来不够牢固,很容易垮掉。
中国人居所的潮湿和冷,是西方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房间的地面用泥土或铺设没烧制好的砖,既不舒适,对健康又不利。还有,房门也是松松垮垮的,两扇门根本就关不严,四周都透风。即使只有一扇门,而且也用结实的纸把门缝糊好了,也还是不能抵挡住刺骨的寒风,因为中国人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曾有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请随手关门”,但是,这在中国纯粹是一句废话,因为没有人会那样做。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即人们进门的时候通常都要低头,因为不管是房子还是院子,门框都做得非常低,不那么做的话头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的窗户一般是用纸糊的,抵挡不住风、雨、太阳、炎热或灰尘的袭击。我们使用的百叶窗在这里不常见,就算有,大概也没有人用。
中国人的家里通常只有一口容量很大的大铁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每次只能煮一种东西,煮饭的时候就不能烧水,而且,还必须有一个人蹲在灶口不断地往灶膛里添柴草。每次煮饭的时候,水汽和烟弥漫整个房间,外国人往往被呛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但中国人似乎是无所谓的。
对西方人来说,冬天没有暖气,是中国人住所的一大弊病。中国大部分地区,取暖只是靠做饭的锅灶和炕,即使冬天特别寒冷的地区也是如此。对于炕的舒适,中国人是充满了高度的赞扬,对西方人来说,恰恰相反,他们喜欢的是适宜于人体的恒温,而不是凉或热得让人睡不着。在寒冷的夜晚,中国的炕远不如“壁炉”或者火炉来得舒适。
就全国范围而言,在有限的产煤地区,煤已经开始作为燃料在使用了,但是在烧煤时,煤烟总是在屋子里出不去。即使家境很好的家庭,在木炭的使用上也非常节省。但像烧煤一样,存在着隐患,用时必须要很小心。
在寒冬腊月,即使待在家里,人们也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因为屋子里实在冷得难受;外出的时候,就没衣服可加了。如果问他们:“你冷吗?”他们的回答总是:“当然冷!”在冬天,他们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河水一样,只是底层在缓慢地流动,表层全都冻结了。一辈子就从来没有暖和过,这就是他们留给西方人的印象。
对于一位中国道台的话,我们曾经很惊奇,他说:美国的监狱甚至比他的衙门更舒适。现在知道了中国人住所的样子,就可以理解他的话了吧。
拥挤和噪声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前面我们也曾提到了。天气冷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会挤在一起取暖。就是在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轮船上挤满了人,或坐或躺。任何西方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拥挤,我们喜欢独门独户的房子,既通风又不被打扰。
中国人似乎并不在意,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条件,既凉快又安静的居住环境,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在中国,我们经常看到在城市的周围,建着许多小村落,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地价太昂贵了,大家不得不挤在一起。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都挤在一起,才抬高了地价。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了,狭小的院子、拥挤的房子,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活动的空间。
在中国,一个小客栈的牲口棚里,有五十头驴,那是很正常的事,而且整个晚上都会有你想象不到的热闹。一位外国旅行者夜宿在小客栈里,兴致勃勃地看着大队人马的到来。可是,到睡觉的时候,同屋住的中国旅客已经熟睡了,而一大群骡子发出的咀嚼、踢腿和长叫声,让他根本无法入睡。
哈克先生说,中国人知道要让牲口不乱叫,在它的尾巴上吊一块砖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人这样做,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并不在乎牲口是否在叫。中国人并不在乎动物的吵闹,这是中国人的天性,并不局限于某个阶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知道曾有一位中国大官的太太,在家里养了大概一百只猫,这个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没人看管的狗到处乱跑,这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会见到,中国人对此熟视无睹,或者是受佛教讲的不能杀生的影响。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罗斯·布朗先生,出版的一本有关东方游记的书,其中有一幅名为“君士坦丁堡大观”的插图。画面中有各种各样的狗,正在举行一个会议。书中同样有一些很能反映中国许多城市概貌的插图。
尽管常会发生被疯狗咬伤的事,人们似乎也不会太担心,也没有什么感觉,一大群狗仍是爱怎么叫就怎么叫。我们有一句谚语:“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的毛治疗”,这充分地体现在了中国人的身上,他们一旦被狗咬伤,往往只是在伤口上敷一些狗毛了事。
上面讲了这么多的事例,都是在讲中国人对舒适的态度,即不在乎。同样,中国人对是否方便也不关注,看下面几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也一直以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骄傲。中国文人的书房里一定会备有“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但是,这四件写字、作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当人们在外需要用到的时候,很难找齐它们。就算都备齐了,还必须有水来研墨,当然,还要知道怎么样把笔毛弄软,否则还是不能用,如果把笔弄坏了,那就更浪费时间了。中国人没有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即使有,也不知道怎么用,他们既没有削铅笔的小刀,也没有衣袋用来装笔。
在西方国家,如果住在高级宾馆里,不仅会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可以享受到各种服务,像提供冷热水、灯光、供热或其他一些宾客想要的服务。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是最好的旅店,也只是口头上说得好,但是客人需要的服务却很少能达成。客人需要什么时,往往要到房门外大声喊叫,希望店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提供他们一些服务,但大多事与愿违。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是想用就能买到的,因为这些都只能从卖货的小贩那里买,而小贩什么时候来是没有固定时间的。在城里,人们晚上行路要打灯笼。即使像这种几乎天天都要用到的东西,在有的城市,也只能从那些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买到,就像我们向小贩买牛奶或鲜酵母一样。
在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很小,买东西非常不方便可能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譬如说,有的地方,人们习惯于二月份卖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从这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卖掉;如果卖不掉,就又拖回去。如果一个缺乏经验的人,不假思索地希望在五月份买到木料,他将很快明白一位东方智者说的话:“在这个世上,机会只有一次”,因为他根本就买不到。
在谈中国人的节俭特性时,我们说过,中国人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成品,顾客买一些部件,需要再加工,按自己的想法进行组装。当然,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不方便的事。
我曾经让一个佣人去买把斧头,劈柴用。市场上没有,结果他带回的是十四个(进口的)大马蹄铁,然后请铁匠打成了斧子的头,再请木匠安了一个柄,合计下来,整个斧头所花的钱比买一把外国的好斧头还要贵得多。
在中国一些不方便的事情中,给西方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缺乏卫生设备。譬如在北京,如果你试图把排水系统治理一番,那么,新产生的问题比你计划治理的要多得多。一个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不能给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找到答案:在中国,哪个城市是最脏的?
一位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外国人,到南方访问,对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感觉上比北方的城市要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横贯游览了厦门,结果发现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干净——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而言。
出于对居住地的嫉妒,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说:“事实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刚下过了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游览福州的时候,这位旅行者认为发现了中国最糟糕的城市。到了宁波,情况也是如此,到了天津,情况还要更糟。最后,无须奇怪,他公正而诚恳地收回了他对北京的看法,因为南方比北方更糟。
在讨论中国人缺乏公心时,我们已经谈过其道路状况。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公路,窄得只容一辆车子通过。在这条路的两端,分别有人把守,上午允许朝某个方向行驶,下午允许朝另一个方向行驶。
无论什么时候,一下雨,中国人就只能待在家里了。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尤其是他们的鞋子——是不防水的。中国的道路,我们也已经知道,下雨就满路泥泞。在西方,碰到下雨天就不出门的人,我们称他傻瓜,而在中国,碰到下雨天不待在家里的人,才被称为傻瓜。
“等雨停了再说”,这是中国人的言语中最常用的一句话。除了政府部门,对其他人来说,活动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紧急的公务,也战胜不了遇雨就停的惯例。
我们确信,从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出来的水柱,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驱散气势汹汹的人群,这是一位外国人在中国看到的事实。橡皮子弹也不会这么有效果,因为人们会捡拾废弹头,然而对于冷水,就像猫一样,自汉朝以来的每个中国人都怀着厌恶。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泼冷水都被看做是致命的。
中国钱币这个话题,不仅可以写一小段,而且能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书。其中的混乱和古怪,足以使西方人发疯。
在“漠视精确”那一章中,我们已经谈过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比如说,一百钱不是一百个铜钱,一千钱也不是一千个铜钱,而是其他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一个钱可以当两个用,二十个可以当四十个用。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听说对方要给他五百个铜钱,他明白将收到的只能是二百五十个,或者更少,不同的地区还会有所变化。
商贩之间因为钱的事经常会发生争吵,因为在钱中,常常会混入小钱或是假钱。地方官吏也为钱的贬值烦恼,不定期地颁布文告,打击这些掺假行为。可是这样做,又给衙门里的污吏创造了机会,对本地区所有的钱庄加重税收,因而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钱币一时匮乏,物价就会立即提高。资源很快枯竭——却没有取得任何效益——回收的是伪币,而价格并不降低。于是,质量较好的货币换成了较坏的,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瞬息不停地逆转。
货币的状况越来越坏,以至于像河南省的有些地方,人们上市场去,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普通的好坏掺杂的钱,另一种完全是假钱。有些东西只付给假钱。至于其他贵重的商品,就要付两倍的价钱,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
银锭在交易中的损失总是很大的,用银子的人,不管是在买还是卖,都不可避免地会受骗。如果使用钱庄的银票,麻烦也不少,因为一个地方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方,或者完全不能通用,或者要大打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即使他去开出银票的钱庄兑现,也很可能要与钱庄的贪心人发生一场争斗,因为他们是不会付给与原款质量相同的钱币的。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不佳的环境下,中国人竟然能照常做生意。迄今为止,据我们观察,他们对这些烦恼已经习惯了,几乎不感到是什么负担,对此叫苦连天的只是外国人。
在经过中国的村庄时,外国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头驴伸开四蹄躺着,一条结实的缰绳绑着它的脖子,拴在一根木桩上。但是缰绳不会合乎驴的身长,驴躺下的时候,缰绳就显得过短,它的头被吊起了四十五度角,看上去脖子似乎要脱臼了。让我们很疑惑的是,缰绳这么短,它为什么不挣扎呢,反而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我们确信,外国的驴决不会这样。
看过我们的论述之后,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看法: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却似乎自我感觉很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标准来说的,而与我们的标准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我们开始时所提出的命题。中国人已经知道怎样去适应自己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会以极大的耐心去默默忍受这不可避免的困难。
时代在变,我们也随之改变。相反,在中国,时代没有变,民族也没有变,舒适和方便的标准,现在和几个世纪前是一样的。但是,只要有新情况出现,这些标准也必将改变。我们已经习惯的标准,他们同样也将具备,这既不仅仅是希望,也不仅仅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