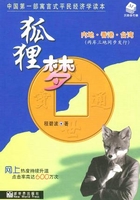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在练习眉来眼去贱法,所以仍旧沉浸在即将成为母亲的欣喜中。
我预产期是七月十日,于是在六月便请了产假,决定回C市生产。一来父母亲戚可以帮忙照料月子,二来医疗环境也较F市好些。
而自从我回到C市后,董承业以和我父母住不方便外加工作繁忙为由,只回来看望了我一次,后来直到我进了产房,他才匆匆从D市赶来。
七月十日中午,我产下了女儿。
第一个想法是:谢天谢地,终于卸货了。
第二个想法是:哇靠,为什么我孩子丑得跟泡发的猴子似地?
第三个想法是:算了,我们俩长得都不咋地也别怪孩子了。
我生产后在医院住了七天,董承业在医院时的表现便有些异样——他手机不离身,时常推着女儿去走廊玩耍,好半晌都不回来。离婚之后,我姨妈才回忆起来,说有好几次都看见他推着婴儿在医院角落打电话,看见她靠近就马上把电话挂断。
七天之后,我和孩子出了医院,董承业也以工作忙为借口迫不及待地回到了D市。
小猴子从出生后就开始吐奶,喝多少吐多少,时常看见她喝完奶后睡得正熟忽然一阵猛烈咳嗽后接着一股白色奶柱从她嘴里如抛物线般喷出。唯一的办法便是在喂奶后将她抱起,拍抚一个小时后再放下。但是新生儿大概每隔两三个小时便要喝次奶,所以大人基本无法歇息。那段日子全家都是处于兵荒马乱之中,我即使在月子里也无法保证睡眠时间,每天累得坐着都会打瞌睡,所以便完全忽视了董承业的异样。
而董承业却在这种时候跟我商量说要用结婚时收的礼金来换车。
是的,他打来电话没有询问孩子近况,没有询问我的身体,只是为了让我把礼金取给他换车。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董承业变了。
以前的他很喜欢小孩,可以耐心地照顾别人家的小孩一下午。而现在,他却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
我们发生了争吵,他挂断了电话,我再打给他,他却始终不接。
那是我生产完后的第十天,他开始与我冷战。整个月子期间,我哭了三次。月子没坐好的结果就是生产前我的身体壮得跟头牛似地,生产后免疫力迅速下降稍稍疲倦点便会感冒发烧。
也是那时我确切地明白了那句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男的入错行最多是没钱没老婆,女的嫁错郎一不小心便会没了命。
后来我坐月子快结束时,董承业父亲听闻他不回家的消息,打电话训斥了他,他不情不愿地回来了。当时婴儿床摆在客厅,他进门后只看了眼女儿便直接进入卧室玩了半小时的手机游戏。
我那颗小心脏,又再次变得拔凉拔凉的,跟在冰箱下层冻了一晚上似地。
这一次,再也没回过暖来。
隔天我和我妈让他开车带着女儿去儿科医院看病,C市的儿科医院位于闹市区,只有在距离医院一公里处才有地方停车。而到了那,他却让我们自己下车,他坐车上等我们。
四十度的高温里,我和我妈背着大包尿不湿奶瓶抱着女儿爬着上坡去医院,走到半途我想起什么,便给董承业打电话,他那边却一直占线。远远望去,驾驶室里的他微微偏着头,很温柔地拿着电话在说着什么。
当时的我没有上前,只是本能地抱着女儿转身往医院走去。
后来回想起来,其实那时的我潜意识里已经明白了些什么,却不敢去证实。
当天晚上,我妈在客厅询问卧室里的董承业明天会否在家中吃饭,如果要,她就去买点好吃的。而本来便是坐立不安的董承业听见这话忽然烦躁起来,低声埋怨说:“为什么每次都问,难道我不回家你们就不吃饭?”
随后他站起身来连招呼也没跟我父母打便提起包很生气地走了。
我当时怔住了,那种茫然感就如同正喜滋滋走在路上忽然有人窜出拿着根木棍对直你脑袋打了一棒。
之后,我始终在琢磨我妈的那句话到底是哪里踩碎了董承业的玻璃小心肝,琢磨得死了好几摊脑细胞后终于顿悟——自己真他妈傻逼,哪里是惹到了,人家就是想找个借口装作生气溜走呗。
待我回过神来时,董承业已经冲下了楼,那速度快得,跟后面有人追着爆他菊似地。
我也不顾一切地冲下了楼,想去拉住他,可他却开着车扬长而去。我追了很长一段路,他从后视镜中应该能看见我,但他却像是躲避瘟疫般逃走了。
当时是夏天夜晚,我因为还在月子中,所以裹着头巾穿着长袖长裤睡衣。其实我平时是个很作的人,下楼打瓶酱油都不肯穿拖鞋。而那一天晚上,我就穿着这样怪异的服装在众人诧异的目光里追着我丈夫的车,而我的丈夫却连一眼也不愿看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自尊,都被践踏得支离破碎。
我拼命地拨打董承业的电话,他终于接起。
我情商低,说不了几句就暴躁了:“你还想不想过日子!”
他性子也不好,说不了几句便咆哮了:“我就是工作忙,你能不能理解!你他妈像个泼妇一样追车做什么!”
我忽然悲从中来,哭道:“我刚生完孩子,我整天辛辛苦苦带孩子,我……”
他没有待我说完,很冷淡地抛出一句话:“每个女人都会生孩子,每个女人都会过这一关。”
那瞬间,我感觉到了冰冷,无休无止,无边无际。
我对着电话那头说了五个字:“我们离婚吧。”
那边传来漫长的沉默,在沉默中,我的呼吸被拉扯成了细长的线条,抵在我们过往美好回忆的咽喉处。
“好。”他说。
然后,美好回忆被割断脖子,鲜血淋漓。
挂上电话后,我独自坐在楼梯口,哭得快要断气。我觉得这段时间经历的事像是噩梦,而我像是站在一个木桩上,下面遍地尖刀,稍不留神便会被穿肠破肚,不安感充溢全身。
生产完后,面对自己臃肿的身材,面对自己小腹上丑陋的疤,面对自己素面朝天的脸,我的自信心低到了谷底,捞都捞不起来。
我向来是比较清高骄傲的一个人,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心里却升起了这样一个念头——董承业不要我了,那么还有谁会要这样的我?
我像是一只弃犬,彷徨迷茫。
可惜我没有多余的伤感时间,我妈打来电话,不是叫我回家吃饭,而是让我回家喂奶。
我听见了电话那头小猴子饿得直哭的声音,说也奇怪,平时我是那样多愁善感没事便悲春伤秋的一个人,可这时却狠狠地止住了眼泪。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我得对小猴子负责。
这件事闹得挺大,很快来了位调解员——杨蓉。
杨蓉的丈夫白洪文是董承业的同学,因为我们四个人年龄差不多,所以在我怀孕前关系都很好,时常结伴出去游玩。
杨蓉弱质纤纤,然而却很精干,做得一手好菜,将家里打理得有条有理,她算是我心中贤妻良母的楷模。
杨蓉赶来C市看我,听完我的诉苦后,斟酌地道:“洪文也打电话去骂了董承业,但那小子不知怎么的,自从去了D市后,越来越不听洪文的话,我们都觉得他整个人都变了。”
我抱着小猴子,只觉得无力。
杨蓉看我一眼,欲言又止:“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方为夫,你月子也坐完了,干脆就回F市吧,他不是说嫌这里不方便吗?那回你们自己的家总方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