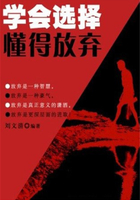果儿和桃儿正准备睡了,就见那窗纸上映了一个长长的影子。
以为是王婶有事要嘱咐,忙又穿上了鞋,嘱咐桃儿先睡,开了门就出去了。
出去了,才知道站在窗外的是洛心。
洛心本打算回屋的,可见想着的人出了来,忙轻步走了过去。
“明天我又得回镇里了,有事就去书院找我,知道吗?”有些不放心的细细嘱咐道。
果儿应声点了点头,有些别扭的回避那关切的眸子。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矫情了,连着脸上都觉得有些发烫。幸好是在晚上,不然得丢死人了。
感受到了她的忸怩,洛心心里的担忧竟也消失了,宠溺的又揉了揉那脑袋,将袖中的一个袋子放到了她手上。
果儿立马想掏出来看看,却被一只素手给钳制住了,忙尴尬的想要抽手,可身体像是不听使唤一般,一动不动。
“等我走了再看”洛心收回了手,俯身柔声道。
果儿低着头,木木的点了点,只觉得脸上烧的厉害。
她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躺到床后久久睡不着。直到后半夜,听到打更的鸡鸣,才迷迷糊糊的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牧儿和洛心带上了王婶准备好的早饭,就乘着村里的一辆牛车走了。
果儿起床时就见桃儿苦吧着脸盯着她。
“怎么了?”迷糊糊的拽起一边的衣裳就往身上套。
“已经快中午了,一直叫不醒你……”
“什么?”果儿不淡定了,唰的一下就跳下了床,趿拉着鞋就往外跑。
这下完蛋了!
等着跑到苏府清苑时,院子里那站了两排的人齐刷刷的全都盯着她。
果儿尴尬的笑了笑,放慢了步子。可这么一慢下来,院子立马一阵哄笑。连着那站在前面的苏管家都忍不住抖了抖胡子。
果儿只觉得莫名其妙,目光投向杜鹃似是询问。
杜鹃抿着嘴,憋着笑指了指自己的衣襟。
果儿愣了愣,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这一看,才知道自己的衣裳穿反了,还把那里衣的带子和外衣带子给系到了一起。
淡定的拉了拉衣裳,一步步走去了边上的换衣房。等到了屋里,猛地关上了门,自己也无奈的笑了。
清苑假山亭子里,苏竹笑的前俯后仰,只差在地上打滚了。
苏澈微搭着眼眸,面上毫无波澜,只是那高敲的嘴角出卖了他。
果儿刚换好丫鬟的统一服装,杜鹃就来喊了,说是主子让她过去伺候用饭。只得爱不释手的将那碧绿的簪子又塞进了袋子里。可又觉得想再看看,干脆就直接插进了发髻,加快了去书房的脚程。
听见敲门声,苏澈本想晾她一晾,可一想那天某小人直接靠柱子在外面等的行为,立马改了主意。
“进来!”
深知自己今天理亏,某女老实的轻轻开门,又轻轻关上了门,垂着脑袋,轻步轻脚的来到了书桌前。
苏澈慵懒的依旧半支着脑袋直直盯着她,目光在她身上不住徘徊,直到落到那翠色簪子上,修眉微皱,眸中沾染着怒意。
“昨晚做什么去了?!”陡然起身问道。
果儿原本在构思着各种迟到的理由,却不想没对上问题,微愣道,“啊?”
抬起了头有些疑惑的对上了那双隐隐怒意的眸子。
苏澈快步迈到了桌前,顺手拔下了那有些碍眼的簪子,勾唇道,“不想着赚钱赔我瓷器,倒想着臭美了!”
“给我!”果儿踮脚就去逮那只手,却不想身高差异有点大,怎么也够不着。只能顺势踩上那双大脚,一双手勾着那脖子往上攀。
苏澈高扬着手,看着那吊在自己身上如树袋熊的女人张牙舞爪垂眸微怔。
“下去!”
“还我簪子!”某女毫不示弱的抓紧了担在某人脖子上的两手,瞪着眼眸。
看那张小脸上铮铮劲骨的模样,一双冰冷的眸子竟染上了水色,本就上扬的眼梢挑了一抹魅惑的弧度,惊艳绝代。
“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投怀送抱?”
果儿盯着那张脸一瞬的愣住了,可听到那满是戏谑的调子立马又回了魂魄,嘴角弯了一弯,笑意灿然。想用这招对姐,可惜用错人了。
欺近那脸,对着那嘴角“啵”了一口,“乖,给我。”
就在那张脸完全石化的时候,踩着那脚一个助力,伸手捞下了那簪子撒腿就跑。
她不可傻,等着那妖孽回过神来不把她剥了才怪,她要先避避风头,等那妖孽过了劲再出来。一个大男人被一个丫头给非礼了,说出去谁信啊,更何况还是他们那貌若神祗,冷若冰霜,拒人千里的妖孽主子!
想想刚才某男那冰冻了的脸,果儿心里还真是畅快啊!让她伺候起床,让她伺候用饭,好啊,来吧,尽管来,咱随时恭候!
就在某女幸灾乐祸蹦逃的同时,某回过劲来的男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被那丫头给非礼了?堂堂叱咤阑启的世子爷被一个乡野丫头给吃了豆腐,豆腐。
果儿在后园的假山下窝了一下午,也不见有丝毫动静。只得无聊的揪着那一边的花瓣儿打发时间,可是肚子已经叫了好半天了,这可怎么办?
又耐心的等了一会,拱出石洞撇了撇那已经偏西的太阳。已经有两三个时辰了吧,那男人该消气了吧?
一个大男人不就被强亲了一下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况且看他那年纪肯定早就是妻妾成群“身经百战”,肯定也不在乎那一吻啦!
这么一想,某女扔了手里揉的不成样的花瓣儿,大摇大摆的就往前院去了。路过荷塘的时候,还不忘伸头看看那为数不多的锦鲤,顺便理了理头发。
只是这一理,就看到那倒映下来挂着淡笑的脸。身体立马一僵,对着那影子呵呵就笑。
一双染着邪魅的凤眸就那么盯着那咧着笑意的脸,她不动,他亦不动。
该死的女人,竟然这么不知羞惭,堂而皇之的去亲男人。真不知已经有多少男人被她给沾染了。这么一想,只觉得嘴角好似被脏东西咬了一般的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