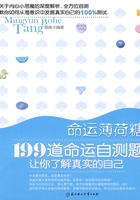第五篇 逼上梁山成好汉——《我的团长我的团》 (3)
“你们知道什么是坦克吗?钢铁的!刀砍上去就断了,子弹打上去弹回来!跟这房子一样高!我掐着鬼子小队长的脖子,拿手榴弹给他脑袋开了瓢!小鬼子拿刺刀从背后捅了我!看这伤!——我不行了!只是想死前吃口饱饭!”
我肘弯里夹着日军小队长的脖子,拿德国长柄手榴弹敲他的脑袋。一个胆怯的日本兵从后边拿刀捅我——这当然是臆想,是我自己都要嘲笑的臆想,但是我的听众已经不仅仅是敬佩,而是敬畏了,他们发出一种哄哄的和嗡嗡的声音。
我非常清楚此战宜乎速,不能给人反应时间。我迅速拉上了我的裤子,在一干人等哑口无言时,我沿着青石路面迅速走开——当然,我挟着那捆粉条。
粉条被摊主温和而坚决地从我腋窝里夺走了,我脸上泛现受惊而失望的古怪表情。摊主也是一个同样的古怪表情,“对不住老弟。我一家也等吃饭。”
我没回头,腋下空空地离开,带着受惊和失望的表情,后来慢慢变成苦笑。禅达也在闹饥荒,日子越来越难,感动人容易,找食很难。
围观者默默无闻地带着羞愧散去。那关我什么事呢?我不可能吃他们的羞愧,拿他们的内疚当药抹在腿上。
决胜之道
孟烦了本来是想要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征服他的听众的,现实却是,他说得把自己都感动了,却不能感动眼下几个要过日子的小老百姓。不是人家心硬,而是“一家等吃饭”的压力,让每个人都变得现实起来。
同样的故事也会在职场发生。
有一个年轻人,他立志要开发传统文化方面的产品,而且认为这将是一个蓝海,他可以提供很好的想法,有钱的人来提供资金,这样慢慢就能把生意做起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行业的领跑者。他带着这个想法四处登门,一百个人当中大概只有一两个人对他的想法有兴趣,大部分人都只是欣赏甚至同情他,“对不起,我们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一句话就将他拒之门外了。
这个年轻人自己办的公司没有坚持半年就垮了,梦想很好,只是别人难以接受。
是真的有人对赚大钱的机遇不动心吗?还是说大部分人都是傻瓜,看不到自己提供的财路?很多想创业的年轻人都会这样疑惑。当孟烦了胳肢窝下面的粉条被老乡拿走的时候,问题就实实在在地暴露出来了,不是你的梦想不够美,只是它不值钱。
那些想要靠着“出卖梦想”去谋生的人,趁早打消此念,在现在这个社会,空谈和梦想依然是一文不值的,人们只有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时,才会愿意和你交换。
有梦想很好,但是不能指望它解决你的生活问题。生活就是生活,不要把自己给骗了。
战术不如战果
场景回放
追赶我们的日军终于在林径上出现,正像我以往经验中的一样,他们拉的是三角队形,轻装步兵在前方搜索,一组轻机枪和一组掷弹筒在后边掩护。我只能看到第一个轻装组,另外的支援兵都在林中和雾里,我们看不见他们就像他们看不见我们一样。
卢沟桥响枪时我弃学,徐州会战时我从军,四年来败战无数却屡屡逃生,逃到后来我很愤怒,飞机坦克没有咱不说它,对方步兵战术的僵化死板像是得了阿译的亲传。一万年不变的三角队形在丛林和大雾中居然照用,火力兵力都被分散,打过半年仗的中国兵都会说找死了。
但败的仍然是我们。直败到有一天,我只好想,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
……
死啦死啦一直推销他的方案:继续往我们死守的机场投送兵力,拖延甚至压垮日军空虚的后防。听着不错,但我军归心似箭,英军忙撤往他们最爱的印度,我们是被扔在缅甸的最后一批。
我们背后机场上的盟友热心和总部联系,只是为了验证死啦死啦的身份。他们的炮兵一直在轰击据说有日军囤集的遥远森林,拒绝让任何一颗炮弹落在攻击我们的日军头上——这关乎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尊严,所以不可说服。
我向着康丫牢骚:“一万年不变的小日本。炮兵轰,步兵冲,步兵冲时炮兵轰。你蹿出来打,步兵退炮兵轰,你不管,炮兵轰完步兵冲,一次次给你耗完了,就这么个死板打法也吃掉半个中国——你服不服?”
决胜之道
我们向来就不缺少战术思想,《孙子兵法》、《百战奇略》、《三十六计》、《吴子兵法》等等,一说出来都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了。但正如孟烦了不能理解的那样,就连一个打过半年仗的中国兵都能看出破绽的日本式打法,却能一直在中国的战场上嚣张跋扈。
“我只能想,是我们出了问题。”的确就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硬件设备不说,相互之前的配合远不如对方那样默契。有再好的战术没有战果,又有什么用呢?
很多想要创业的人,总是会想出大量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思路清晰、步骤明确。但这些想法都无法落实到行动中,也就直接减弱了行动力,到头来还是一团乱麻,不如人家简单的方案有效果。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说:“一家企业有太多的盈利模式即等于没有盈利模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过于高明的战术等于在分解你的实力,等你在战术上花够了心思,可能就在执行中没有了耐心和实力。战术再高明,没有结果就等于胡闹。反而是简单的东西,便于操作和执行,更能推动进程。
但还是有很多人将目光紧盯在想法上,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有哲人说“存在即合理”,我们有时候过于偏重道理,就会不自觉地忽略眼前的现实。不要做一个对现实没有反思、只有质疑的人,把你的目光从分析放回到行动上吧。
再差的战友也胜过没有
场景回放
郝兽医在为蛇屁股检查他胳膊上的一块溃烂,他是望闻问切加摸心脏看舌头,主观加客观地乱用,可以说他用尽一切在无器械情况下能用的诊疗手段,但没有任何治疗手段。老头子五十六岁,或者说,才五十六岁,就被我们不客气地称为“老头子”和“老不死”。他是我们中唯一的医生。没人知道他算医官还是算医兵。做老百姓时匆匆赶往战场救助伤兵,然后被伤兵裹挟进溃军大潮,套件军装,便成军医。他的医术很怪,三分之一中医加三分之一西医,加三分之一久病成医。他从没治好过任何人,所以我们叫他兽医。
……
“不帮!你个能把脚气治到截肢的半吊子兽医!”
那并不是我的形容,而是真事,郝兽医的表情也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那种念叨是并无信心的,痛心指数很高,而说服指数很小——这一向是他——“……有总比没有好的。”
我并不想放过他,“爬到你那儿等死吗?还不如没有的好。”
“没我你们就连往哪爬都不知道了。”
“小太爷正好省事,小太爷就地一躺,等死。”
老头儿看着我,“别孩子气啦。没了我你们也难过的,要不我早走啦。”
我是看了老头儿的神情才知道我说了多过火的话,我不是个擅长道歉的人,我只是换了较柔和的语气,“可是有什么用。”
“有总好过没有的。”老头儿又重复了一遍。
……
迷龙抱着李乌拉走过,确切说是迷龙而不是李乌拉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受尽折磨的李乌拉已经完全寂静下来,连呻吟都不再,于是我看着迷龙走过我们,把他手弯里的东北人放在一个最安静的角落。
安静地照顾着一个垂死者的迷龙看起来让人心碎——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他用草叶为李乌拉垫高了头,用一双刚砸碎过几副骨架的手理清李乌拉湿透了的头发,他把他得到的那份食物全放在旁边,掰下很小的一块,放进李乌拉的嘴里,他甚至有耐心去帮对方的下牙床用些微的劲把饼干压碎,然后用适量到绝不会呛着一个垂死者的水帮李乌拉冲服。
我轻轻捅了在帮我包扎的郝兽医,郝兽医只是抬头看了眼便低下头摇着,“救不了。挨了十好几枪,血还在水里就流光了。”
于是我只好又看着,迷龙把肉干嚼成了丝塞进了李乌拉的嘴里,我看着一个东北黑龙江人抱着一个东北吉林人湿透了的头颅,用他们真正道地的东北话在垂死者耳边絮语,偶尔能飘过来两句,能听懂的话全是“好啦好啦”、“没事啦没事啦”、“算啥玩意嘛”、“老爷们啦”一类全无意义的絮语。
我们从来不知道迷龙和李乌拉到底有什么恩怨,只知道迷龙总揍李乌拉,但总在后者饿得半死的时候给他食物。我们因此更加躲着迷龙,我们想得多恨一个人才能这样对他,让他活着仅仅是为了承受怒气。
但迷龙拥有的好像不仅仅是怒气。
我们看着迷龙用额头顶着李乌拉的额头,那是我们从未想见过他会对他人而发的亲昵举动。
决胜之道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任何一个人,似乎都只是那个年代的符号,但是看过这部小说,却觉得不管是嘴损的孟烦了,还是娘娘腔的阿译,他们都是不能替换的,不能撇下不管的。因为他们是袍泽弟兄,是同生共死度过日日夜夜的人,即使有再多的缺点和不足,他们还是无可替代。
工作中,你可能看到有的人时心里会不爽,可能有人老是对你挑刺儿,可能在你最高兴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向你泼冷水。可能,你一直在想着摆脱这些人,和真正的精英们为伍。其实,最好对付的是那些刻板的精英,最不好对付的恰恰是你身边这些看起来平庸、无赖、难缠的人。他们需要你投入百分之百的生命、时间和精力去面对,如果轻视了他们,也就等于轻视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郝兽医没有能力治疗一个人,但是他的存在,不是治疗不治疗的问题,而是让人心安。李嘉诚宁可不要丰厚的回报,也要留下没有盈利空间的老塑胶花生产厂,只为了让老员工安享晚年,老有所依。
抛开工作关系的轻重,人情不是简单能衡量的。这一点,很多人工作了上十年才明白。不要觉得你身边那些看似没有“业绩”的人是多余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一种身份。人情是社交的副产品,也是人生的收获,别做一个以金钱衡量一切的人。
打仗不用跑得太前面
场景回放
木牌上用精致的工笔书写着:白菜猪肉炖粉条。
识字的人,诸如我和郝兽医,已经快窒息了。
半识字的人,诸如康丫,正在艰难地一个个字数着。
不识字的人,诸如要麻豆饼蛇屁股,还没有反应,没有我们那种从大脑直击胃腔,再从胃腔倒卷回口腔,整得满嘴生津喉头抽搐的生理反应。
康丫只挑自己认得的字念诵:“白——肉——米。”
阿译开始扩大攻势,用他的白灰在每一个要素下划着道儿,“白菜——猪肉——炖粉条!今天我们吃这个!——白菜猪肉炖粉条!”
康丫用了压倒他的音量的音量喊:“我有盐!”
“我弄酱油!”蛇屁股踊跃地卖弄着他的广东腔。
要麻大方地举起了整只手臂,“我找白菜!”
但要麻是那么的仗义,热烈地捅着被他欺负过的豆饼,以至于豆饼都开始发声,“我找劈柴。”
周围都在回旋爆炸着这样的呼声,哪个都比我响亮多啦,“我整锅!”“我来搭灶台!”
“我找碗筷!”“我……我管葱!蒜!大料!”
“兽医你年纪大,说句公道话……。”
郝兽医瞪着我看了一会,慢慢举起一只手,“……我有油。”
……
我站在一张桌子后,如果这个法庭再正规一点儿,这地方叫证人席。
“我是学生从军的,做学生的时候想着当兵,抗击日寇,脑子里的景是所有人往上冲,我是其中的一个。当了兵,我真冲了,迎面炮弹炸出的热气,屁股后莫名其妙地生凉气,我回头一看,我一个,其他人在战壕里乐。”我说。
很多人在笑,看起来有很多人熟悉这么个场景,但我没笑,虞啸卿也没笑。